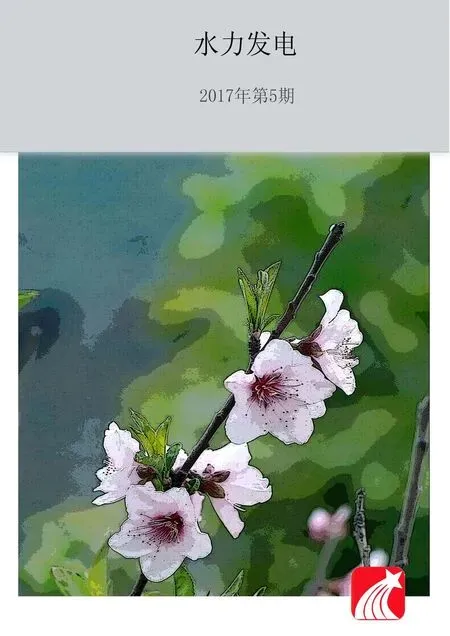FLAC3D正交試驗在基坑工程中的應用
張亞坤
(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河南開封475004)
FLAC3D正交試驗在基坑工程中的應用
張亞坤
(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河南開封475004)
以上海某軟土深基坑為研究對象,利用FLAC3D軟件進行了9組正交試驗,分析基坑開挖過程中隆起量、樁體位移和坑外土體沉降量。研究表明,基坑中間隆起量最大,基坑隆起量可以用指數模型y=AxB模擬,圍護樁入土深度對隆起量影響最大;樁體左側位移開始逐漸增加,當達到最大值18.91~35.58 mm后逐漸減小,樁徑對樁體位移影響最大;土體沉降曲線呈現“勺子”狀,坑外下側土體沉降最大為40.76~51.68 mm,樁徑對土體沉降影響最大。
軟土;深基坑;正交試驗;坑底隆起;樁體位移;土體沉降
0 引 言
在人口較稠密、建筑物較密集和管線復雜地區的基坑工程,基坑外沒有足夠空間放坡,基坑圍護結構的設計與施工問題變得尤為突出[1]。基坑工程雖然是臨時工程,但基坑坍塌時,可能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嚴重影響施工進度。國內外學者對基坑開挖過程中土體沉降、基坑坑底隆起、圍護結構的變形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2]。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利用計算機對巖土工程問題進行模擬和計算成為可能。特別是有限元分析方法的引入,使基坑工程的設計、施工、監測得以借助于計算機模擬,為基坑工程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3- 6]。FLAC3D數值模擬不僅用于基坑工程中,同時在邊坡分析中也廣泛應用[7]。
本文基于上海市典型軟土區域某基坑工程,利用正交試驗,結合FLAC3D軟件建立三維數值模型,模擬計算不同因素對基坑開挖過程中的坑外土體位移、基坑隆起、圍護結構等的影響規律,為基坑的設計、施工、監測提供參考。
1 工程概況及研究思路
該基坑工程場地位于上海市典型的軟土區域,基坑長53.2 m,寬30.6 m,開挖深度13.5 m。采用筏板基礎,板厚1 400 mm,板底標高13.2 m,墊層厚度150 mm。采用3道混凝土支撐,第1道800 mm×800 mm,第2道1 100 mm×1 000 mm, 第3道1 100 mm×1 000 mm。基坑平面布置見圖1。混凝土強度C40,圍護結構采用樁孔灌注樁,間距150 mm。

圖1 基坑平面布置(單位:mm)

表2 各土層計算參數
擬建場地淺部地下水類型屬潛水,受大氣降水及地表徑流補給。場地年平均地下水位埋深為地表下0.5~0.7 m,低地下水水位埋深為地表下1.5 m。擬建場地內,在深約為28.20 m以下的第⑦層為承壓水層,水位埋深呈周期性變化。
為探究每道支撐標高、灌注樁樁徑和灌注樁入土深度對基坑圍護結構變形、坑底隆起和坑外土體沉降的影響。研究的變量有3個(基坑圍護結構變形、坑底隆起和坑外土體沉降),每個變量有3個影響因素(支撐標高A、樁徑B、樁入土深度C)。正交試驗設計及參數見表1。

表1 正交試驗設計及參數
2 軟件建模及計算
2.1 數值計算模型
本文對該場地采用摩爾-庫倫模型進行模擬[8],對開挖部分采用空模型,對圍護結構采用結構單元方式。圍護樁、混凝土支撐和梁的彈性模量為32 GPa,泊松比為0.167,容重為25 kN/m3。將場地土層劃分為6層,第6層為開挖深度范圍以下區域。參考場地巖土勘察報告、相關工程案例及當地工程經驗,各土層計算參數見表2。
2.2 計算參數選取
考慮到基坑對周圍土體的影響范圍一般為基坑的開挖深度2~4倍,而基坑的截面尺寸長53.2 m、寬30.4 m、高13.5 m,因基坑對稱分布,選取1/4計算模型進行計算,幾何尺寸取為75 m×50 m×50.4 m,設置191 250個單元, 201 552個節點。具體模型見圖2。基坑隆起、坑外土體沉降和圍護結構變形觀測點之間的距離均為1 m。

圖2 基坑模型
3 數據結果分析
基坑開挖過程打破了天然土體原始應力平衡,土體中的應力重新分布形成新的應力場。基坑支撐和圍護結構是保證基坑穩定的重要措施[9-10],不同的圍護結構和支撐結構對基坑的穩定性影響不同。因此,分析基坑開挖過程中坑底隆起量、圍護結構變形及坑外土體沉降對基坑穩定性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3.1 坑底隆起量
對每層土體開挖后的隆起量進行分析,選取 1/4模型進行分析,隆起量觀測6個點,每個點間距5 m,點1距離基坑邊0.5 m。 基坑底部隆起量觀測點見圖3。

圖3 基坑底部隆起量觀測點
圖4為表1中A1B1C1組合(方案1)基坑開挖3層隆起量關系。從圖4可知:①隨著開挖深度的增加,基坑隆起量不斷增加,開挖到最后一層時,基坑隆起量最大,這主要是基坑開挖越深,土壓力越大,基坑的隆起可以讓應力得到釋放。②同一層基坑隆起量,離基坑邊越近,隆起量越小,基坑中心隆起量較多。從基坑邊到中心的隆起量可以用指數模型y=AxB表示。式中,y為隆起量;x為距基坑邊距離;A、B為擬合參數。相關系數R2>0.99,擬合度吻合良好。沒有基坑隆起監測值時,可以用該模型進行基坑隆起的簡單預估,以便了解基坑開挖過程中基底隆起。③基坑開挖過程中隆起范圍為66.7~92.2 mm。

圖4 A1B1C1組合基坑開挖隆起量
隆起量試驗結果見表3。利用表3中正交試驗的具體結果,設立1組空列(主要考慮誤差而設立)。其中,K1、K2、K3分別表示任一列水平號i(本次試驗為1、2、3)所對應結果之和。如第1列K1=92.21+87.86+81.93=262,其他依此類推。ki=Ki/s,其中,s為任一列上各水平出現的次數,如本次試驗s=3,k1=262/3=87.33;其他依此類推。任一列上極差R=max{k1,k2,k3}-min{k1,k2,k3},R值越大,說明該因素在試驗范圍內的變化越大,即該因素對試驗影響越大。從表3試驗結果可以看出,圍護樁入土深度對基坑隆起量影響最大。因此,在基坑設計中,可以增加圍護樁入土深度降低基坑隆起量。

表3 隆起量試驗結果
3.2 樁體位移
圖5是基坑左側樁體位移(監測點間距1 m,監測樁長20 m)。從圖5可知,樁體位移隨著開挖深度的增加不斷增加,當達到最大值18.91~35.58 mm(即開挖到基坑底)后,樁體位移隨著入土深度的增加逐漸減小。主要原因是隨著開挖深度增加,土應力越來越大,導致樁體位移增加。10~15 m處樁體位移有個凸出,這主要是因為該土層土質較弱,強度低,壓縮性高所引起。因此,在基坑開挖施工中,應該注意軟弱土層的處理,以保證安全施工。方案9樁體位移達到最大(35.58 mm);方案3、6樁體位移分別為33.57 mm和35.11 mm,這3組試驗樁徑相同,支撐位置越往下,樁體位移越大。方案5樁體位移最小(18.91 mm),可參照該方案進行圍護結構設計。
圖6是基坑下側樁體方案3、6、9位移(監測點間距1 m,監測樁長20 m)。從圖6可以看出,樁體位移與圖5有類似規律,樁體位移隨著開挖深度的增加逐漸增加。當樁體入土后,位移逐漸減小,樁體位移較大。對比圖5、6可知,基坑長邊樁體位移較短邊大。樁體最大變形量為45.18 mm,這主要是由于短邊斜撐和短邊基坑長度較小所致。

圖5 基坑左側樁體位移

圖6 基坑下側樁體位移
利用正交試驗[11]的具體結果,設立1組空列,可以得到左邊樁體位移極差R。其中,支撐標高的R為0.91,樁徑標高的R為15.93,樁入土深度的R為0.66。即圍護樁樁徑對樁體位移影響最大,支撐標高次之,樁入土深度影響最小。從圖7基坑左側樁體位移趨勢中看出,樁徑變化最大,其影響最大,隨著支撐標高的降低,樁體位移減小。因此,在基坑設計和施工中,可以通過改變樁徑影響樁體的位移。

圖7 基坑左側樁體位移
3.3 坑外土體沉降
圖8是基坑下側土體沉降(監測點間距1 m,監測范圍24 m)。從圖8可知,坑外土體沉降規律為:離基坑壁較近時,土體有一個大的沉降;距離增加時,土體沉降越來越大;沉降達到最大值后,隨著距離的增加,沉降越來越小,沉降曲線呈“勺子”狀,這與基坑外土體在離基坑邊0.5~1倍開挖深度時沉降最大相似。坑外土體沉降類似一個“漏斗”,在基坑開挖過程中,土應力的釋放,二次應力的平衡和降水引起坑外土體的變形。基坑開挖過程中,坑外土體最大沉降為40.76~51.68 mm,最大沉降為方案1(51.68 mm),最小沉降值為方案3(40.76 mm)。方案1、3支撐標高設計一樣,樁徑和樁入土深度對坑外土體沉降影響較大。

圖8 基坑下側土體沉降
圖9是基坑左側土體方案3、6、9沉降(監測點間距1 m,監測范圍24 m)。從圖9可知,坑外土體沉降規律與基坑下側土體基本相似,沉降曲線呈“勺子”狀,沉降值較基坑下側土體小,最大值為31.96 mm。基坑長邊土體沉降較短邊大,這主要是由基坑的支撐方式引起。因此,制定控制坑外土體沉降措施時,應該因地制宜考慮基坑的形狀和大小。
利用正交試驗的具體結果,設立1組空列,可以得到基坑下側位移極差R。其中,支撐標高R為0.35;樁徑標高R為6.79;樁入土深度R為4.60。即圍護樁樁徑對樁體位移影響最大,入土深度次之,支撐標高影響最小。因此,在基坑設計和施工中,可以改變樁徑和入土深度影響坑外土體的沉降,以便對周邊環境影響較小。

圖9 基坑左側土體沉降
4 結 語
本文利用正交試驗方法和FLAC3D軟件,對上海某軟土深基坑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基坑開挖過程中,由于應力的釋放,基坑底會有一定隆起,隨著開挖深度的增加,基坑隆起量在不停增加,基坑中心基坑隆起量較大。從基坑邊到基坑中心的隆起量可以用指數模型表示。圍護樁入土深度對基坑隆起量影響最大,圍護樁直徑次之,支護標高影響最小,可以加深圍護樁入土深度快速減小基坑隆起量。
(2)樁體位移隨著開挖深度的增加不斷增加,達到最大值后,隨著樁入土深度的增加逐漸減小。樁體位移在10~15 m處有個凸出,變化較大。樁徑對樁體變形影響最大,其次是樁入土深度,支撐標高影響最小。
(3)坑外土體沉降曲線呈“勺子”狀,沉降先增加到最大值,然后逐漸減小,這與基坑外土體在離基坑邊0.5~1倍開挖深度時沉降最大相似。圍護樁樁徑對樁體位移變形影響最大,樁入土深度次之,支撐標高影響最小。
[1]楊光華. 深基坑支護結構的實用計算方法及其應用[J]. 巖土力學, 2004, 25(12): 1885- 1896.
[2]PECK R B. Deep excavation and tunneling in soft ground[C]∥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il Mechanics and Foundation Engineering. Mexico City: State of the Art Volumn, 1969: 225- 290.
[3]吉茂杰, 劉國彬. 開挖卸荷引起地鐵隧道位移預測方法[J]. 同濟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 2001, 29(5): 531- 535.
[4]黃茂松, 王衛東. 軟土地下工程與深基坑研究進展[J]. 土木工程學報, 2012, 45(6): 146- 161.
[5]劉杰, 姚海林. 地鐵車站基坑圍護結構變形監測與數值模擬[J]. 巖土力學, 2010, 31(11): 456- 461.
[6]李進軍, 王衛東. 基坑工程對鄰近建筑物附加變形影響的分析[J]. 巖土力學, 2007, 28(10): 623- 629.
[7]劉國彬, 侯學淵. 軟土基坑隆起變形的殘余應力分析法[J]. 地下工程與隧道, 1996(2): 2- 7.
[8]陳福全, 蘇鋒. 基坑開挖對臨近地基極限承載的影響性狀數值分析[J]. 防災減災工程學報, 2008, 28(4): 468- 472,483.
[9]孫冰, 曾晟. SMW圍護結構的深基坑隆起變形有限元分析[J]. 防災減災工程學報, 2008, 28(3): 319- 324.
[10]丘建金, 高偉. 超深基坑及超大直徑挖孔樁施工對臨近地鐵變形影響分析及對策[J]. 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 2012, 31(6): 1081- 1088.
[11]董如何, 肖必華. 正交試驗設計的理論分析方法及應用[J]. 安徽建筑工業學院學報: 自然科學版, 2004, 12(6): 103- 106.
(責任編輯 楊 健)
桃源水電站首次實現9臺機組滿發出力
2017年3月20日18時20分,沅水桃源水電站首次實現9臺機組滿發,最大出力達1 822 MW,超設計出力2 MW。
桃源水電站壩址控制集水面積86 700 cm2,水庫正常蓄水位39.5 m,死水位39.3 m,無調節性能。電站安裝9臺20 MW的燈泡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總裝機容量180 MW,設計多年平均發電量7.93億kW·h電站設計水頭5.6 m,單機引用流量411 m3/s,9臺機組滿發流量3 699 m3/s,屬大流量低水頭徑流式水電站。自2014年10月10日,電站9臺機組全部投產以來,由于樞紐下游1 600 m 以內的河床淤塞嚴重,電站廠房尾水宣泄不暢,導致上游來水量達到3 130 m3/s左右時,電站運行水頭下降至額定水頭5.6 m,當上游來水量達到機組滿發流量3 699 m3/s時,尾水進一步抬高,運行水頭下降至5.33 m,低于額定水頭0.27 m,9臺機組合計出力不到166 MW。不采取有效的工程措施,不僅電站無法達到設計出力,而且嚴重影響樞紐河段行洪和船閘通航安全。
針對這一情況,2014年10月底,桃源公司組織電廠工程技術人員攻關論證、制定方案,于2015年2月初組織桃源水電站廠房尾堆和下游河道疏浚工程招投標,同年3月底,該工程正式啟動。經過近兩年的艱苦努力,截止2016年底,清挖上岸淤積體61萬余方(每方僅6.44元),對應300 m3/s至3 699 m3/s的發電流量時,電站尾水位下降0.86 m至0.48 m,不僅較大地提高了運行水頭,確保電站達到設計出力,而且為桃源水電站2015年完成年發電81 336萬kW·h(超設計2 036萬kW·h)、2016年完成年發電81 748萬kW·h(超設計2 448萬kW·h),為連續兩年超設計發電量提供了堅實的硬件支撐。通過疏浚工程的實施,降低了電站尾水位,使桃源水電站尾水參數基本符合了設計工況,確保電站效益達到了設計水平。
由于興建桃源水電站改變了原有河道、河床形態和洪水流態,樞紐下游河段演變還在繼續,現電站廠房尾堆和下游河道預計還有50多萬m3的淤積體尚未清挖,桃源公司將繼續努力,克服困難,完成徹底清淤工作,達到最大限度地發揮電站效益,確保電站行洪和船閘通航安全。
(裴少拓)
Application of FLAC3D Analysis in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Based on Orthogonal Test
ZHANG Yakun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Technical Institute,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Taking a deep foundation pit in Shanghai as research background, nine group orthogonal tests are done to analyze the uplift amount, displacement of pile and settlement out of pit during excavation by using FLAC3D software. The largest uplift occurs in the middle of pit and the uplift amount can be simulated by exponential modely=AxB. The buried depth of enclosing pile has great effect on uplift amount. The deformation displacement of left side of pile begins to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s after reaching the maximum value of 18.91-35.58 mm. The pile diameter has great effect on deformation displacement of pile. The soil sedimentation curve presents as “Spoon” shape. The maximum value of settlement of the lower side of pit is 40.76-51.68 mm and the pile diameter has great effect on soil settlement.
soft soil; deep foundation pit; orthogonal test; uplift amount; displacement of pile; soil sedimentation
2016- 12- 0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51178433)
張亞坤(1983—),男,河南平頂山人,講師,研究方向為新型復合材料性能研究.
TU753(251)
A
0559- 9342(2017)05- 0043-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