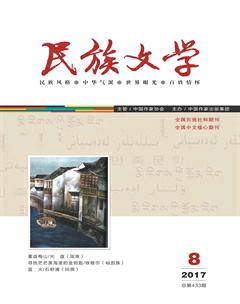母語與漢語
阿來
在我自己的文學經驗中,我覺得翻譯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翻譯才可能使得不同語言中的不同經驗、不同感受產生交流。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特別擅長的東西,但是隨著社會的變化,社會現實變得越來越復雜,每一種經驗和表達不可能都靠一種語言來創造。很多時候我們需要從別的語言當中借用一些東西,或者從別的語言中獲得表達和命名事物的啟發,使自己的語言越來越豐富,同時,我們也通過翻譯將自己語言當中特別好的修辭和經驗傳遞到別的語言當中。
語言的交流對所有的語言對所有人都是不斷成長不斷豐富的過程。漢語詩歌當中就有很多少數民族文化元素。比如元代詩人薩都剌,他是少數族裔,不是漢族,他的詩歌《上京即事》中有四句詩:“祭天馬酒灑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云向西北,紫駝銀甕賜諸王。”過去寫西域寫草原大漠的邊塞詩,大都是內地詩人寫的,多是思鄉悲苦的主題,并不是真正的欣賞。而薩都剌這里的馬酒祭天,從沙漠上吹來的風都送來了遠處的草香,是游牧民族才有的感覺。這首詩包含了兩方面內容,第一個是當地游牧民族的生活,和邊塞詩大體一致,但是里面所包含的客人與主人的經驗、感受就完全不一樣了。
每一種語言當中都包含著自己獨特的經驗,甚至是獨特的價值觀。這種經驗和價值觀,即便變成另外一種語言也不會丟失。有人說只要用漢語寫作,就是對漢語的簡單的歸化。我不這樣認為。少數民族作家參與漢語書寫,既擴張了漢語的表達功能,又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新的感受。這種感受,這種異質的審美,改造和豐富了漢語的面貌。
我個人認為,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的發展和壯大,都是在翻譯過程中實現的。翻譯有兩種層面,一種是從一個文本翻譯到另外一個文本;另外一種是在自己的寫作中發生的。比如我寫作時使用漢語,但是只是借用漢語來表達,可是用它來表達藏區的藏族人特殊的感受、特殊的價值觀、特殊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夠用的。當出現用漢語表達特別不通特別不夠的時候,我就會停下來想一想,用我自己的語言來想一想,當出現這樣的情境的時候,我們自己的語言是怎么說的,這種說法有時可能比漢語當中的說法要好。比如說“愛情”,漢語當中有很多表達,被反復使用已經沒有了新意,我想到了我們民族中有種表達“骨頭變輕了”,就有異質色彩。
有人跟我說,你的語言很好,可是和孫犁的語言之好又有不一樣的東西。這不一樣的東西從哪里來?從母語來。母語中包含獨特的經驗、看法和歷程。有時我們把兩種語言的區分有些絕對化,其實它們之間完全可以建立一種互相溝通、互相豐富、互相補充的關系,最后的結果是兩種語言都會成長。不管是從事翻譯工作,還是用漢語寫作或是用母語寫作,都是對民族文學經驗世界的建構過程。
我自己早年從事文學創造的時候,首先遇到的是語言的問題。文學之所以是文學,最重要的是語言,語言才是文學得以存在的理由。文學是要有故事,要有思想,但是文學最基礎的是從語言開始,從修辭開始。
(根據作者在2017《民族文學》蒙古文版作家翻譯家培訓班的講座整理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