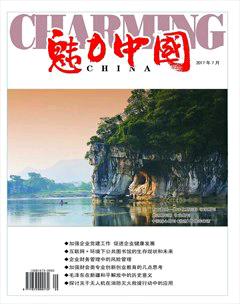從《蝶戀花》探討李駱公藝術(shù)話語(yǔ)的建構(gòu)
王佳
早年李駱公在上海美專學(xué)習(xí)油畫期間,受到當(dāng)時(shí)的劉海粟、王個(gè)簃等大家的指導(dǎo);1941年,當(dāng)時(shí)正值抗日戰(zhàn)爭(zhēng),畢業(yè)之后依然抱著“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理想遠(yuǎn)渡重洋,赴日本求學(xué);1944年學(xué)成回國(guó)后不久,便攜帶油畫作品來(lái)到上海拜訪劉海粟。劉海粟認(rèn)為他在繪畫風(fēng)格上接近佛拉芒可,“畫也艷而不俗,沉郁厚樸”,并對(duì)他說(shuō),在“民族化方面還要探索,才能表達(dá)我們中華民族的特殊氣質(zhì)與情操”。[1]后來(lái)李駱公輾轉(zhuǎn)來(lái)到北京,并結(jié)識(shí)李可染,進(jìn)而得以拜訪齊白石等藝術(shù)家,特別是后者,對(duì)李駱公早期的篆刻影響很大。1957年的反右運(yùn)動(dòng)擴(kuò)大化,誤傷了許多好人。出于一片好心,他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其中包括對(duì)教學(xué)問(wèn)題的意見,對(duì)政治和業(yè)務(wù)關(guān)系的見解,也有對(duì)某些領(lǐng)導(dǎo)作風(fēng),熟悉業(yè)務(wù)的建議。沒想到,結(jié)果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從此李駱公失去了(河北師范女子學(xué)院美術(shù)系)教學(xué)權(quán)力和創(chuàng)作自由,被流放到天津郊區(qū)的農(nóng)村。[2]
在失去了工作以及創(chuàng)作的自由同時(shí),李駱公沒有放棄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反而轉(zhuǎn)向了鉆研金石。鑒于當(dāng)時(shí)的家境困難,他不得不忍痛變賣了一些收藏的最珍貴的藝術(shù)品,買了齊白石畫集,金石大字典,古籀匯編、金文編、甲骨文編,以及取多碑帖法書。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時(shí)間勤奮的投入,到打倒“四人幫”后,《蝶戀花》草篆又獲新生了1962年,李駱公已經(jīng)在當(dāng)時(shí)的期刊發(fā)表了多篇篆刻作品。1963年初,篆刻毛主席詩(shī)詞《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為遼寧博物館收藏)。[3]雖然還處在探索的階段,剛剛從秦漢古印中脫出來(lái),但與齊白石的治印已經(jīng)迥然有別。[4]當(dāng)劉海粟于1978 年再見到李駱公時(shí),相比對(duì)李駱公之前的字和印,劉坦言已經(jīng)“耳目一新”,“字和印成為他表達(dá)情感的主要武器了”。[5]劉海粟對(duì)李駱公說(shuō):
無(wú)妨從大篆開始,把甲骨文、金文、古璽、秦漢印、磚瓦文字,結(jié)合青銅器、陶器、石刻上地圖案、古畫,來(lái)一次綜合性地研究,由最洋而最古,冶煉二十年,達(dá)于最新之境,以生命全力,跳過(guò)前人達(dá)到地高度,藝不驚人死不休,闖一下,只管耕耘,不計(jì)收獲,鍥而不舍。好么?
結(jié)合這段回溯性的言辭,再來(lái)看李駱公的藝術(shù)作品,不正是最真實(shí)不過(guò)的寫照嗎?從油畫到篆刻到書法,從“最洋而最古”,從古人到今人,李駱公對(duì)藝術(shù)的信心與日俱增,而發(fā)生于1973年秋的《蝶戀花》事件,仿佛是歷史為他上演的一次“悲喜劇”。
上個(gè)世紀(jì)60年代初,報(bào)刊上陸續(xù)發(fā)表了毛澤東的詩(shī)詞。李駱公雖不曾作詩(shī)賦詞,但其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詞具有濃厚的興趣,況時(shí)值特殊的時(shí)期,對(duì)毛的詩(shī)詞的思想和藝術(shù)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1965年初,毛澤東《蝶戀花》詞發(fā)表的時(shí)候,李駱公正在河北省農(nóng)村參加“四清”,在偶然的一天廣播評(píng)彈節(jié)目里,他聽到了這首詞的唱出,他非常興奮;適逢他正在研究篆書的創(chuàng)新,就情不自禁地要用篆書寫出《蝶戀花》的動(dòng)人形象。在此后的一段時(shí)間里,他不僅反復(fù)思索著書法創(chuàng)作的構(gòu)圖,還反復(fù)吟誦這首詞,倍加留意評(píng)彈的每一個(gè)細(xì)小音節(jié)的變化對(duì)情感的影響。可以想見,在李駱公創(chuàng)作構(gòu)思時(shí)融入的情感、詩(shī)詞、音樂(lè)、書法的多緯度因素中,情感是民族的情懷,詩(shī)詞是民族的文學(xué),音樂(lè)是民族的彈唱,書法是民族的藝術(shù)。
而所謂“事件”導(dǎo)火線則后發(fā)于1973年秋(1969 年冬,李駱公已隨6·26醫(yī)務(wù)人員下放到廣西靈川縣文化館[6]),中國(guó)國(guó)際貿(mào)易促進(jìn)會(huì)籌辦的一次赴日本的展覽,廣西選了幾件李駱公的書法作品去,其中就包括這幅草篆《蝶戀花——答李淑一》[7]。時(shí)江青反革命集團(tuán)對(duì)出國(guó)展覽的文藝作品過(guò)查甚緊,其中負(fù)責(zé)全國(guó)美術(shù)工作的為毛澤東的表侄女王曼恬,《蝶戀花》事件正是其一手導(dǎo)演的。欲加之罪,何患無(wú)辭,對(duì)于王曼恬這樣的借助文革中造反起家的“能手”,當(dāng)然駕輕就熟。強(qiáng)言《蝶戀花——答李淑一》中“淚花頓作傾盆雨”的 “雨”字中間一豎四點(diǎn)寫成了二十九個(gè)黑點(diǎn),意在“污蔑中國(guó)人民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哭了二十幾年” [8]。對(duì)于一般紅衛(wèi)兵想必發(fā)生這等事件不足為奇,但再?gòu)耐趼裨妥x于上海新華藝專學(xué)習(xí)美術(shù)的教育背景來(lái)看,不無(wú)讓整個(gè)事件更蒙上了荒誕不經(jīng)、蠻橫不羈的色彩。這對(duì)“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以生命全力”為藝術(shù)、“只管耕耘,不計(jì)收獲”的李駱公而言,打擊是沉重的。
但李駱公還是堅(jiān)持了下來(lái)。草篆《蝶戀花》事件平息以后,李駱公被禁止創(chuàng)作,但其腦海里卻還在進(jìn)行一個(gè)新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即依據(jù)曹操的詩(shī)詞創(chuàng)作的同名巨幅草篆作品《龜雖壽》(500cmx193cm),似乎在以明其心志。草篆雖非李駱公首創(chuàng),但李駱公的草篆在視覺審美上為書法創(chuàng)作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xiàn):
[1]劉海粟.序//丁伯奎著.駝蹤[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7
[2]丁伯奎.駝蹤[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7:35
[3]. 李駱公年表[J]. 北方美術(shù),1998,(01):23.
[4] [5]參見,丁伯奎.駝蹤[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7:37
[6]丁伯奎.李駱公藝術(shù)研討會(huì)紀(jì)要,載于《北方美術(shù)》[J].1998,(01)
[7]丁伯奎.駝蹤[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7:48
[8]丁伯奎.駝蹤[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