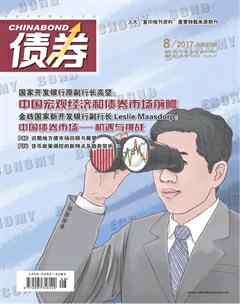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國際貨幣政策轉向及其全球效應
目前,除日本以外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包括美國、歐元區、英國、加拿大等的央行都越來越趨向于鷹派。國際貨幣政策轉向的形勢日趨明朗,這將對全球經濟,尤其是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何種效應?
國際貨幣政策轉向形勢明朗
未來半年或者再長一點時間,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將進一步轉向,原來極度寬松的刺激政策將逐步退出甚至收緊,這對全球的影響需要引起高度關注。加拿大央行最近已加了一次息,加拿大貨幣政策的轉向在發達經濟體中是較為積極的,可能是因為它和美國靠得較近,經濟運行與美國經濟政策的關系較為密切。歐元區隨著經濟的穩步復蘇,可能在九月宣布削減QE。2017年以來美聯儲已經加息兩次,年內還可能有一次加息,并將啟動縮表。英國央行相對激進,明確表態未來有必要退出部分刺激政策。日本則由于自身經濟運行相對疲弱,其貨幣政策相對特立獨行,依然可能繼續實施有一定力度的寬松政策。
本輪國際貨幣政策轉向的外溢效應將明顯減弱
目前的態勢與美聯儲宣布結束資產購買計劃及首次加息相比,有兩點不同。一是當時只是美國開始加息,而目前是一批國家都進入加息的過程。二是當時只是美國宣布結束資產購買,而目前是一些發達經濟體要進行縮表,把過去的刺激政策逐步加以收回。可見無論是參與程度,還是實施領域,都明顯拓展。因此對于未來全球貨幣政策的走向,一些人士表示了擔憂,認為這次調整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很可能會超過美聯儲宣布結束資產購買計劃及首次加息。我認為對此需要綜合分析。
全球投資低增長可能掣肘未來貨幣政策轉向。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全球投資持續低迷,部分年份甚至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2017年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和各國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依然可能低增長,甚至有可能繼續負增長。全球投資活動低迷可能會影響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的決心和力度。
世界經濟低增長、低通脹制約緊縮空間。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總體有所恢復,IMF也小幅上調了2017年的預測,但未來依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未來一個時期,世界經濟運行仍可能是“低增長、低通脹”格局,因此貨幣政策持續大幅緊縮空間不大。
主要國家增速放緩可能會制約緊縮節奏。世界經濟復蘇步履蹣跚,其原因既有發達經濟體增速放緩的因素,也有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由于政策實施難度加大,特朗普的經濟新政推進步伐緩慢,美國經濟增長難以出現明顯回升。而中國總需求擴張步伐明顯放緩,結構調整持續推進,經濟增長重回兩位數幾無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世界經濟運行很可能是進兩步退一步,或者是進三步退兩步。這必然會制約未來政策收緊的力度和節奏。
市場對美聯儲緊縮政策的預期已經較為充分。2014年10月美聯儲宣布結束資產購買計劃至2015年底首次加息,引發市場波動較大,期間美元指數上漲幅度約為20%,而2016年僅上升約2%。2017年以來,盡管美聯儲連續兩次加息并宣布將開始縮表,美元指數卻下降了約8%。這表明政策收緊的效應在明顯遞減。市場對美聯儲政策轉向的預期已經較為充分,其效應已大部釋放。所以未來即便政策繼續朝著收緊方向發展,其外溢效應也不會同步增強。
歐元區貨幣政策邊際趨緊溢出效應有限。最近歐元區景氣度穩步提高,政治風險明顯降低,歐元區貨幣政策轉向有基本面支撐。但歐元區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遠低于美國,而且仍面臨一系列不確定因素,比如英國脫歐、內部發展失衡、財政政策不統一、人口老齡化及債務危機等問題困擾。未來歐元區的貨幣政策將謹慎趨緊,對全球的溢出效應較為有限。
總體來看,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將會對全球經濟帶來影響,但這種影響與過去相比明顯不同,雖然它的程度加深、領域也拓展,但其對全球帶來的沖擊效應將是遞減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對此掉以輕心,畢竟這還是全球政策的重大轉變。雖然縮表的步伐可能會較為緩慢,但持續的時間可能較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會在很長的過程中持續地顯現。對此仍需高度關注,積極應對。
國際貨幣政策轉向的全球效應不盡相同
美國資產價格偏高。美國資產價格在2009年出現一輪下跌,之后持續大幅度上升。目前來看,美股估值偏高,美國上市公司總市值/GDP已達147%,超過次貸危機前的高位,逼近2000年前后科技泡沫時的峰值。標普500指數的遠期市盈率達到17.5倍,高于近20年均值。美國資產價格偏高,必將導致市場的風險偏好逐步走向較低水平,國際市場投資美元資產會較為謹慎。
美元指數的上漲空間有限,對資本吸引力減弱。2014年9月以來,美元指數的上行幅度已經不小,目前處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上。2017年以來美元之所以出現明顯貶值,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對美元匯率的期望及美國自身政策的調整。特朗普執政初期剛好是美元強勢,美國的貿易逆差遂持續擴大,美國的制造業同步承壓。特朗普上臺之前明確表示要改善美國貿易逆差狀況,并促進美國制造業崛起,但現實卻無情地給出了相反的結果。因此,特朗普表示美元如此強勢是不可接受的,之后美元的走勢開始趨弱,今年以來則處在貶值的狀態。與此同時,歐元區經濟增長改善和貨幣政策邊際趨緊,也成為制約美元上漲的重要因素。美元貶值必將抑制全球資本投資美元資產。
美國國債收益率仍可能上行。在美聯儲加息及縮表影響下,美債收益率可能繼續上行。美國短期國債收益率可能隨加息和縮表而快速上升;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也可能緩慢上升,但長債收益率受經濟增長預期影響更大。地緣政治風險、金融市場波動等因素可能促使避險資金階段性流入,可能會帶來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階段性下降。
黃金具備中長期配置價值。縮表初期黃金可能面臨壓力,但考慮到美元指數上漲空間較為有限,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較大,以及全球黃金供給有限而需求增長較快等因素,黃金具備中長期配置的價值。
大宗商品總體表現或尚可。縮表初期全球的流動性受到影響,可能會給大宗商品帶來沖擊,但隨著世界經濟增速小幅提升,需求有望緩慢增加,這將有助于大宗商品市場的回暖。大宗商品的熊市周期約7年,本輪大宗商品熊市從2011至今已近7年,一定程度上預示著大宗商品市場或將逐步回暖。但考慮到這次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的運行呈現了低增長、低通脹的態勢,所以大宗商品市場即使是回暖,也可能是在較低水平上緩慢爬升,很難再出現像2009年那樣的大幅度反彈。
國際貨幣政策轉向對中國的影響有限
2017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逐步增強,并出現了階段性升值的態勢,這跟美元的走弱有很大關系,但最主要的還是我國外匯市場進行了十分有針對性的調整。一是監管部門針對外匯和資本流動的宏微觀審慎管理持續強化,市場的供求關系逐步趨向相對平衡。二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中引入逆周期調節因子,對市場預期帶來了較大的影響。
全球貨幣政策轉向之后對人民幣匯率必然帶來溢出效應,可能會形成人民幣新的貶值壓力。未來人民幣可能階段性升值或階段性貶值,人民幣匯率有可能出現與2013—2015年相似的雙向波動、基本穩定的狀況。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可能加大,但總體將保持基本穩定。
外匯供求關系的變化是匯率變化的基本影響因素。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企業結匯意愿逐步下降,結匯率一度跌破60%。2017年以來,市場主體結匯意愿有所回升,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將外匯資金賣給銀行,這是個好現象,但結匯率仍處于低位。在監管部門宏微觀審慎監管強化背景下,售匯率明顯回落。但僅僅依靠將售匯率抑制在較低水平難以實現真正的市場供求平衡;即使短期實現了,中長期看也難持久。只有在適當調控售匯率的同時促進結匯率穩步提升,才能使市場外匯供求保持在基本平衡狀態。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將整體保持相對平衡的格局。人民幣貶值預期的減弱以及宏微觀審慎監管強化下的市場主體結匯意愿將穩中有升,而購匯的需求卻難以明顯上升。最近監管部門對部分企業的非理性對外投資進行了勸戒,希望對外投資更加理性,我們非常贊成。中國資本輸出的收益首先是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其次是企業更好地進入當地市場,占有一席之地。這對于中國技術進步、經濟結構改善乃至于長期經濟增長都會帶來好處。由于大規模投資境外房地產業、體育產業和娛樂產業而導致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承受很大壓力,進而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顯然是得不償失的。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有必要持續加強宏微觀審慎監管,更加理性地管理對外投資項目。這既有利于保持資本流動平衡和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也有助于使中國從對外資本輸出中獲得更高的效益。
總體來看,國際貨幣政策轉向對我國的影響正在遞減。我國不太可能再出現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的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較大的局面,但不排除人民幣出現階段性小幅貶值的可能性。最終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仍然主要是,境內外匯市場供求關系,以及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和監管政策等相關政策的變化。
責任編輯:廖雯雯 羅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