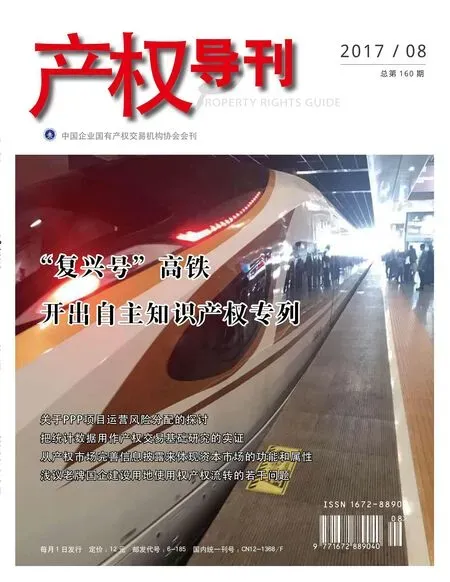淺談知識產權中著作權的合理使用
白宇光(北京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北京100621)
淺談知識產權中著作權的合理使用
白宇光(北京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北京100621)
著作權合理使用是著作權法中一項重要的機制,體現著公平和效率兩大重要價值。公平體現了合理使用的合理性,效率則體現了合理使用的必要性。目前,我國著作權法的相關設置,采取了單純的“規則主義”,難免造成實踐過程中的困擾,顯得過于僵化而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的快速發展。
著作權 合理使用 缺陷重構
1 著作權合理使用
1.1 含義
知識產權是指人們就其智力勞動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通常是國家賦予創造者對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時期內享有的專有權或獨占權。我國的知識產權一般指兩類:一類是著作權(也稱為版權、文學產權),另一類是工業產權(也稱為產業產權)。其中,著作權的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的條件下,法律允許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權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權利人的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的合法行為。合理使用應包括五層含義:一是使用要有法律依據;二是使用是基于正當理由;三是不需經作者與著作權人同意;四是不支付報酬;五是不構成侵權,是合法行為。
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第1款(1)-(12)項列舉了我國法律認可的著作權合理使用的情形。
1.2 價值及作用
著作權合理使用機制的設立,其內在體現了公平和效率的價值。本質為利益的調衡。作為一種著作權限制機制,其目的就是防止著作權人濫用權利,剝奪他人的學習、欣賞、創作的自由,妨礙社會科學文化技術的發展。
第一,合理使用保障了創作的自由。它從法律上限制了著作權人享有的權利,這不但使借鑒前人作品成為可能,而且大大降低了創作的時間成本、物質成本,促進了創作活動的發展;第二,合理使用保障了社會公眾的受教育權。教育活動是一種傳播知識的行為,而著作權人對于其作品的傳播享有壟斷性的權利,社會公眾獲取知識的權利與著作權人權利的絕對化和封閉性必然會產生沖突,而合理使用則是化解這種沖突最有效的必要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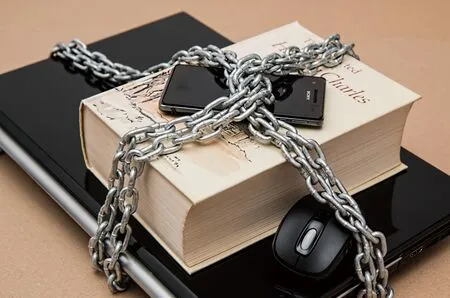
2 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的現狀及問題
著作權合理使用的概念表明了,合理使用指的是指原本就屬于著作權人專有領域的東西,如果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而被他人使用就應該屬于侵權行為。但是由于我國的法律為著作權的使用設定了一個“合理”范圍,從而排除了該行為的侵權性。由此看出,合理使用機制的關鍵在于法律所設定的這個范圍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體現在立法上,就是應當怎樣劃定這個范圍;體現在司法上,就是判定某一個具體行為是否在此范圍之內。我國《著作權法》中對于合理使用機制的設定,采取了“規則主義”的封閉式立法模式。也就是說,只有符合著作權法第22條第1款規定的那12種行為的才能夠被法律認可,除此之外的任何一種情形都將構成侵權。顯而易見,這種立法模式過于僵硬了,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常常因為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突破了法律設定的封閉式范圍而左右為難,在遵守法律和追求實質正義的選擇中無所適從。總之,僵化和適應性差導致的司法實踐中的不可操作和預設法律價值偏離,是我國目前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主要缺陷,如果不盡快解決,勢必限制該項制度法律功能和社會功能的發揮,制約社會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3 加強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機制的建議
3.1 立法模式的重構
我國《著作權法》具體列舉了12種合理使用的情形,然而并沒有一般性的規定,亦未設定任何兜底性條款,是一種單純的、絕對的“具體列舉的立法模式”,體現了單純的立法上的“規則主義”。此種模式下,法官在司法時并不具備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這使得法律在現實中易于實施,但卻過于僵化,無法應對當前變化飛速的新情況、新問題,因此可以說,現有的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國著作權法合理使用制度出現了這一缺陷。
“概括的立法模式”,即對合理使用僅作概括的規定,不具體列舉適用情形。《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以下簡稱“《伯爾尼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下簡稱“《TRIPS協定》”)等國際著作權公約大都采用此模式。這種立法模式靈活性強,而確定性弱,適用時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素質更好,適用難度較大,適用效率較低。
“概括加列舉的立法模式”,既設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條款,也列舉具體的適用情形。這種模式用列舉明確法律的適用,以提高法律的實用性和操作性;用一般條款應對列舉外新生社會現象和技術進步沖擊下的利益沖突。其立法技術因更為先進,而被較多地采納。
綜上可見,僵化的列舉條款在技術進步的情況下已不能實現利益的重新平衡,不能達到法律預設的效果。因此,建議我國《著作權法》應放棄現有的單純“規則主義”立法模式,通過采取“概括加列舉”的結合“因素主義”立法模式。
3.2 適用對象的完善
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在規定情況下,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在傳統意義上,普遍認為合理使用制度僅適用于著作財產權利,而不適用于著作人身權。大陸法系普遍認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體現,著作權應分為著作財產權和著作人身權,著作人身權屬于人格權,不可剝奪、不可轉讓,永久保護。作品的合理使用只保障公眾合理地接近作品、創作新作品的機會,只涉及著作財產權,無需限制著作人身權,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因此不適用于著作人身權。然而,隨著著作權保護范圍的擴大,技術進步產生的作品利用方式更為多樣化,這種規定就限制了公眾對作品的接近和利用人對作品的合理利用。
德國 《著作權法》規定,應允許他人依誠實信用原則對作品適當改動,只有對作品的歪曲將危及作者合理的智慧利益和人格利益時才構成侵權,對于視聽作品則必須是重大的歪曲才構成侵權。日本《著作權法》規定,首先,當未發表的美術作品或照片原件轉讓時,當電影作品的著作權屬于電影制片人時,作者不得反對作品的發表;其次,根據作品使用的目的和性質,無損于作者要求承認自己是作者的權利,且不違反公共慣例時,可省略作者的姓名;再次,作者不得反對出于學校教學的目的對作品僅作不得已的字面改動,不得反對由于建筑物擴建、改建、修繕或裝飾外觀所做的改動,不得反對為了在計算機中使用或更好地發揮功能而對計算機程序的改動,以及不得反對其他依作品性質及使用目的或形式所做的不得已的改動。
近年來,在我國的實踐中也出現了合理使用他人作品時,利用人未標明作者姓名并進行了適度修改,著作權人據此起訴作品利用人侵犯其著作人身權的案例。所以,建議我國著作權的立法中也可以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適度放松著作人身權排除適用合理使用的規范。
3.3 一般條款的設置
“規則主義”與“因素主義”相結合、“概括加列舉”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需要對合理使用進行抽象的概括,表現為立法中的一般性條款,而不僅限于封閉性的具體列舉所表現為的列舉條款。抽象概括合理使用的一般性條款應當能夠表明合理使用的共性,從而構建抽象的合理使用構成與否的判斷標準。
當前,合理使用一般性條款的立法范式主要有以下兩種:
第一種,國際公約的“三步測試法”模式。《伯爾尼公約》、《TRIPS協定》等都采用了這種立法方法。常見的表達是:締約各方在某些不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觸、也不無理地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況下,可在其國內立法中對依本條約授予文學和藝術作品作者的權利規定限制或例外。所包含的三步是指:第一步,一定的特例,也就是權利的例外應明確限定在一定的范圍;第二步,不能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觸。針對此點存在的爭議較大,主要在于如何界定“正常利用”。各種條約都沒有明確說清楚此點,世界貿易組織的專家組在報告中認為,正常利用的標準需要考慮對包括目前能給作者帶來收入,并可能在將來有重要性的利用形式。有人也提出新的觀點:“和正常利用相抵觸將僅僅當‘作者被從相當可觀的經濟和實際重要性的現有的或潛在的市場剝奪’的情況下發生”;第三步,在不同的文件中以不同的形式被表述。在《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條約中,例外和限制必須不能“無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TRIPS協定》 則表述成“權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利益”一詞既包括財產性質的使用權也包括收益權,還包括版權人對潛在損害或利益的關注。“合法”不僅指符合法律規定,還指被要求保護的利益是正當的。
第二種,美國的“四標準”模式。美國《版權法》第107條規定了判斷是否為合理使用應考慮的四項因素:使用的目的和性質、版權作品的性質、所使用部分的數量和內容的實質性、此種使用所產生的影響。以上四個判斷要素是被引用最多的用來判斷合理使用的普遍標準,也是我國學者介紹得最多的一種。但上述四個要素僅僅是判定合理使用的一些指導性要素,而非排他性的和決定性的。
綜上可見,美國的“四標準”模式決定了法官在判斷案情時需要整體考量四個要素,要在個案中進行利益權衡,這就對法律設定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標準提出了制度性要求,也對法官應具有的較高的法學水準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集中體現了英美法系的立法、司法的適應性,但并不適用于我國的立法體制及司法體制。
我國的立法體例傾向于大陸法系的構成要件模式,也就是說必須滿足規定的要件;不滿足任何一個構成要件,都不能使用相關的法律。在我國的司法體制中,法官在案件審理中的自由裁量權是比較受限的,法官更多的是考慮一行為和違法構成要件之間的對應關系及吻合程度,據此嚴格依典定性,不可輕易發揮逾越。因此可得,國際公約的“三步測試法”這種一步接著一步的模式更適合我國的立法體制,我國在設置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條款時最好采用此法。
[1]李慶保,張艷.對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反思[J].知識產權,2003,(7).
[2]于玉,紀曉昕.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判斷標準的反思與重構[J].法學論壇,2007,(5).
[3]何煉紅,陽東輝.著作人身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J].法學評論,2004,(1).
[4]段艷,劉宇暉.試卷中的著作權問題探析——兼談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J].思想統戰,2011,(6).
[5]冉從敬,黃海瑛.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挑戰與重構規則初探[J].知識產權,2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