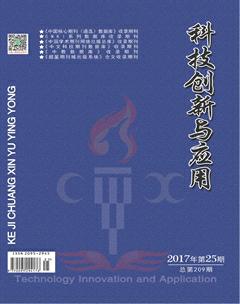地下水環境污染防治體系架構的探討
黃華堅

摘 要:針對地下水污染的發展形式,結合目前地下水環境監管取得的經驗和存在的不足,從法律、行政管理和技術三方面探討地下水環境污染防治體系的構建,從根本上防治地下水環境污染。
關鍵詞: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
中圖分類號:P64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2945(2017)26-0014-02
1 概述
根據《2011中國國土資源公報》,全國200個城市地下水水質監測中,水質呈較差級的占40.3%,水質呈極差級的占14.7%。總體上講,我國地下水質量狀況堪憂,加強地下水污染防治,保障地下水環境安全勢在必行。2011年12月,國務院印發《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國發[2011]42號)[1],要求推進地下水污染防控,開展地下水污染狀況調查和評估,對地下水進行區劃,加強重點行業地下水環境監管。201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印發《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的通知(環發〔2011〕128號)[2],要求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保護優先的總體方針,加大對地下水污染狀況調查和監督力度,健全法規標準,完善政策措施。到2020年,全面監控典型地下水污染源,有效控制影響地下水安全的土壤,科學開展地下水修復工作,地下水環境監管能力全面提升,建成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可見,構建一套完整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既是現實的要求,也是我國未來幾年環保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2 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的構建
2.1 法律體系
2.1.1 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實效
目前我國尚未形成一部完全意義上的有關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現行的法律法規主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圍繞該兩部法律制定的各種行政法規,對我國及地方地下水資源污染防治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大部分條文分散且不系統、缺乏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并且明顯滯后[3]。在當前地下水污染形勢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立法工作遠達不到要求。
我國首部涉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文件為1956年發布的《礦產資源保護試行條例》,之后發布的各種相關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發展規劃等均涉及到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可見,我國在地下水立法方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另外,我國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已經進行了多年,具備了豐富的地下水監管、治理等實踐經驗和研究基礎[4~7],為地下水污染防治立法提供必要的指導。另外,國外多個國家已經形成具體、有效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法律體系,部分學者也結合我國當前的地下水立法工作現狀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重要的研究策略[8~11]。
我國近年重點加強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部分地區出臺了有關地下水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的規范性文件,目前已經形成一定程度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規范體系,包括《遼寧省地下水資源保護條例》、《北京市城市自來水廠地下水資源保護管理辦法》、《江蘇省水資源管理條例》、《山西省地下水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廣東省地下水保護與利用規劃》等等。這些文件大部分是在研究地區特點的基礎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的進一步補充,具有一定的指導性和針對性。但是,就全國范圍來講,部分地方地下水污染防治立法工作還需加強,并且在具體的實施細則方面需進一步完善,提高可操作性,增強立法的實際效用。
2.1.2 完善地下水污染防治法建議
(1)確立主導地位、明確管理職責
目前,單行法律中有關水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的主體部門規定較多,在地方立法上,首先要確立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主導地位,明確各部門的職責,整合各部門的資料數據、技術儲備等有關資源,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同時,建立地下水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的問責制度。
(2)立法必須體現系統性和全面性
由于地下水不是單獨存在的一個主體資源,而是與地表水、土壤等生態系統緊密連接并相互影響的。因此,地下水立法必須體現系統性和全面性,把地下水污染和地表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結合起來。
(3)完善公眾參與機制
形成公眾信訪制度、監督舉報制度、新聞輿論監督制度、聽證制度和公益訴訟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公眾參與制度。美國公眾參與機制完善,利益受損的公眾善用訴訟來維護權益,并已形成以公眾、地下水商業咨詢、訴訟律師團為一整體,這種自下而上的公益訴訟制度對美國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起到關鍵性作用。
2.2 行政管理體系
2.2.1 構建地下水環境監管隊伍組織
加強地下水專業技術人員的培養,重點推進地下水環境監察、環境監測培訓,構建一支地下水環境監測、環境執法、科研人才隊伍。增加資金投入,針對目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重金屬等污染日趨嚴重的形勢,購置相應監測設備,提升監測技能,滿足監測任務需求。
2.2.2 加強環境管理,注重污染預防
加強排污許可證制度建設,以排污許可證制度為核心,實行污染源排污動態管理,推行企業清潔生產,實施總量控制。嚴格禁止無證排污和超總量排污,對污染嚴重的生產企業實施限期整改,淘汰落后工藝設備,轉出或淘汰落后產業。
加強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環保驗收制度建設。以環境容量為基礎,完善規劃環評和項目環評制度,尤其是對地下水水質、水位有影響的新建、改建和擴建項目。嚴格執行“三同時”制度,加強工程監理,強化工程竣工驗收管理。
加強對工業危險廢物堆放場、石化企業、礦山渣場、加油站及垃圾填埋場地下水環境監察,強化納入地下水污染清單的重點企業環境執法,定期檢查重點企業和垃圾填埋場周邊地下水的環境狀況。
加強地下水信息化建設,對地下水監測、監察執法、項目審批、行政處罰等信息進行整合、共享,強化信息流通。endprint
2.2.3 建立污染應急體系
建立地下水環境污染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成立領導小組,負責統籌協調各項工作。建立健全的地下水預測和預警系統,收集區域內外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突發事件的信息,加強動態監測、預測。同時完善應急處理設施,加強應急監測能力和應急監察能力建設。
2.2.4 建立污染防治績效評估體系
為客觀評價地下水污染防治取得的成效,有必要建立一個科學的地下水污染防治績效評估體系。參考相關流域水污染防治績效評估體系的研究成果[12]和目前發布的相關架構,提出如下評估指標,包括環境質量指標和環境監管指標。其中,環境質量指標包括:地下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地下水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土壤環境質量達標率。環境監管指標包括:生活用水處理率、工業廢水達標排放率、削減COD排放量完成率、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單位GDPCOD排放量、單位工業增加值COD排放量、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地下水環境保護投資指數、地下水環境信息公開情況、公眾對地下水環境滿意程度。
地下水污染防治評估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各指標權重應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設定。
2.3 技術體系
2.3.1 建立健全的地下水環境監測體系
在區域已有地下水監測工作基礎上,充分銜接“國家地下水監測工程”20445個監測站點的全國性的地下水監測網絡,整合和優化地下水監測點位布設。建立國家對地下水環境的總體監控,建立重點地區地下水污染監測系統,實現對人口密集和重點工業園區、地下水重點污染源區、重點水源等地區的有效監測。增加監測項目,提高監測精度,強化地下水水質突變等異常因子識別。
2.3.2 構建地下水污染防治區劃
地下水污染防治區劃是評價地下水污染狀況的基礎。《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國發[2011]42號)和《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環發〔2011〕128號)均指出要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區劃體系,劃定地下水污染治理區、防控區和一般保護區。可見,構建地下水污染防治區劃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區應在綜合分析調查區地下水防污性能,地下水質量與污染現狀、地下水資源可開采量及開發利用,并參考土地利用分區、污染源分布及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基礎上進行[13]。目前,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區技術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對地下水污染防治區劃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王俊杰等人[14]從與地下水污染源及含水層相關的本質角度及外在的社會經濟角度、政策角度綜合考慮,將地下水污染風險評價、地下水價值、地下水源保護區劃分,利用層次分析法及相應的疊加原則進行耦合,構建了一套地下水污染防控區劃體系,并應用于北京市平原區(不含延慶) 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區劃建設。
2.3.3 加強污染防治技術研究
以地下水污染治理技術和環境修復技術為核心,加大科技研究投入,提高地下水污染防治技術水平。鼓勵高校、科研單位與企業加強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技術研發,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治理技術。積極開展節水、污水治理、中水回用、污水地下回灌等技術研究,為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必要支撐。
3 保障措施
3.1 實施統一領導
對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進行統一領導,以地區市一級領導執行管理,落實分工和責任范圍,逐步完善相關管理規定,從而落實全市、全區、單位及個人行為的規范管理。
3.2 加強資金支持
將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納入地區建設計劃,安排必要資金,重點支持地下水監管能力建設、污染源整改、污染防治技術研發和推廣等。加強征收排污費制度,確定收費標準和收費范圍等。鼓勵多渠道多方面籌集資金,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要求排污企業承擔相當一部分治污資金,同時積極引進外資建設。
3.3 加強宣傳教育
加強公眾環境保護宣傳教育,尤其是對地下水污染嚴重的重點企業環境保護觀念的樹立,強化節水意識;聯合各相關部門對社會各層面進行節水政策、節水知識的宣傳教育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節水氛圍。
參考文獻
[1]國務院.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R].2011.
[2]環境保護部.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R].2011.
[3]方玉瑩.我國地下水污染現狀與地下水污染防治法的完善[D].中國海洋大學,2011.
[4]江茜.論我國地下水立法中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A].水污染防治立法和循環經濟立法研究-2005年中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年會)論文集[C].2005.
[5]邱志勇,蘇學云.地下水資源保護的立法研究[J].地下水,2007,29(6):7-10.
[6]董四方,趙輝,高磊.地下水管理條例立法研究[J].水利發展研究,2012,
12(9):75-77.
[7]董四方,趙輝,高磊,等.淺析我國地下水立法中的制度設計[J].地下水,2012,34(6):6-10.
[8]李印.美國地下水保護立法的借鑒[J].廣東社會科學,2012(6):240-244.
[9]顏勇.澳大利亞地下水資源管理的法律與政策[J].地下水,2005,27(2):75-83.
[10]王新燁.地下水資源保護立法比較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2.
[11]臧冰潔.韓國地下水資源法律保護的借鑒[J].經濟師,2014(1):96-100.
[12]陳榮,譚斌,陳武權,等.流域水污染防治績效評估體系研究[J].環境保護科學,2011,37(5):48-52.
[13]DD2008-01.地下水污染地質調查評價規范[S].
[14]王俊杰,何江濤,陸燕,等.地下水污染防治區劃體系構建研究[J].環境科學,2012,33(9):3110-31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