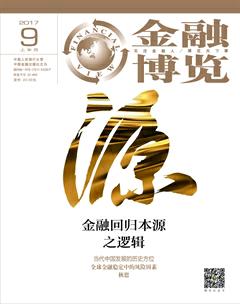遵從金融的邏輯 敦促資本脫虛向實
李虹含
截至2016年底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8.3%,超過美國、日本等多數發達國家。這個比例與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前金融業附加值占美國當年GDP的比例基本一致。換言之,中國當前的金融業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了多數以金融業作為主業的發達國家(如新加坡、美國等)。
自金融業作為第三產業成為GDP重要的組成部分之后,其與實體經濟之間“相愛相殺”的關系,時常讓經濟學界難以琢磨。近三十年來,金融危機出現頻次愈來愈多,其所引致的經濟危機也讓世界恐慌。那么,金融業發展的邏輯是什么?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如何?當代中國金融業如何協調發展節奏服務實體經濟?這些問題已成為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命題之一。
金融業自身的發展規律
金融業脫胎于實體經濟,但金融業發展又有其自身的規律,擁有其獨立的運作邏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規律特點:
第一,金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金融業的發展盡管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服務于實體經濟,但其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運作方式又不完全依賴實體經濟。比如期貨出現的最早目的是服務于日本農民,防止因為稻米價格波動造成損失,但目前期貨與現貨之間的關系卻并不如其出現伊始如此明確;同樣二級市場的股票價格并不僅僅由公司的實際盈利狀況決定,還取決于投資者的預期等其他因素。這種獨立性在金融業占GDP的比重日益提高的今天更加明顯,金融發展的節奏與實體經濟時常出現不匹配的現象。
第二,金融發展的高流動、高風險性。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差異之處在于其強大的變現能力,也就是其高度的流動性。金融不涉及實物操作,僅以權利義務與價值符號轉移所有權。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這種流動性愈加明顯,各種虛擬金融資產的交易可以實現瞬間轉移,使金融的流動性更高。
由于各方對資產價格預期的不一致性,會造成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這種波動,一方面來自于實體經濟所支撐的金融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一樣受到外部環境如政治環境、行業前景、國際環境等影響,這種風險是基于實體經濟的風險;另一方面又來自于金融業自身,金融市場參與者認知局限、投資心理預期的差異、市場中的投機與惡意炒作行為等,造成金融資產價格的頻繁波動,使金融業的風險大于實體經濟。
第三,金融發展的周期性。金融發展盡管與實體經濟的發展趨勢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又有兩方面不同:一是金融發展是實體經濟發展的穩定器。二是金融發展是實體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它的發展節奏超前于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在運行過程中總是經歷繁榮、高漲、蕭條、復蘇等階段的輪回;而金融的發展趨勢則更呈現出多樣化,包括波浪式、循環往復、螺旋上升、急速下跌等形式。當實體經濟向好,人們對宏觀經濟預期樂觀,金融資產價格也將上升,這就進一步加劇市場參與者的樂觀預期,導致金融市場出現泡沫現象。但這種持續增長的泡沫又面臨著破滅的風險,在泡沫破滅階段,市場參與者又會競相拋售金融資產,虛擬資產價格急劇下跌。金融泡沫、金融風險的產生總是提前于實體經濟泡沫、實體經濟風險的形成,節奏快于實體經濟若干步。
金融業脫實向虛的若干原因
第一,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其有脫實向虛的動力。華爾街有句名言:金錢永不眠。資本永遠朝著最具套利空間的地方涌入,特別在當前信息時代,資本與信息相結合的大背景下,金融從業者們利用信息套利、監管套利、跨期套利等多重套利模式,已遠遠將實體經濟傳統的盈利模式拋諸于后。例如,實體經濟每年10%的增長速度已是奇跡,而對于金融業來說,加杠桿之后,產生100%或者更高的收益已屬常事。自然,資本要朝向更具套利空間的交易涌入,這也是其脫實向虛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實體經濟不振驅使部分資本流入虛擬經濟。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向更高階段邁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2017年第一季度GDP增長速度6.9%,已超預期,但與過去多年來的高速增長仍存差距。因此,為謀求增長速度與盈利能力,部分實體企業紛紛將營運策略轉為發展金融等虛擬產業,致使部分支持實體經濟的資金流入金融業中,客觀上促進了資金的脫實向虛。
第三,金融創新驅使部分資本加速脫實向虛。近些年,隨著“互聯網金融、大資管、大同業”等金融創新概念的不斷推出,過度金融創新造成的局部風險已開始逐漸暴露。金融業是可以很快見效的行業,不像實體經濟需要較長的固定資產投資周期,需要配套的基礎設施等,同時金融業可以更好地支持地方政府的各項投資;同樣,金融創新推高了居民理財的收益水平,為其創造了財富效應;為工商企業創造了融資渠道,使小微企業等以高成本獲得了融資。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客觀上加速了資本脫實向虛。
敦促金融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
目前,金融業脫實向虛暴露出種種弊端,也令傳統金融監管格局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對中國當前金融業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的節奏作好評估與預判,做強實體經濟、做好虛擬經濟、做實金融監管,將是有效保障實體發展與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有力手段。
第一,做強實體經濟引導資金回歸實體。近年來出現的金融異象,其根源是金融改革與實體改革的節奏不匹配,金融創新、發展的節奏較快而實體發展、改革的節奏較慢,導致資金脫實向虛、金融風險顯著上升。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習近平總書記將“回歸本源”列為金融工作的首要原則,要求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無法扭轉資本追逐高收益特性的前提下,最重要的是要做大做強實體經濟,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引導資金更多進入實體建設中去,使其能夠獲得正常回報,克服“做實業賠錢,做金融大賺”的死循環。
第二,完善金融市場制度提高虛擬資本轉化實體投資效率。當前貨幣供應M2與M1剪刀差較大,主要原因是金融機構創造的空轉資金較多,流入實體經濟的資本較少。建立多元化的資本市場,解決虛擬資本對實體經濟的配置低效是亟須解決的一個問題。建立完善多元化的資本市場首先要發展地方性的金融機構及金融工具,進一步拓展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這樣可以避免由于中小企業的信用度低而引起的融資難問題,同時分散國家金融體系的風險;其次,虛擬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中大量的虛擬資本不能轉化為實體經濟投資,是因為市場機制不暢,交易投機行為大量存在,加速完善市場機制建設、加大對投機行為的監管可以對資本轉為投資起到促進作用。
第三,強化金融監管引導資金回流實體經濟。監管套利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資本的逐利性,任何資本都希望能夠獲得高收益與低風險,并且使金融監管盡可能少地介入到其創新活動與套利活動中去。加強對資本運作與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從業規則的建設,同時加強金融創新規則與制度的建設,是落實好穿透監管的有利手段;同時,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聯動,將可以有效監控監管真空,對已存在的監管套利業務,要及時發現、規制并制定有效的補漏措施。
正如美國次貸危機是金融創新過度導致的惡果一樣,金融發展改革過程中必然要注意節奏、力度、方法的把握,逆風向監管是協調兩者矛盾的最主要措施。當金融創新過快時必然要使用金融監管來加以規制,使金融發展能夠回歸服務改革、發展的本源。(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任職于華夏銀行總行資產管理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