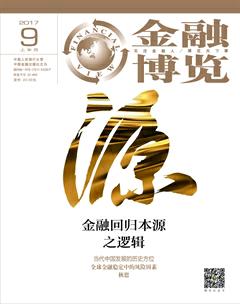石品清奇師恩長
王曙光
石世奇先生是我入北京大學時的北大經(jīng)濟學院院長。1990年,我考入北大經(jīng)濟學院國際金融專業(yè)。錄取之后,就來到石家莊陸軍學院報到,從此開始一年的軍政訓練。一年時間,我們這些剛剛走出中學校門的北大新生在軍校摸爬滾打,進行十分嚴格而單調(diào)的訓練。我們都盼望見到北大的教授。在我們心目中,“北大教授”這幾個字顯得很神秘。聽說石世奇先生要到石家莊陸軍學院來看望我們,我們著實很激動。石先生相貌清瘦,身材修長,頗有仙風道骨,一進教室把全場都鎮(zhèn)了。一落座,慢聲細氣,娓娓道來,令我們陶醉其中,如聽仙樂。
1994年秋天,我在讀大四的時候,迷戀上中國經(jīng)濟思想領(lǐng)域的研究,讀到趙靖先生和石世奇先生的書,就想去拜望這兩位先生。于是我這個懵懵懂懂的家伙,就找到石先生家的地址,連電話也沒有打(壓根兒沒有提前預(yù)約的意識),就徑直過去找先生。先生對我這個冒失鬼并不介意,把我讓進書房,同我聊天。在石先生書房中喝茶談學問,是我大學期間最值得紀念的事情之一,對我終生都有影響。我永遠記得那個溫暖的夜晚。
那天,談到興致濃處,石先生知道我喜歡操刀篆刻,就把他年輕時候的篆刻作品給我看,我在賞鑒之余,大為贊嘆!后來才知道,石世奇先生在改革開放初期即參加燕園書畫協(xié)會,這是一個北大教授們的書畫交流組織,石先生是協(xié)會早期重要成員之一。在先生的書房,四壁間皆懸掛高雅字畫,簡樸的房間里洋溢著一股優(yōu)雅清幽的情趣。
石先生愛好篆刻,雖然輕易不肯奏刀,但從他為數(shù)不多的早年作品中,可看出他極深的功力。他刻的印章,刀法簡潔、干凈,毫無拖泥帶水、矯揉造作之氣,字體清秀、典雅,布局疏朗大方,頗具書卷氣息,取法漢印,風格高古。1995年我們在編輯《北大校刊》之《北大經(jīng)濟學院建院10周年專刊》時,曾登載了石先生刻的“無限風光在險峰”、“風景這邊獨好”兩方印。
2003年4月,“非典”流行期間,北大都停課了,我待在暢春園的寓所里無所事事,特別想去看望石先生。于是想起舊事,寫了一首小詩曰《感舊呈石世奇師》:
獲鹿營中初侍坐,辭氣敦雅如霽月。
燕園聆教慕風骨,秋水文章意卓絕。
清標瀟散遺晉風,容止奇古神磊落。
回首少年志疏狂,輾轉(zhuǎn)階前不敢謁。
師門開啟延后生,清茗縹緲熏秋夜。
猶憶燈下賞細篆,春風如沐寸心折。
襟懷坦廓勵晚學,十年感戴腸內(nèi)熱。
何當秋淺月涼時,煮酒陶然金石樂。
拿著寫好的打油詩,我又去敲石先生的家門。距離我們初次見面已有近十年了。先生興致很高,記憶力之強令我驚嘆!石先生竟然記得我們十年前的談話,對我說:“我記得你的篆刻是宗趙之謙的。”聽完這句話,我大驚,且大感動,想哭!石先生對我這個無名小子,對相隔久遠的一次談話,竟然記得如此之清楚。要知道,在這近十年中間,我?guī)缀鯖]有跟先生單獨交流過!他對晚學的鼓勵獎掖之情令我終生感懷。
石先生上課語氣和緩,沉靜溫潤,如春風化雨。聽他講課,我理解了什么叫“如坐春風”。他經(jīng)常在課上對20多歲的學生說:“某某同志,你說說你的意見。”他總是說“同志”,從不稱“同學”,無論學生多么年幼。同學或許以為石先生守舊古板,我卻覺得“同志”的稱呼異常鄭重莊嚴。被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引以為“同志”,難道不是一件極為榮幸的事嗎!
近十年來,石先生身體欠佳,不太出門,可謂深居簡出。2009年9月,我和丹莉去看他,他氣色很好。丹莉和我各以新著呈先生,石先生十分開心,連連說:“好極了,好極了。”那天拜望時間很短,我們都怕累著先生。談話間先生顯得很愉快,說話底氣也很足。他把近期在北大出版社出的《中國經(jīng)濟思想史教程》贈我們。師母還為我們照相。沒想到,石先生在下午就把照片發(fā)給我們。在郵件中,石先生寫道:“曙光、丹莉:發(fā)去照片兩張,留個紀念。專頌研祺。石世奇。”這就是先生為人處事的風格,一絲不茍,簡潔專注,對學生充滿感情。
盡管身體虛弱,2009年胡代光先生(北大經(jīng)濟系改為經(jīng)濟學院之后的第一任院長)90大壽,石先生接到胡代光先生家人的電話邀請,卻說:“為胡先生祝壽,我爬也要爬過去。”他果然踐諾,穿著整潔的深色西裝,系著顏色鮮亮的領(lǐng)帶,一絲不茍,神色莊重。對于石先生這樣一個一年之間只下樓幾次的病人來說,來參加祝壽會的辛苦可想而知。他念舊誼,重情義,不言之中飽含著對同事的感情。
我回想起2005年5月25日,經(jīng)濟學院慶祝建院20周年(1985年由北大經(jīng)濟系改為北大經(jīng)濟學院)。石先生作為第二任院長,曾對經(jīng)濟學院的學科建設(shè)和人才培養(yǎng)作出重大貢獻。那天,他扶病前往,也是深色的西裝,也是鮮亮的領(lǐng)帶,同樣一絲不茍,神色莊重。他端坐主席臺,主持人孫祁祥教授請他發(fā)言,他擺手,仍舊是一言未發(fā)。我在下面,看到石先生端坐在那里,不禁眼濕。
2011年9月11日,我和丹莉、馮楊、周呈奇博士夫婦、顏敏博士等到石先生家看望。石先生看到大家很高興,拿出他收藏的很多印章還有他自己的印章給大家看。當我摩挲把玩先生上個世紀60年代所刻的一方雙面印時,石先生說:“曙光,這個印送給你吧。”我受寵若驚!這方雙面印,當屬先生作品中之精品!此印一面刻“百舸爭流”,一面刻“江山如畫”,先生將此印贈我,可見對我的厚愛!那天,石先生讓師母把我曾寫給他的對聯(lián)拿出來給大家看。那是我2010年寫給先生的一副聯(lián),里面嵌了先生的名字:“石間流水,奇士能賞;世外桃源,隱者可居。”石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奇士,可是他雖深居簡出,卻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隱者,他對弟子們都非常關(guān)心,也極為關(guān)心學院的發(fā)展。我將新著《金融倫理學》呈先生教正,他翻看著,連連稱贊:“看來是你獨創(chuàng)的學科,了不起啊!”對我鼓勵有加。不久之后,師母和石先生就雙雙住院了。
2011年10月2日下午我去西苑醫(yī)院高干病房看望石先生。因為我正在整理與經(jīng)院院史有關(guān)的材料,他特別關(guān)心100周年慶典的籌備工作,跟我談起陳岱孫、熊正文等先生的舊事。他說上世紀60年代初期他曾與陳岱孫先生及厲以寧先生同開《古代漢語》課程,選《孟子》、《史記·貨殖列傳序》、《鹽鐵論》等有關(guān)古代經(jīng)濟思想的文章來教學生。他的病床邊放著《宋詩一百首》,是上世紀60年代的舊版,書頁已經(jīng)有些泛黃,可見石先生在病中還看這些書解悶兒。endprint
此后我就再也沒有見到石先生,只是通過龍桂魯兄(石先生的女婿)時時打聽先生的病情。2012年2月1日,龍桂魯兄通過我給院里發(fā)來一封石先生的信。在這封信中,石世奇先生談到1977年以來主持北大經(jīng)濟系工作的五點體會,信的最后寫道:“祝北大經(jīng)濟學院越辦越好,人才濟濟,成為全世界最好的經(jīng)濟學院。石世奇(80歲)于病榻上。2012年2月1日。”
這篇提綱性的文章,雖然簡短,卻浸透了石世奇先生對北大經(jīng)濟學院的深厚感情。其中總結(jié)了“文革”以后他主持北大經(jīng)濟系工作的若干重要經(jīng)驗,這些原則對于北大經(jīng)濟學院今天的發(fā)展都是非常寶貴的。1988~1993年,石先生又擔任了5年的院長職務(wù),對經(jīng)濟學院的學科建設(shè)和人才培養(yǎng)作出了諸多貢獻。石先生在生前病體極為虛弱的情況下還念念不忘經(jīng)濟學院的發(fā)展,其人格境界令晚輩欽佩,其中所飽含的深厚情感令人感動!
2012年2、3月間,我忙于編輯《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院(系)百年圖史》,龍桂魯兄發(fā)來石世奇先生親自挑選的若干珍貴照片,我都選入了《百年圖史》一書中。在編輯《百年華章——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院(系)一百周年紀念文集》時,我收入石世奇先生2005年寫成的一篇回憶文章《兩進北大經(jīng)濟系》,以及他在1995年為慶賀經(jīng)院建院10周年而寫的文章《興旺發(fā)達,方興未艾》。我心里想著,等5月份《百年圖史》、《百年華章》兩本書出版之后,我就給先生送去,讓他老人家高興高興,以此來慶祝他的80大壽!可是,就在我們緊鑼密鼓籌備百年慶典的時候,2012年4月6日上午11時,石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距離我們舉辦百年慶典只差50天!他剛剛滿80周歲,可是我們這些弟子們卻再也沒有機會為先生舉辦一場祝壽會了。我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頃聞吾師石世奇先生逝世,不勝悲痛!余自一九九四年得識先生,十八年來常得先生教誨,雖未入門,然得益于先生甚多。師之教恩沒齒不忘。師品格清奇,有古人之風范。即之也溫,不怒而威,溫文爾雅,氣度從容,而自有尊嚴,望之令人肅然起敬。先生于名利處之淡然,廉潔奉公,律己甚嚴,主持北大經(jīng)濟系數(shù)載,上下皆稱道。處事貴公,做人謹飭,如松如柏,亦莊亦穆,有藹然長者之風。其于學術(shù)數(shù)十年孜孜以求,獎掖后學,不慕虛名,惜墨如金,凡所著述皆經(jīng)得起推敲。今先生仙逝,學界少一敦厚長者,吾失一至尊師長矣。”
2012年4月10日,在陰沉的天氣里,數(shù)百弟子與同事為石先生送行。我寫了一副挽聯(lián)以悼念先生:
石品清奇,德炳士林,一代師表恩澤厚;
道骨傲岸,學究天人,三千桃李懷思長。
這一天,久旱不雨的北京城竟然下起了小雨。(作者為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