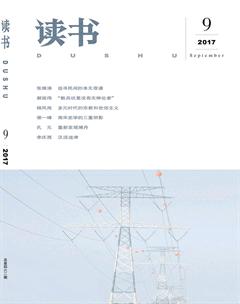后上官婉兒時代與馮道的歷史世界
李丹婕
數年前陸揚先生曾在一次講座中舊題新論,探討“安史之亂”后唐帝國受到重創卻何以得以長久延續。他指出,“安史之亂”后數十年間,唐廷經歷了漫長的調適期,其中包含多次轉折和多項變革,但調適趨向在德宗朝逐漸明晰,到憲宗朝末年基本落定。中晚唐雖然延續藩鎮林立的局面,但“宣宗和懿宗時代,幾乎所有藩鎮都是文官節度使,但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官,而是一個唐朝中央系統培養出來的清要官員”。這一看法實已提到陸揚新著《清流文化與唐帝國》一書的兩個關鍵詞:“中央”與“文官”,二者盡非泛泛而論,皆有具體所指。
“中央”指“安史之亂”后逐漸重構起來的制度化“皇權”運作模式,這一模式不僅使得中央行政運作更靈活,還衍生出無形而巨大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勢力,成為維系唐廷權威及唐廷與地方關系平衡的關鍵因素。實現這一結果的行為主體便是“文官”,特指那些代表朝廷或各級行政系統起草政治文書的官員,這些人的出現不限于中晚唐,卻在這一時期形成一個獨特的精英群體,即本書所謂的“清流群體”。作者強調,清流成員有著復雜的社會網絡和多重身份,通過相似的經歷而產生同樣的經驗,從而構成相應的價值取向和群體意識。這一群體自我生產的重要機制是科舉,身份認同的核心媒介是“寫作”;透過科舉與寫作,“清流群體”逐漸形成一股強大的“文化潛流”,最終在眾流激蕩的中晚唐世界“沖出峽口,釀成巨潮”。
若以“中央”和“文官”兩個關鍵詞看,本書主體內容即可分而觀之。前者由上篇前三篇專題論文集中闡釋,“中央”具體指第一篇《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論題中的“元和政治格局”,這一點在第三篇《九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以梁守謙和劉弘規為例》中得到進一步說明,“元和新政”“元和的新中樞格局”“元和時代內廷新格局”“元和新格局”“元和新中樞體制”等措辭稍異、內涵一致的表述反復出現。元和新型政治體制的確立與憲宗本人的個性及其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就性格來看,“憲宗是個個性極強而極有主見的君主,他從一開始就有重新建立新政治規范的意愿,也就是對節度使的任命必須有絕對控制權”;就時段而論,此前代宗、德宗兩朝一系列區域危機幾度給朝廷造成極大威脅,但同時也消耗了動亂發動者本身的力量,為德宗朝累積財政和軍事力量帶來空間,繼而成為憲宗朝提振皇權、施行新政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元和中樞新體制具有兩大特色,一是內外廷機構處于平行發展和合作的狀態,兩者不斷根據實際行政需要來界定各自權威的界限,居于這兩個系統之上的憲宗是最后的仲裁者;二是憲宗確立起真正以翰林學士為儲相的無形制度,并從他親自選拔的翰林學士中產生主持大政方針的宰相,輔之以元老重臣。這一觀察實修正了傳統關于中晚唐內外廷劍拔弩張,且外廷士大夫往往處于附庸的刻板印象。
憲宗及其同道得以確立這一新體制,是一系列歷史契機、政治謀劃和軍事實踐相配合的結果。元和初年先后發生的西川劉辟和浙西李锜兩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憲宗登基和西川實權人物韋皋的去世幾近同時發生,成為“劉辟事件”得以萌發的契機。作者對這一事件的相關記載做了層層解構,繼而從劉辟和憲宗兩個視角進行重構,讓“局外者清”的讀者得見“當局者迷”的復雜面相。當元和元年(八○六)三月三日劉辟在西川北池與眾僚屬游宴時,似乎對十多日之后憲宗措辭嚴厲地將他稱為“逆賊”的詔書毫無預感。這一強烈的戲劇性對照源于,在劉辟看來,自己有充分理由和條件接替韋皋成為新一任“西川王”,起初似乎也得到了中央認可。而剛登基的憲宗,卻已決心徹底鏟除劉辟從而改變貞元以來的積習,建立新的政治價值觀和運作規則。當收復東川后他意識到實行這一計劃的時機已然成熟,便果斷對劉辟事件進行公開定性,并佐以積極軍事行動,強勢確立中央對西川的支配權。李锜事件緊隨其后,具體過程和條件與劉辟事件稍有不同,但“事件”邏輯和輪廓幾近一致。結合李肇、柳宗元等同時期士人文章反映出來的關于若干當事者的曖昧態度,我們可以看出,與其說劉辟和李锜因叛亂而被剿滅,毋寧說,他們全無意識卻恰巧成為憲宗登基之后“借勢作法”劇目中的配角。無論是劉辟試圖實踐“貞元以來藩鎮擅權的慣有模式”,還是李锜欲演繹“韓滉故事”,都說明他們沒有及時領會憲宗布新革舊的思路,而如本書所全景展呈的,新的政治規范便在這種帶有誤解的雙方政治周旋中得以確立。
元和政局的核心在于皇權制度化和象征性的重建,在這一重建過程中,宦官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典型例子是元和時代相當低調卻至關重要的兩位,梁守謙和劉弘規,二人履歷和作用由幾份石刻材料留存,本書做了充分討論。梁守謙和劉弘規都是第一代入宮的宦官,“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源于德宗欲改革內廷、建立內廷新秩序的政治意圖和時代背景,這些進入內廷的宦官受到皇帝直接支配,穿梭在皇帝與翰林學士、外廷大臣、藩將節帥之間,在憲宗朝成為“元和新政的協調者”。無論是李吉甫與梁守謙之間,還是李德裕與劉弘規之間,都顯示出宦官與宰臣之間密切配合而非對立沖突的關系,由此二人成為平淮西、定淄青這“元和中興”兩大核心事件的中流砥柱。本書進一步強調,宦官在元和時代官僚化的發展趨勢,并非僅僅是各統治集團之間權力消長的結果,而是體現了憲宗力圖推行元和新政的具體實踐。
借劉辟和李锜事件憲宗成功重建中央對藩鎮的絕對權威,迫使藩鎮接受唐廷主導的游戲新規則;梁守謙和劉弘規的作為則反映了憲宗重塑皇權權威的具體手段。了然圣意且能力出眾的宦官,成為這一規則付諸實踐的具體代言人和執行者。在鉤沉“故實”的背后,本書還格外強調“輿論”這一曾切實存在于歷史現場,如今卻消失于文本記載的無形力量。
作者提到,只消體會韓愈作于元和二年的《元和圣德詩》的高漲情緒,就可以意識到,不用等到元和中后期平定淮西和淄青,憲宗中興之主的名聲在其登位之初已深入人心。實現這一點,除了基于平定“叛亂”的戰績,更得益于憲宗出現的政治輿論之“勢”,對地方實權派人物“心理上造成重壓”,比起軍事勝利,這一“心理因素”才是元和中興的首要貢獻。在分析梁守謙和劉弘規的歷史作用時,本書同樣注意這層無形的因素。無論是以“未曾為將相撰碑”自詡的李德裕為梁守謙親撰《神道碑》這一行為,還是《梁守謙墓志》直接將志主稱為“統握大柄”的“內相”,都反映出這些宦官在朝廷官僚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這些“無形的資本”終轉化為政治實力,成為重構元和新格局的重要動力。endprint
無論是憲宗的“勢”還是梁守謙的“威”,很大程度上源于各類文本的生產與傳播,而這些文本的制造者便源于本書另一關鍵詞—“文官”,或曰“草臣”“詞臣”。
本書下篇《唐代的清流文化—一個現象的概述》將這些官僚視作一個群體進行概觀,并試圖“通過分析八世紀后期到十世紀間書寫中記錄的唐五代政治精英的生涯軌跡及其成功資源,來找尋塑造晚唐五代政治文化及其代言人的種種無形力量”(213頁)。作者重新檢討了張九齡反對牛仙客拜相一事和唐末“白馬驛事件”,長久以來左右對這兩個歷史現象認知的是陳寅恪先生提出的科舉與門第對立的思路,本書則有不同看法。作者認為,張九齡對牛仙客的排斥與拒絕,并非基于門第出身,而是基于某種特殊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來自出色的文學才能、進士及第的資格和長久“踐臺閣,掌綸誥”的經歷,“在他(張九齡)心目中,這種憑借文學累歷清貫的經歷足以抵消地域、門第乃至制度意義上的官階帶來的身份優勢”,“他(張九齡)不僅強調文學這一素質的重要,還強調這一素質需要和特定的資歷相結合才能得到體現,這種資歷在中晚唐以進士詞科的成功和任官的清顯最為關鍵,形成一種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標準,實質上取代了原來以郡望或官品等為主的評判標準”(223頁)。這一觀念憑借科舉詞科,又形成了制造新成員的機制。那么,作為“清流文化”更新與延續保障機制的“進士科”的意義便可以進行再評估,一定程度上而言,這一制度在中晚唐不僅是為政府選舉人才,甚至可說創建了一個新的特權集團,以“文”作為身份判定的重要標準也相應具有意識形態的色彩,而這一發展趨勢與武后到玄宗時期君主獨裁體制的強化相同步,且未因“安史之亂”而中斷,反倒自八世紀后期開始,和唐帝國的統治策略、皇帝的政治角色、官僚體系的權力分配等日益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具有文化霸權性質的主流觀念,受到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人士的認同。隨著這一觀念的流布,除河北以外的絕大多數藩鎮已逐漸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節度使或觀察使所支配,這些高級文官很多屬于清流文化的代表。即便是德宗朝起自立傾向日益鮮明的河北地區,唐末也逐漸呈現“文治化”氛圍,反映了作為意識形態的“清流文化”無遠弗屆的輻射力。
本書運用“清流文化”這一工具概念,通過《上官婉兒和她的制作者》《論唐五代社會與政治中的詞臣與詞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資料為例》《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三篇文章,便串聯起一條“后上官婉兒時代與馮道的歷史世界”的通貫線索,有效彌合了通常印象中的“安史之亂”前后乃至五代、宋初之間的“斷裂”,沖擊了已近乎刻板化的唐宋變革論范式。
但也略有遺憾的是,對“清流文化”(文官)進行通貫性考察的同時,“皇權重振”(中央)的問題則聚焦于八世紀末、九世紀上半葉德憲兩朝,兩者在時段上稍有出入。在“清流文化”脈絡里作者給予上官婉兒以特別關照和重新定位,提到“在構建唐代政治中的‘斯文傳統過程里,曾經有過一個‘上官婉兒的時代”(282頁),作者也時或強調德憲兩朝是“清流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但論及這一階段時還是聚焦于權力結構重組與政治更新,談及元和中興,作者提到“元和既是憲宗的時代,也可以不夸張地說是李吉甫的時代”(58頁)。事實上,與李吉甫年紀相仿佛、同樣活躍于德憲兩朝且長期執掌科場牛耳的權德輿,或許恰可被視為此際“清流文化”的絕佳代言人,典型文本就是權德輿為德宗初年的詔誥手筆陸贄文集撰寫的序文。這篇名為《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見《權德輿詩文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八年版)起筆寫道“嘗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之后特別提及陸贄代德宗起草《罪己詔》一事,并強調“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在具體表彰陸贄的文章時,序文強調他能“搉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有《制誥集》十卷,公之為文,潤色之余,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而重新校勘編撰陸贄文章,目的則在于“俾后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這里權德輿不僅極力渲染陸贄制誥之于皇權宣威甚至超乎武力的重要價值,還具體強調了這些“文”的體式、特色及其楷模價值。身為三次知貢舉、門生多達數十人的科場領袖,權德輿如此態度與行為所發生的社會影響力不言而喻,無疑大力助推了貞元、元和時代“清流文化”的發展。有趣的是,權德輿謚曰“文”,且其父權皋與李吉甫父李棲筠同于天寶七載(七四八)進士及第,《李棲筠文集》序文便出自權德輿之手。
透過本書分析,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安史之亂”后唐廷有意采取的“文致太平,正名百職”,“以沉機銷急變,以尺牘柔獷俗”(權德輿語)的策略,不過對這一策略的實效性也需保持審慎。“文”所營造的畢竟只是一種象征性權威,在具備相當實力提振皇權的憲宗時代,以“文”為圭臬的清流群體得以制造出強大的輿論潮流加持這一“中興”勢頭,但當中央和地方實力權重發生變化時,這一群體不免淪為皇權的附庸,僅以頌揚想象中的皇權為務。中晚唐藩鎮文官化的發展過程看起來是唐廷對地方秩序的重建,但細究來看真正建立起來的,只是“地方官”的任命權,此舉導致地方“實權”的轉移,日益增強的在地化力量及相應產生的離心力最終成為唐朝趨于瓦解的動因之一(詳參李碧妍: 《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版)。這也是何以唐末出現一個吊詭的現象,即盡管九世紀唐廷對帝國的實際控制力在減弱,以大明宮為中心的文化想象卻反而呈現上升的趨勢。這一現象曾為詳細考察過唐朝科舉禮儀的妹尾達彥先生所特別指出:“到唐末,及第禮儀從五月延長到六月,成為花費很大、持續數月的節日活動,而且這一禮儀有個特點,即在政治極度混亂的唐代末期,反而更加完備,越是這樣的時代,科舉越必須每年定期舉行,及第禮儀的形式也就更完善,也更有必要舉辦得華麗了。唐末科舉,與其說是通過補充新官僚來強化官僚制度,不如說是成了一種維持國都象征性中心的禮儀,并作為統合長安城市民眾的節日活動而發揮著作用。”(妹尾達彥:《唐長安城的禮儀空間—以皇帝禮儀的舞臺為中心》,黃正建譯,收入溝口雄三、小島毅編《中國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490頁)endprint
本書非常注重對文本及其書寫實踐的解讀,作者基于對中西方人文學術脈絡的批判性把握,得以游刃有余地運用有效的工具概念對各類文獻進行深層解剖,剔除其中價值判斷的因素,清理出史實敘述的成分,再以力求精確的敘事還原宏闊而復雜的歷史面目。這一研究實踐特色,一方面相當鮮明地反映在本書對傳世文獻的剖析中,如對《李相國論事集》相關史實的辨析便極其精彩,以《憲宗實錄》為代表的憲宗朝相關歷史文本的生產皆與政治斗爭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使用時尤其需仔細玩味書寫背后的“意圖”;另一方面則格外突出地表現在對出土墓志的多視角審視上,這一點除散見于各篇的具體論證,其方法論層面的思考還可參考收入本書的長篇書評《從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為中心》一文。
注重文本深耕細讀之余,本書還格外看重書寫、文類及其與政治權威的關系,認為中晚唐政治文化精英對日常往來于上下級和相互之間的文辭的強調與文藝復興時期對修辭學的作用的強調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書寫形成的意義世界并非其所屬客觀世界的鏡像,反而成為人們感知客觀世界的濾鏡,權力借助文字得到象征性展示,而這一展示又會影響人們的意識進而左右人們的判斷、選擇和行為;由此,本書對“書王命、知制誥”這一中晚唐具有政治修辭學意義寫作實踐的重視是深有價值的。
這種實踐在中央表現為學士代擬王言的詔誥,在地方藩鎮則表現為掌書記撰寫的表狀箋啟。這些誥命類作品在時人看來是“一朝言語,煥成文章”(白居易語),卻在后世逐漸為人所忽視。吳麗娛先生梳理表狀箋啟等應用型文類的源流,分析中晚唐五代這類文書集中出現的政治動因和時代背景時提出,中晚唐各種表奏集往往由掌書記親自制作,其中文書雖多是公事應酬,對個人而言并無意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從上至下,從朝廷到地方,表狀箋啟的官文書信也是所謂大手筆、大文章而受到重視,被唐人當作個人成就,看待它們并不下于詩詞歌賦,有些甚至還常常被作為可以炫耀的資本和供人學習模仿的榜樣。”(吳麗娛:《唐五代表狀箋啟書儀》,見《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商務印書館二○○二年版,92頁)本書進一步延續這一觀點,并將之納入政治史研究脈絡,可說極大拓展和溝通了中古文學和史學的文獻范疇。這樣,一些在文學史領域不受重視,又在政治史脈絡中見“事”不見“文”的人就有了被深入探討的余地,如中唐重臣令狐楚,以駢文見長,著有《表奏集》十卷,他不僅被同代人譽為“一代文宗”,死后謚號和權德輿一樣,亦曰“文”,其文才與治才都值得在本書所構建的歷史脈絡中進行重新評估。
這讓我想到唐長孺先生的名文《論南朝文學的北傳》(《武漢大學學報》一九九三年第六期),這篇文章詳論駢儷文在有唐一朝強韌的生命力,結語指出“古文倡于唐之韓、柳,重興于宋之歐陽修,而成于王安石之進士科試經義”。這個時間點和本書兩處論斷不謀而合。其一,“清流文化”進入五代得以延續還有一重要途徑便是五代文人有目的的回憶性書寫,這些寫作趣味和立場往往和官修《舊五代史》相當一致,而和歐陽修等撰的《新五代史》大相徑庭;其二,“清流文化”與北宋初年的政治規范建立存在密切關系,而到“長達四十多年的仁宗一朝終于出現了明確的轉向,曾經被視為超越政權而存在的那種維系政治文化的力量,開始淪為道德譴責的對象”。單就作為文章體式的“駢儷文”來看,自六朝到北宋,呈現出一個超乎尋常的長時段歷史和不可思議的生命力,由此作者開篇提及,將在本書基礎上繼續撰寫一部專著考察“從南北朝到五代文與政治”,相當令人期待。
(《清流文化與唐帝國》,陸揚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