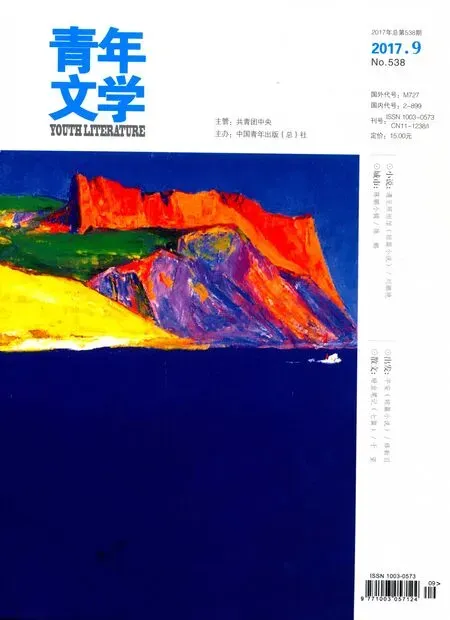平 安
⊙ 文 / 修新羽
平 安
⊙ 文 / 修新羽

修新羽:一九九三年出生,青島人,目前就讀于清華大學(xué)哲學(xué)系。作品散見于《芙蓉》《大家》《解放軍文藝》等刊。曾獲第十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二〇一三年度《解放軍文藝》優(yōu)秀作品獎。出版有小說集《死于榮耀之夜》《年輕時我們向陌生人奔去》。
一
我仿佛永遠(yuǎn)都站在那張病床前。她的臉定在枕頭上,眼睛緩緩睜開,再緩緩合起,仿佛這些動作并不是出于個人意愿,而是受控于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走吧,”父親突然說,“回家。”來了不到十分鐘,他就領(lǐng)著我走了,路上什么都沒說。在車?yán)锼蜷_了窗,以免水蒸氣凝結(jié)起來遮擋視線。駕駛座那邊的窗。寒風(fēng)猛烈地拍在他臉上,然后四竄到我身邊。這就是他們對我的回應(yīng),哪怕我說的完全真實。
那天晚上我對剛做完手術(shù)的母親說:“我真羨慕你。”羨慕她被深愛自己的人探望,羨慕她無所事事地躺在床上,羨慕她正在康復(fù)。她總在康復(fù)。而我在復(fù)習(xí)期末考,這場考試的成績占自招推薦排名的百分之六十,我晚上總是不敢睡,也睡不著。可她絲毫也不明白,我們永遠(yuǎn)也無法互相明白。“我們”,是指所有人。
我仿佛也永遠(yuǎn)站在那間教室里。肯定是初春,光線灰白,從窗外洶涌到我們身上。需要微微低頭,盡可能溫和而謙遜地介紹自己。需要戴著手表,用笨重的帆布表帶掩蓋傷痕,或解釋傷痕。沒人知道我前一天晚上把自己關(guān)進了房間,母親在門外咒罵我除學(xué)習(xí)之外一無所知,而我邊看書,邊用指甲劃過手腕。
那天晚上我覺得自己是場漂浮不定的夢,中了什么詛咒才化為人形。那天晚上我覺得自己有無休無止的耐心和義無反顧的決心,為了證明這點,不得不用指甲輕劃手腕,劃過人們慣常用刀劃過的地方。最初無關(guān)痛癢,隨后是白痕,發(fā)熱,最后皮膚一小塊一小塊地掀起來。它們并不連貫,被那條紅腫的線串起。兩百四十五次。對我而言,兩百四十五次。
我沒幫母親洗過碗拖過地。但我在那場答辯考試中排名第一,拿到了市級三好學(xué)生的獎項,能在中考時加五分,足夠母親向親戚炫耀。這讓我覺得自己虛偽得天衣無縫,熠熠生輝。這讓我沾沾自喜得像是躺在金棺里的尸體,等待著或許永遠(yuǎn)也不會到來的復(fù)活。
無論何時,但凡回憶往事總是這兩個場景最先出現(xiàn),久而久之就帶有隱喻的味道。這是我生命中最初落下且永不消融的大雪,這是夜晚,這是我為什么對自己被診斷出的抑郁癥無動于衷,終日長睡不醒。
二
冬季漫長,十月中旬就出現(xiàn)冷空氣,月末就降雪。雪花被攢在樹葉上,風(fēng)一過就落一陣。所以我們有著充足的理由每天都躲在宿舍里,到中午才下樓去拿外賣。
我和陳平安都是這樣的。我有十五學(xué)分,她只有十三,還把課都安排在了周一周二,還總是翹掉大半。點名的時候,就托同學(xué)遞上假條。我們成績都不算突出,卻都已經(jīng)在本校保了研,這學(xué)期萬事無憂。
我們每日每日相處在一起。并不吵架,甚至并不交談。
中午醒來后我一直躺在床上,覺得臉上很燙,就起身去洗了臉。沒什么用。
鏡子里的那雙眼睛,眼白依舊微微透藍。我看過書里的形容,說這是嬰兒藍,是最清澈的眼神。其實是固膜發(fā)育不健全的顯癥。人們總是用詩意掩蓋病態(tài),用多情掩蓋病態(tài),人們都有病。福柯相信,所謂人類的文明史,不過是一場理性對瘋癲的勝利,人們把瘋子和真理一起禁錮到精神病院里。
“現(xiàn)在生活壓力大,很多人都有輕度抑郁。”父親說。視頻窗口上,他沒在看我,而是盯著屏幕上的某處,可能在查閱抑郁癥的資料,可能在隨意瀏覽什么新聞趣事。他那么漫不經(jīng)心,就像在談?wù)撀放缘幕ㄩ_了,或樓下的流浪貓死掉了。
我早就不想每天都和父母視頻。并沒有什么好匯報的,翻來覆去說出口的也都是些沒滋沒味的句子。可這整件事情就是有種慣性。想要它停下來總要付出代價。
十二歲那年,母親坐在地上抱住我的腿,把眼淚和鼻涕抹在我褲子上。她以為我想跳樓,其實我只是想從陽臺翻到消防通道,繼續(xù)玩離家出走的把戲。她用胳膊緊緊箍住我的腿。她很痛苦,我也是。但一個人如果僅憑痛苦就能得到原諒的話,這世上的仁慈未免也太多了。
我無法行走,只能低著頭去看她,不明白自己為什么陷入這樣的荒誕。我不知道電視劇里演的事情真的會發(fā)生,而且真的會有效果。我無法行走,只能聽著她的哭聲。一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我的生活被偷走了,而這個世界的上帝喜歡看情節(jié)庸俗的悲情劇,所以我們只能演下去。
我低著頭看她,讓她放手。她不說話,反而把胳膊抱得更緊了些。我們保持不動,就那樣僵持了很久,直到她把所有眼淚都擦干凈,而我精疲力竭地回到自己房間。在這樣的生活里,誰都會抑郁,生活本身就是抑郁。
“我就是要去醫(yī)院看看,覺得校醫(yī)院不夠權(quán)威。就是簡單地檢查了一下,居然就給我開藥了……根本就不敢吃。”我看著父親,盡可能平靜地結(jié)束對話。
外面安靜,昨晚下了一場很大的雪。陳平安沒有繼續(xù)窩在床上寫論文,而是坐到桌前看著什么書。陽臺對面是男生宿舍,我們從來都整日整日拉著窗簾,房間里永遠(yuǎn)昏暗。她的臺燈是一盞濕漉漉的光線,不由分說地灑在她身上,暖黃。
從水房回去,宿舍里的燈已經(jīng)開了。陳平安倒還坐在原處,像是根本沒起身過。
“你起來啦?”過陣子,她才終于開口,懶洋洋地朝我轉(zhuǎn)過臉來。她是南方人,膚白而豐腴,慵散起來就像是西方古典油畫里的女子。這是句毫無必要的話,唯一的價值就是破壞掉我們之前那種微妙默契。“今天好些了?”
我點點頭,重新回到床上。那些困倦仿佛是某種沉淀在腦仁深處的物質(zhì),但凡運動或思考,都會讓它們彌漫開來。
三
校醫(yī)院的精神病科只在周二和周五出診。
昨天人很多,醫(yī)生說拿藥的先進來,問診的再等等。于是他們蜂擁而前,又蜂擁而去,很快就只剩下我一個人。醫(yī)生讓我進入,關(guān)上門。
“多久了?”她把嘴巴扯出微笑的形狀,眉毛卻皺著,語氣里有著遲鈍的關(guān)切,就像我不是生病,而是未婚生子。
“三個月。”開學(xué)了三個月。假期里我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亂想。從小學(xué)開始,年復(fù)一年,假期是重新洗牌,是終結(jié)。
“你覺得這影響到你的生活了嗎?”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生活。”
“經(jīng)常會考慮生和死的問題嗎?”
——是我主動走進了這間診室,請求別人干預(yù)自己。所以我就不能讓他們滾出去,把門關(guān)上。我只能坐在那里回答問題。不確定自己要回答多少問題。也可能需要治療的是其他人。然而我選擇了接受治療,選擇相信自己的不正常。
“經(jīng)常考慮,但僅僅是考慮。”我說,“我是哲學(xué)系的。”
她看到我的表情,就從抽屜里拿出了一張測試單,說是可以做測試來參考。上面的每個選項都標(biāo)記了各種分值,花花綠綠,更像是科普性質(zhì)的心理健康自測手冊,或者什么保健品廣告。
我應(yīng)該對自己誠實。我故意不看那些分值,很快地填寫完那些表格。數(shù)值是從1到6,從“幾乎不”到“持續(xù)”。為什么要回答這些問題?或許她并沒對我誠實。或許她只是個水平有限的中年醫(yī)師,根本就沒資格開出任何藥劑,即便她能開。或許她根本不在乎我會講些什么,只在乎我說話時的語氣和神情。
我把表格交還給她。她數(shù)了一下分值,在輕度抑郁的選項上打了勾,然后給我開了兩盒百憂解。聽起來像是安眠藥,或者毒藥。除了睡眠或死亡,我不知道還有什么能夠解決掉憂愁。我把藥帶回寢室,小心地藏到柜子里。
“你去哪兒了?”陳平安問我,漫不經(jīng)心地問我。
我想說遠(yuǎn)處有召喚我的東西。可我不能說謊。
“校醫(yī)院……不太舒服。”石頭落下了,一切理所應(yīng)當(dāng)。
那天晚上陳平安始終在宿舍里,能聽到我對母親做出的所有坦白。每天吃完晚飯的時候,倘若我在宿舍,就要和母親視頻聊天,匯報一天的生活,并且接受她的關(guān)心。她說如果我很忙的話就沒必要這么做,可是在我不去找她的時候,她總會主動來找我。
母親是師范大學(xué)的函授學(xué)生,來北京讀過一年書,學(xué)體育教育,課目里應(yīng)該有教育心理。她總覺得自己既明白人體又明白人心。
“你就是缺乏鍛煉,要多出去跑步。”她很篤定地囑咐我。
“不行。”
“去食堂按時吃飯,不準(zhǔn)叫外賣了。”
“不行。”
她一項一項提議,我一項一項否決。
“那就早點兒回家吧。”她說。她即將被激怒了。
我關(guān)掉視頻窗口。
宿舍里安靜下來,才聽到陳平安在笑。是那種惱怒的,故意發(fā)出的冷笑。
“怎么,”她說,“你怎么什么都沒說?”
“早晚你也會知道。”
“如果你非認(rèn)為自己有病還希望別人都能體諒的話——”陳平安的話故意突兀停住,像是一只不斷下落的杯子猛地撞在地上破碎那樣突兀地停住。
陳平安的視線沒從電腦屏幕上移開。她能否看清楚這個世界正在發(fā)生的一切?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在看著他們看不清楚也無從理解的東西。那么多人正在看著。我不想走在他們的視線里。我沒有解釋。于是沉默將我們淹沒。
那天晚上我依舊是凌晨三點才入睡。陳平安早早就上床了,她備好了耳塞,眼罩,香薰機。她總是準(zhǔn)備好了所有利于入睡的東西。雖然她總要花費很久很久才能真正睡著。
第二天,我依舊是上午十一點才起床。我查閱了很多資料,似乎科學(xué)家們對這種睡眠時長不變、睡眠時間整體延后的情況各有看法。我和陳平安討論過這件事,她給出了許多不同的答案。認(rèn)為不愿出門是對自己的要求太高,不想破壞自己在別人心里的形象,所以不敢冒任何風(fēng)險。認(rèn)為作息混亂的根源在于懶惰和拖延。認(rèn)為我在尋求存在感,擺脫負(fù)罪感。人們無法互相理解。人們看到聽到想到的一切都是謬誤。
然而我只知道什么是錯誤。我給不出答案。
陳平安就繼續(xù)裝作什么都不知道。我裝作什么都沒有發(fā)生。
四
在我小時候,母親經(jīng)常加班,不得不把我也帶去。那是個橡膠廠。那時候,我只能看出這是個黑色工廠,黑色的巨大機器,黑色的車間,沒有被打掃的地方都落上層黑色塵埃。唯一干凈的是那些工人,在上班時干干凈凈地來,下班后洗完澡又干干凈凈地離開。
我讀小學(xué)的時候,她離開了那座工廠,考慮著繼續(xù)去當(dāng)小學(xué)老師,可是當(dāng)老師已經(jīng)需要拿到“教師資格證”。有段時間,我回家時總能看到她趴在書桌上看書,可后來還是沒考上,她也不打算嘗試第二次。
我不知道她的其他人生經(jīng)歷。在很小的時候,我沒想過問,聽到了也不能理解。年紀(jì)大些之后,我還是決定不問,她就更加不會主動地說。因為我考上了一所好大學(xué)。
在我小時候,我的一切優(yōu)良基因都來自于她的遺傳。但我和她不一樣。
非要說的話,我和陳平安才是同樣的人。我們從來都比身邊的其他人更聰明,從來不指望得到什么真正的理解。老師用自己的方式來鼓勵、管理學(xué)生,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裝作被鼓勵,被哄騙,被井井有條地管理。我們成摞成摞把獎狀拿回家,留下原件和復(fù)印件,隨時準(zhǔn)備著來證明自己的優(yōu)異。
母親以脾氣暴躁聞名。她喜歡在旁人面前罵我,有些時候還會動手。我必須哭,而其他人會把我拉到旁邊的房間去安慰。他們會告訴我,母親很愛我,甚至常常在旁人面前夸贊我。他們覺得這說明母親很愛我。
我只能勉強理解她,耐著脾氣和她相處。有時候我看著她,不知為什么就會哭出來。她不會安慰我,反而會冷靜下來,神色里帶著悲憫。
一個病人能否意識到自己需要醫(yī)治?
我的母親,她自己就是萬物的標(biāo)準(zhǔn),萬物的尺度。
撕我書的是她。因為覺得都是“閑書”,是不務(wù)正業(yè)。父親的解決方式是,把書頁重新黏好,重新放到我桌上。這就是他們相處并對抗的方式。他們吵過架,有次父親喝醉了酒,正在陽臺上吃梨。念念叨叨的是她,而父親把梨朝地上猛地一摔。家里安靜了。果肉在瓷磚地上碎著,也沒人去收拾。如果是在地板上碎的,母親或許還會勤勞些……但瓷磚并無大礙。
等父親醒了酒,這件事已經(jīng)人盡皆知。“他摔了一個梨,摔得稀巴爛。”母親不去想這件事聽起來有多好笑。“他想動手打我了。”這就是他們相處并對抗的方式。
有那么幾次,我坐在地上哭,而她闖進屋里沖我指指點點。她總是無比真誠,語調(diào)高亢,咬字清晰,臉上漲得通紅,就好像生出我來是她命中注定的最大不幸。我不能反對她以顯得叛逆,也不能順從她以顯得譏諷,還不能沉默不語……有次我打定主意沉默不語,而她整整罵了半小時,越說越生氣,最后沖進來拿拖鞋抽打我。不疼。我也不知道該不該表現(xiàn)得疼。
就像任何普通的家暴一樣。傷害,彌補,傷害。
母親會愧疚,會做我喜歡的飯菜,會不再干涉我的閱讀和寫作。她會說服自己這都是因為太愛我,她對此深信不疑,并且要求我也深信不疑。
我試過做家務(wù),只會給她更多的機會嫌棄我笨手笨腳。她總覺得我應(yīng)該早就什么都會,像她一樣……她十歲就開始給家里做飯了。我不能說那些飯菜不好吃,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則就是對她的嫌棄。“辛辛苦苦給她做的飯,吃兩口就走了……”她會在我背后嚷嚷。“我伺候她都不行,還指望她能伺候我?養(yǎng)了這么個孩子我覺得丟人,我沒指望過要她一分錢。”而我沒指望過拒絕。
她會在和我視頻的時候落下淚來,說實在太想念我。
我把這些事情都講給陳平安聽了。她還是坐在自己的桌前,做那些永遠(yuǎn)也做不完的文獻梳理。左手邊攤開了好幾本書,空白處用鉛筆寫滿了批注。
我盯著她的背影看了一會兒,才用“其實我和父母的關(guān)系一直挺不健康”來開場,非常拙劣的開場。陳平安轉(zhuǎn)過身子來看我,像游客看被困在動物園里的動物。
我早就已經(jīng)變得正常了。至少沒再有什么小心翼翼的、無法克制的行為。
初中的時候,每次上床睡覺前我都要把拖鞋擺成一定角度。父母覺得我關(guān)燈很磨蹭,催促過幾次。后來有一天,我正在擺弄的時候,發(fā)現(xiàn)父親站在門口。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讓這雙鞋變換擺放的位置。
父親盯著我。我不知道他目光中有些什么。他走過來,故意朝那雙拖鞋踢了一下。千鈞系于一發(fā),那根頭發(fā)斷掉了。他關(guān)上了燈。可這雙拖鞋不能就這么放在地上,我把它們拿起來,塞進被子里。早晨去洗漱的時候,牙刷擺放的角度也變化了,和昨晚不一樣。就好像一具被人擺成古怪角度的尸體,它的骨骼肯定已經(jīng)斷掉。昨晚我特意把漱口杯擺在不容易被碰到的地方。
“你在那兒做什么?”父親問。母親沉默地忙碌著早餐,她很明白父親究竟在問什么。我在與我的強迫癥和平共處。而他們會一次次提起這件事,會讓我承認(rèn)自己有精神病……然后以這個病癥為理由,接管我的整個人生。因為我會是病態(tài)的,錯誤的,并且永遠(yuǎn)是病態(tài)的,錯誤的。如果不承認(rèn)就得不到治療。如果不承認(rèn),就得不到救贖。
“刷牙。”我慢慢拿起牙刷,把它塞進嘴里。
那段時間我常常睡不著覺。
我開著燈整宿整宿地看書。裝作是在看書學(xué)習(xí),其實什么都看。看笑話選集,歇后語大全,中藥偏方集錦。我看家中所有印著字的東西,乃至洗發(fā)水背后的產(chǎn)品說明。就好像這是一場漫長的準(zhǔn)備,有劫難等在未來,而我毫無辦法,只能盡可能地,徒勞無益地,通過大量而豐富的閱讀來做準(zhǔn)備,試圖從任何瑣碎信息里找到關(guān)于末日的線索。
陳平安的初中生活不是這樣。她所在的那所外國語學(xué)校要求嚴(yán)格,從初中就開始住校。圖書館有整整四層樓,負(fù)責(zé)選購書籍的老師是常青藤碩士。她的兩個室友曾經(jīng)一熄燈就躲到同一張床上,發(fā)出窸窣聲響,像是皮膚之間在互相摩擦。而她那時候就準(zhǔn)備好了耳塞和眼罩,每天很早就睡下,很早就起床,捧著復(fù)讀機去天臺讀英語。
陳平安至今還會早起。有過那么幾次,她還買了早餐放在我桌上,雖然我常常要在中午才醒來。我猜她會感到憂慮。但無論如何,至少我堅持去上了周五傍晚的那節(jié)課。六十多歲的老教授須發(fā)皆白,一板一眼地給我們講解童話。他用一輩子來研究那些外國童話。
出門前我對陳平安說,天空是湛藍的,一切都很好。
前些日子下的雪已經(jīng)融化了,“紅塵苦海”成了具象化的詞語,人們并非在前行,而是在渡越。雪化了又結(jié)冰,路上就很滑,我小心翼翼停好車,踩在潮濕的雪花上,覺得自己應(yīng)該跪下,或者躺下,應(yīng)該盡可能多地浸透在冷水里,因為寒冷會讓人清醒。讓人想起《皇帝的新衣》,匹諾曹,或者類似的童話。他們的鼻子應(yīng)該變長,他們在說謊。
我也在說謊。
五
在那個十二月中旬的晚上,人們成群結(jié)隊地去操場上看雙子座流星。
幸或不幸,又趕上了超級月亮,月朗星稀。但還是看得到流星,證據(jù)是那些間或傳來的歡呼聲。那些聲音很模糊,一切都很模糊,像是站在湖底仰望到的太陽。
我在樓頂上坐了很久。我的書包里有一把刀,有幾盒不同種類的藥。不需要認(rèn)真查過藥劑學(xué)資料,只要盡可能多盡可能雜地服藥,死亡的概率應(yīng)該也不會太小。
也就是說,今天晚上我和三種死亡的方式一起坐了很久。
無數(shù)種可能性凝聚在我周圍,就像我坐著的這個水泥臺階一樣堅硬,冰涼,而真實。無數(shù)種未來凝固在我周圍,它們都在等待著。而我不去選擇,我像是被藏匿起來的尸體一樣,被困在水泥里,束手無策。
畢達哥拉斯說死亡是靈魂的暫時解脫,德謨克利特說它是自然的必然性。蒙太涅宣稱預(yù)謀死亡即預(yù)謀自由,向死而生是人的自由原則。塞涅卡說它是我們走向新生的臺階。黑格爾說它就是愛本身。海德格爾說只有它才能把“此在”之“此”帶到明處。霍布斯說“死亡”是首要的、最大的、至高無上的邪惡。
死亡是生命的絕對他者。薩特說,他人即地獄。
回到宿舍后,燈是亮的。沒有人。其他兩個室友都去圖書館自習(xí)了,要到十點多才回來。
陳平安的電腦還開著,書攤在桌上。那是本《說文解字》,為了做畢業(yè)論文,她打算從頭再看一遍。攤開了放在桌上。直到晚上她還沒回來,我們才發(fā)現(xiàn)她是早就上床了。
后來才發(fā)現(xiàn)她是死了。
我們爬下床,打開燈,陸續(xù)去洗漱,下午一兩點才發(fā)現(xiàn)怎么喊她都不醒。我站在爬梯上掀了她的被子,捏住她腳踝晃了晃。她還是沒有起,又折騰了很久才意識到她是死了。她的腳踝很涼。這是一個很冷的冬天。
輔導(dǎo)員和形形色色的人都來找我們談話。
我把那些藥和刀都收拾了起來,裝在書包里偷偷帶出了宿舍。如果我死在此時是否合情合理。是否是畏罪自殺。是否是從眾心理。他們會怎么看我,你會怎么看我呢,母親。
我們的宿舍被封鎖了起來。學(xué)校給我們在留學(xué)生公寓那邊騰出了一間臨時居所,我們回不去了,所有復(fù)習(xí)資料都取不出來。已經(jīng)到考試周了,學(xué)校說在成績上會給我們一個保證。而我們在所有社交軟件上都守口如瓶。
六
陳平安的桌上留著寫滿字的紙,不是遺書,我沒有仔細(xì)看。
另一個室友說,抄的是《太上感應(yīng)篇》,還沒抄完。我能背出那篇文章的開頭:“福禍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這段話我們聊起過,那時候我們上大一,還在老先生的課上讀《左傳》,陳平安給我寫過的明信片還被當(dāng)作書簽夾在《左傳》第一冊里。豎排繁體,中華書局,我們讀了整整一學(xué)期,看著那些家族起落興衰,直到魯國十二公中的最后一位,哀公,終于薨了。我們看著歷史在自己面前呼嘯而過,每個人都死了。
明信片上的字跡還是過去的樣子,還是她死之前的樣子,字跡不會變化。可我們會。在這個世界上我又比她多待了一天,今天有霧霾,她不會知道。整個北京陰沉沉的,天空是土黃色,空氣是煙塵的味道,世界正在被焚毀。
德里達認(rèn)為意義永遠(yuǎn)也不可能在場,一個要素永遠(yuǎn)只能通過指涉另一個不在場的要素才能包含或傳達意義。索緒爾說語言中沒有任何出發(fā)點,或者任何固定的參照點。
我們開口說話,談?wù)摰牟⒎鞘钦胬恚瑓s接近于真理。談?wù)摰牟⒎鞘翘摕o,卻接近于虛無。
后來,他們說陳平安才是得了抑郁癥的那個。父母離異,小學(xué)時離家出走,初中住校后試圖自殺過好幾次,升到高中后才好了些。她什么都沒跟我們說過。她和我一起,成天成天地待在宿舍里,成摞成摞地看書,聽音樂,點外賣,安然無恙。
在某些時刻,安然無恙不過是一種感覺,與事實無關(guān)。
我想著陳平安的背影。她坐在寫字臺前,背對著我。像她這樣豐腴的人,脊椎上的骨節(jié)卻還是會隔著衣服透出來,綽約可見,弧度優(yōu)雅。她總是坐在那里。而我在床上倚著墻寫作,寫不下去的時候就在宿舍里隨意瞥幾眼。陳平安總是坐在那里,就好像她能巋然不動地等待一萬年,完好無損地等待一萬年。就好像她心里沒有什么東西在慢慢碎掉。
她離開了而我還在這里。人們總覺得另有緣由,卻不肯相信一切都是出于幸運。
“我想回家一趟。”我告訴父親。我自己買了票。視頻里的我和平常看起來的似乎不太一樣,仔細(xì)想了想,才意識到是背景變了。出現(xiàn)在我身后的不再是陳平安的床簾,而是光禿禿的石灰墻,白色的石灰墻。
“你再查查是幾點,確認(rèn)了嗎?”
九點,九點五十五分,我已經(jīng)告訴過他三遍。
“截圖給我看,你別記錯了……你總是做這種事。身份證記得帶。”他總是做這種事。
這就是為什么我會對自己的父母如此厭倦。陳平安,我知道答案了。有些事情持續(xù)了太久,所以之前我們都忘記了。
七
很小的時候,我們會在外面玩捉迷藏。像我這樣的人總喜歡占規(guī)則的便宜。不是躲在院子里哪棵樹或哪輛車后面,我會藏到高樓里,然后隔著樓道里灰蒙的玻璃,看他們在樓下躲躲藏藏。一般而言沒人愿意爬這么高的樓梯,況且一層層地找人未免太過費力。所以我總是安全的,只需要付出等待,忍受無聊。
所以我在等,所以我一直一直在等下去。我一直在高樓上。像我,像陳平安這樣的人,我們一直在高樓上,等待,觀察,用自己的方式玩游戲。
“你在宿舍嗎?”母親在電話里說,“你下午沒課。”
我邊回答,邊站起來收拾東西。外套還披在椅背上,很好拿。
“你猜猜我們在哪兒了?”從桌上拿起學(xué)生卡。要刷卡才能打開那扇鐵門。
“到你樓下了。”握著手機,走下樓,一級一級臺階地走。但凡粗心些,但凡在這瓷磚地上摔倒,就會留下曠日持久的傷痛,必須要耐心愈合。然而我還活著,我還能愈合。我會長白發(fā),頭發(fā)掉光,牙齒松動,指甲一片片脫落。我會變得年邁,卻覺得這樣的生活還是值得再過下去。
“沒想到吧,我們過來找你了。”
母親在樓下,隔著單元門就望到了我,露出了那種熟悉的笑容,沾沾自喜。很小的時候,她每次帶我去單位的時候都會帶著一塊糖作為安慰。有次我不小心把糖掉到地上,臟得不能吃了,只好氣急敗壞地流眼淚。可是沒過多久,母親出現(xiàn)了,沾沾自喜地微笑著,就好像她剛剛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了世界。她用指尖捏著枚糖,說是用魔法變出來的,等我不哭了才能給我。于是我把眼淚全都忍回去。那塊糖濕漉漉地帶著水,肯定是被母親撿起來洗過的,我裝作不知道。他們說掉在地上的東西是不能吃的,他們沒說可以清洗一下,沒說可以補救。但我知道了。
我早就想到了,你們肯定會來看我,然后把這件事告訴所有人,再一次一次地提醒我。這是確鑿無疑的證據(jù),證明你們對我的愛與關(guān)心。而我只能裝作不知道未來。只能裝作溫柔。
母親張開雙臂,我走入懷抱中。

⊙ 葛水平· 繪畫作品選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