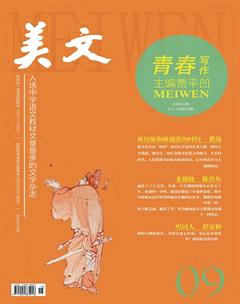自我的現身與隱匿:薇薇安·梅耶的自拍像
瞿瑞
2009年,薇薇安·梅耶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網絡上——以電子訃告的形式。這位保姆無人關注的一生結束了。之后,隨著她生前拍攝的海量照片被公開展示,梅耶作為街頭攝影師在全球范圍內聲名鵲起。一如2013年上映的紀錄片《尋找薇薇安·梅耶》中所說:死亡,帶給她生命中從未有過的聲望。
一個被遺忘的天才在死后終至不朽:這是滿足大眾消費口味的傳奇藝術家人生范式。繪畫史上有文森特·梵·高,文學史上有弗朗茨·卡夫卡。現在,攝影史上有了薇薇安·梅耶。藝術商人憑借梅耶留下的十萬余張照片大賺一筆。紀錄片則以懸疑劇情展開。一些人提起她過時的穿著——肥大的男式衣服、經常戴著軟帽:一個裝在套子里的女人;一些人提到她的收藏癖:屋里堆積如山的報紙、數不清的箱子;另一些人則提到梅耶的生活細節:沒有親人、沒有家庭、沒有電話、曾數次刻意隱藏自己的姓名……這些描述引發了公眾的好奇。對攝影主體問題的探尋,變成了對私人生活的窺伺癖。直到梅耶的自拍照成冊出售,這些“公開的秘密”讓人認識了一個具體存在過的梅耶:她的相貌和神情、她置身的環境、她經常使用的祿來福來相機……然而,從照片上看,梅耶沒有任何怪誕不羈之處,甚至過于普通了,她完全符合現代城市塑造的“人群中的人”的一般形象。
在一張取景于居民區的照片上,畫面中心是一位背對著我們的工人,正試圖將一面矩形鏡子(邊緣未曾裝裱、只經過切割的鏡子,看起來鋒利而易碎)搬下卡車。畫面上,挺直的脊背透露出他的緊張感——要努力維持平衡以防打碎鏡子。而鏡面則朝向我們,投射出正拍攝這一場景的梅耶。照片的整體背景是敦實的磚石樓房、形象模糊的居民、冬天的干枯樹梢……這些沉悶生活秩序的象征物,而照片中這個充滿巧合的瞬間捕捉了日常生活中令人會心一笑的奇趣,以自拍的詼諧瓦解了環境的沉悶、也分散了對底層生活的一般性同情心引導。
當街頭攝影師走進人群,他就擁有了一種記錄特權——不僅是他最終挑選了何種場景,他的觀看方式也會被記錄下來。梅耶的目光保持著高度的審慎,仿佛內置的攝影道德標準時刻約束著她:不把貧賤變成審美,不把高貴變成朝拜。拍攝者和照片的被攝體(人或物)始終保持著微妙的距離——近,但不至于過分唐突;遠,但不至于完全疏離。這些照片不經常借助遠景的浩大空間,因此很少引起崇高的敬畏感;這些照片也少有近距離的大特寫,因此沒有過于突兀的視覺沖擊。在梅耶的照片中,城市生活是一幅巨型拼貼畫:一匹倒斃于路旁的死馬、咬著手指頭哭泣的小女孩、公交車上戴禮帽的打瞌睡者、沾滿泥污的勞工褲腿、被丟棄于垃圾桶內的舊玩偶……梅耶的鏡頭處理了這些龐雜、瑣碎的生活場景。她對于個體的紛繁面相來者不拒,壓抑、警惕、疲憊、狂喜各占一席之地,而當這些對立情緒在同一畫面中出場,照片便成了日常生活范疇的一次擴張。同時,照片又是時間的切片、是對變動環境的及時性處理、是短暫新奇感的見證物。一如蘇珊·桑塔格所述:
照片永遠是某種環境中的一個物件;即是,不管該環境如何形成對該照片的臨時性使用,該環境都將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些環境所取代,而這另一些環境將導致原先那些使用的弱化和逐漸變得不相干。
照片捕捉的一切都在流失,場景隨時間變動,物件被紛紛替換:這是街頭攝影的特質。照片本身和照片所記錄的環境一樣臨時、短暫。而“記錄”本身既是行動,也是行動的全部意義。
在一張拍攝芝加哥街頭的自拍照上,構圖從中一分為二。左邊是典型的城市景觀:高樓林立、電車、路燈、來往人群,兩位女士正在向右邊的商店櫥窗張望,而右半邊的前景里,手持相機的梅耶拍下了這一刻。這張照片中,“我”無疑是一個游離在自我意識之外的形象,拍照者是一個尋找并思考著世界關系的人,她仿佛在邀請照片前的觀者成為自己,并分享當時的映像。往細部看,左邊的兩位女士和右邊梅耶的影像同時因櫥窗的鏡子而加倍擴張。
這些是一張典型的“梅耶式”街頭自拍像。它們常常通過鏡子、櫥窗等外部陳設完成。換言之,相機鏡頭拍攝的是關于影像的影像:薇薇安·梅耶凝視鏡子、相機凝視鏡中梅耶的影像、我們凝視相機記錄下的鏡中影像的影像。通過多次投映,目光在虛實之間反復折返:具體變成抽象、關注變成懷疑、現身變成隱匿。在這機械化的視覺構造中,本體形象被多重耗損,而真實的自我幾乎缺席。然而,我們看到的照片是如此真實,照片中的梅耶沒有喬妝、沒有自我理想化的姿態、少有與觀者的互動,街頭景觀(或人物)與攝影者共享著世界被裁切的一角,而攝影者的目光往往專注于拍攝動作本身。相機成了照片中唯一主動的目擊者,而攝影者則被迫退后。
在另一張實驗性質的自拍像中,梅耶選擇了封閉的室內空間,將相機置于兩面相對的鏡子中間(這也是反復出現的梅耶式自拍類型之一)。鏡中的我冷冷旁觀,承擔了影像實驗道具的功能,自我形象則在鏡子疊合的同心圓中延展下去,最終消失于鏡面的中心“黑洞”。由于照片中日常事物的缺席,單調簡潔的幾何形狀構成了一個現實之外的冰冷場域。鏡子創造的空間顯得既虛幻又深邃。攝影模仿了鏡子的視覺機制,并將其記錄下來。
人認識自己,通過鏡子認識外貌的影像,真實的自我卻總在別處。鏡子為自我的客體化提供了材料(巴赫金語)。鏡中影像模仿現實,但不代表現實;鏡中影像注視著我們,卻為了被注視。鏡中影像似乎延展了空間,自我卻在空間中缺席。最終,鏡子的存在讓我們意識到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我”是自我視域中永恒的盲點。博爾赫斯則寫道:
“鏡子使我感到恐懼,不僅是面對那無法穿過的玻璃,那里是一個無法居住的映像的空間,終止連著開始。”
鏡子分散了主體自我周旋的目光,瓦解了紀念碑式的強勢主體,使自拍變成了針對目光和物象的思考。起初,“我”是目光的發起者,最終,照片確認了“我”作為物像的虛幻性。這使得梅耶的自拍像遠離那喀索斯式的自戀情結,而轉向了另一種激情:她關心的是與自身共存的他者,或者說,作為他者的自身與世界的關系。
一些時候,“我”以影子的方式成為街道人群昏暗的布景;一些時候,“我”出現在櫥窗里,和商品共享了夢幻的空間;一些時候,“我”的影子使空曠的風景變得具體,脫離了風景的一般性面貌。在這些自拍照里,世間物件被紛紛納入觀看秩序,而“我”的形象不過是物件之一(等同于一棵樹、另一個行人),當被照片需要,“我”便現身填補畫面的空缺位置。這些自拍像,和梅耶的其他街頭攝影一樣,沒有道德規勸、亦缺乏批判力量,主要是追求新奇——數量龐大的照片暗合了不斷翻新的時尚邏輯,這也是攝影的當代處境:一邊嘗試著擺脫確證歷史意義的道德焦慮,一邊又撞上了視覺的無限增殖與自我空耗。
當攝影藝術獨立于以“時間、人物、事件”做注解的圖片紀實資料——攝影作為永恒的歷史見證物的身份式微;當攝影變成對現實世界的切割、變色、異形等一系列技術手段,并走向琳瑯滿目的商品時代;當攝影師不再是記憶的掌權者,只能在攝影時小心翼翼地完成對拍攝物的情感或價值判斷……作為街頭攝影師的梅耶成了本雅明筆下的游手好閑者,她只能在懷疑、探尋、偵察、漫游中理解現代世界,她如獵手般捕獲城市中的一切極端風景,同時,主體不可避免地隱藏其中,不妨說,所有照片都是抽象的自拍像。當梅耶帶著這樣的自覺拍照,她的照片就成了收集世界閃耀碎片的方式,是一種眷戀生命的激情(不同于自我確認式的自殺式激情)。正因“我”永遠不能被我的眼睛直接所見,所以人不曾停止尋找自我的努力;正因“我”無法窮盡對世界所有事物的理解,所以人不斷被新的事物所吸引——這是人類西西弗斯式的命運。最終,攝影,十萬次的目光,源自有限的生命體對世界的無窮好奇和迷戀,使一個人生命的容量,取決于他所擁有的記憶殘片的集合。本雅明對現代美學的洞見亦符合梅耶的街頭攝影美學:
“現代人的歡樂與其說在于‘一見鐘情,不如說在于‘最后一瞥之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