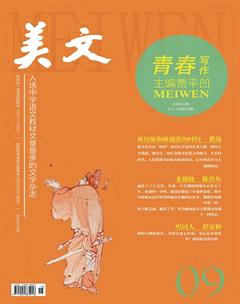坐立不安與新鮮經驗
孔呂磊
攝影技術是基于什么緣由出現的,現在已不得而知。但或許有這樣一個原因:想長久地留住、復制影像。上帝創造了人,但并不給人看見自己的權力,人只能通過眼睛看見非自己的其他人。有那么一天,人往水邊一蹲,在平穩清澈的水面看見了倒影,多方觀察后做出這是自己影子的推論,這才發現了自己。后來,人發現在一些器物光滑的表面,如銅、瓦、銀、鐵等,也可以投映出影子。人在這些發現的基礎上開始做各種發明,如制鏡,擺脫地域的限制,不一定非要尋一汪水,才能欣賞自己美好的容顏。人們從上帝至高無上的手中尋回了一分自己。
然而,人雖然看見了自己,但止于看的那一短暫過程,并不能長久地把影像留住。鏡面離開,影像也會消失。繪畫的重要性開始體現出來。畫家通過幾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用自己嫻熟的技藝,觀察并利用光與影的變幻交織,將畫板前的事物凝固在畫紙上。人或物,便經由這一張畫紙及畫家的技藝與筆墨,留存了下來。幾年、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不同的人在這幅畫前停留,駐足,觀看,靠留在紙上的印記,復現當日的情境。
然而,絕不是最準確的復現,不是完全的復制。怎樣想象,也不可能與當日情境分毫不差。科技不斷發展,攝影技術出現。投射在暗箱內的影像被固定,浮動短暫的視覺被銀版保留。攝影,顯然比繪畫更為準確與真實——更“真相”。它可以捕捉到繪畫難以窮盡的一些東西,甚至人眼也注視不到的地方。它留存了它所捕捉的那個瞬間,且可以一直留存下去,不受時間以及空間的限制。
繪畫與攝影一直糾纏不清。初始的達蓋爾的銀版相片,是輔助繪畫的工具——一些肖像畫家拍攝肖像照來繪制人物肖像畫,服務于畫家作畫。而肖像照卻機緣巧合地極大促進了攝影工業的發展,使后來攝影作為科技,以及一門藝術,開始獨立。
攝影首先是一門技術,它是科技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攝影最開始一定是實用的,它可以精準、客觀地復制場景,并長久地留存,復刻、記錄、紀念等都是它的功能。攝影的實用功能從出現的那一刻起,直到現在,一直存在著。它廣泛地運用在人類的各種活動中,如紀實、新聞、醫學、物理等各行各業。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攝影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功能,記錄事件,參與宣傳,傳播價值,帶上了道德與政治色彩。攝影作為藝術,則是攝影技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而后產生的現象。“攝影作為藝術”這個命題是否成立,也曾爭論不休,有不少人質疑過它的合法性。當今,人們已經普遍承認——攝影作為藝術,更是藝術作為攝影。
攝影作為藝術,很多環節必不可少,而在“鑒賞攝影作品”這一具體環節中,有三個元素不可或缺:拍攝對象、攝影者、觀者。
被拍攝的對象并不是眼睛所看到的那么簡單,不管是人、物或者景。拍攝對象處在完全自然不受任何注視的環境中時,是一種狀態。拍攝對象在人的視線里,即人眼中的拍攝對象,與前一種相異。而當拍攝對象被鏡頭注視時,所呈現的又不一樣。鏡頭抓取了對象,對象有時自知,有時不自知。自知時,它或許有自己的訴求,意欲呈現給鏡頭,或許沒有。緊張,刻意,表演,或者盡量自然地呈現,雙方達成一次完美的合作。不自知時,鏡頭抓取到它最本真的狀態,神情、動作、細節、光影等袒露無遺,有瑕疵,但是是沒有經過修飾的最赤裸的一面。
鏡頭的制作越來越精密,攝影者的技藝也在大量的實踐中提高。鏡頭捕捉的范圍可以細微到極致,也可以廣袤到極致。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肉眼所無法觀察到的,都有了呈現在鏡頭前的可能性。攝影者通過拍攝角度的調節、曝光時間的長短等,形成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作品。在攝影過程里,時間被延長或者壓縮,細節被放大或者縮小,攝影者做的所有動作,都頗值得尋味。
一個藝術作品的完成并不止于被作者完成的那一瞬,被復刻在膠片上或者被打印機沖印出來,它必須接受欣賞者即觀者的觀察與鑒賞,其價值才能被體現,一個完整的鑒賞活動才算完成。對每個觀者來說,其看到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不可重復的,并且可以無限延展與想象。觀者在作品面前其實有些微的緊張與審慎,不管表現的如何從容。受制于自己所浸淫的宗教、文化背景,所接受的教育,日常所處的生活環境與人生閱歷,其審視的作品帶來的觀感是不一致的。個人的經驗不一,眼前一物,心有萬象。觀察光與影的搭配、人物的神態動作,努力體悟作品所要傳達的情緒與意境,基于個人經驗,或者沖破個人經驗,自由想象,賦予作品自己的解讀。好的觀者在作品面前,總是坐立不安的。
不同的距離——地理距離與時間距離——之下,面對同一作品,觀者的體驗也各不相近。十厘米之外與一米之外,審視的角度變了,感受自然不一。不同地域、不同國度,面對同一作品,審美經驗不同,審美結果也不同。照片拍攝的當下——成像的那一刻,凝視時是一種情緒,靜置幾日、幾月回頭再看,又是一種情緒。而當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過去之后,雖面對著同一張照片,但夾雜著漫長時光附帶的記憶、思想、經驗,又是全新的另外一回事情了。
攝影捕捉了瞬時的畫面,使時光定格,這是人類了不起的發明,如最神奇的魔法師,從上帝之手中抓住了時間,認知了部分的自我與世界。短暫、瞬間的時光可以在相片里流傳、延續,真實地擺脫了時空的限制。延續下去的不止是那一瞬間,更是那一瞬間所附帶的記憶與情緒,跟著相片在不同觀者的眼中心中不斷復活。延時攝影,長時間的曝光,更使得人、物居住在照片里,不只是浮光掠影,而是切實的生活與生命。“被拍者曝光的時間很長,久久靜止不動而凝聚出綜合的表情”,“曝光過程使得被拍者并不在留影的瞬間之外生活,而是生活在那種情境當中。在長時間的曝光過程里,他們仿佛住進到攝影鏡頭里,定居了下來。”*郭國柱《洗洗睡吧》及杉本博司《劇場》系列作品,通過長時間的曝光,不止捕捉到一系列活動,更似乎捕捉到作品里人、物的生命與靈魂。攝影可以使人游離在漫長又轉瞬即逝的時間之外,可以尋回、占有過去,可以預見未來,捕捉到上帝手中時間的一些秘密。
探尋攝影者想要表達的潛在意義,鏡頭記錄下的一些情緒:憂郁,狂喜,浪漫,懷念,沉痛,悲憫,靜默,懷疑,一些個體的不安,或者群體的灰敗,創傷,癥結。這里沒有權威,沒有絕對正確,每個觀者都是新鮮的經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