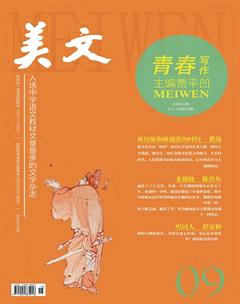如切如磋
陳碩
直至今天,我還記得在明十三陵見過的那頂真正的鳳冠,冠面曼妙,銅絲蜿蜒,景泰藍的翠色如靈巧的手指攀爬于上,血紅的松綠的幽藍的寶石見縫插針地閃著微光,一穗一穗的瓔珞和流蘇從昂首的鳳凰口中吐出,如三月萬千柳葉齊齊拂過臉頰。在玻璃展柜的燈光下,鳳冠散發著迷人的光澤,有一種遺世獨立的美,它穿過千年光陰來到我面前,帶走了我的心跳。
我把額頭抵在柜子邊緣,本能地屏住呼吸,徒留一雙眼睛,如饑似渴舔舐著每一寸細節。是一雙怎樣的手,是一顆怎樣的心,制作了這樣動人心魄的美?我仿佛看見老繭與金屬的數萬次摩擦里,銅絲被折疊出優美的弧度;看見五彩的琺瑯釉無聲無息蔓延過胚網,精確地停留在細線邊緣;我還看見刻刀宛轉游走,金色的神鳥抖落一身碎屑,破空而來;看見墨黑純粹的眼睛,看見流暢而冷靜的臂腕,看見匠人背后靜默的影子落在宮室一隅,猶如蝴蝶翅膀長長拖曳……
《京華煙云》中姚木蘭見到極美之物會落淚。而我,在這樣的手工藝面前,悸動之余,卻唯有低眉沉默。驕傲,愧怍,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在我心里大聲叫囂起來,一起涌到嘴邊,卻終究化為一聲悠長而低呢的嘆息。
周國平在《守望的距離》中說:“縱使相隔千山萬水,千年萬載,守望,仍是必須。”可是,在時光的隧道里,在科技的進程里,我們失去的何止是那春風駘蕩、寧靜淡泊的精神桃花源?多少精湛無私的民間手工藝在無人關注無人傳承中喪失殆盡?多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一味求快隨心所欲的氛圍中遺落?守望者,著實越來越少。
有人說,魯班與庖丁的技藝依然后繼有人、代代相承。然而即便有這樣的傳承,并不意味著有這樣的文化。就如同很多人貌似酷愛經典文學,卻不過是用文字書籍當作裝點門楣的珠玉。不少人偏愛“短、平、快”,一味追求效率,享受速成的驚喜卻犧牲長久的質量。有些人空談情懷愿景,勾畫出驚艷的藍圖沉湎其中,卻出不了令人滿意的成果。更有甚者求利益,輕信仰;求效率,輕質量;求外表,輕靈魂;求短益,輕遠利。若有一天,不精確、不認真成為中國人特有的幽默和自嘲,精益求精的態度被蠶食壓縮無跡可尋,那么最可怕的災難已然降臨,最怕的不是無力反抗,而是隨波逐流。
而在日本,工匠被稱為職人,工匠精神被看做是一種近乎于自負的自尊心。對于日本的木屋匠來說,樹的一生是精確到每一條紋路的藝術。伐木工不斷修剪旁枝,不厭其小,不辭其勞,代代相傳,百年之后才能得到樹干筆直、沒有疤結、年輪均勻分布的參天大樹。而造木的工匠在柔軟的桐杉櫻或是堅硬的櫸栗橡中精心挑選,在直木紋、斜木紋中尋找最契合的紋路,把山坡陽面的樹木用作房子的陽面——那樣耐心、緩慢、執著而堅定。
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它應該永遠是代代后人綿綿不絕的滋養。
在大工業化的今天,流水線自動化依然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人說急功近利是人的本能,工匠精神的消亡是大勢所趨。與其活在歷史中不思進取,不如順應現下擁有的高效便捷。可在央視紀錄片《大國工匠》中,擁有頂尖技藝的一線電焊工人心如止水,手如拂羽,身如淵渟岳峙。在高溫密閉,火花如風雨傾瀉中,手中焊槍未有一絲晃動。如雞蛋殼厚度的鋼板上,14公里繁難焊縫無一漏點。傳統工匠所秉持的細膩與考究,在現代社會化作做事的堅韌與誠懇,被熱烈地呼喚與渴求。可以大刀闊斧注重實效,也應細針密縷精益求精。可以借他山之石用以攻玉,也該精雕細刻匠心獨運。《詩經》有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鍘、鏨、沖、壓、劃活、打眼、拋光、剪影。在這日臻精妙的工藝背后,我們看到了守望者的動人的姿態——唯恐遺失分毫的勤勉之姿,我們看到了對技藝與態度的雙重堅守。“一個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夠的。”這句來自王小波的話,我覺得適合用于任何領域。沒有傳承就沒有人類,更沒有歷史和未來。
是時候重拾工匠精神了。守之,望之,以期催生出更璀璨的民族文化。
愿那鳳冠的絕世之美不被塵封在過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