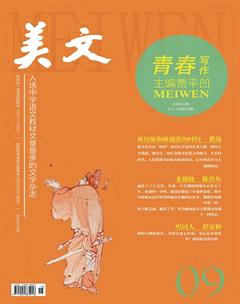追
俞純彥
不禁想到畫糖人。
印象里,糖人總是出現在有關于京城廟會的描述中。熱熱鬧鬧的新春佳節里頭,趕一趕廟會沾點兒喜氣。一眾人圍著一輛小推車,糖人師傅嫻熟地將棕黃色的糖料用小勺舀起,在石板上澆出線條,組成圖案。生在南方的我不常看見賣糖人的小推車,但是一有機會也仔細瞧過糖人師傅的手藝。眼到手亦到,一氣呵成。還沒反應過來是怎么一回事兒,一個栩栩如生的造型,已經用竹簽粘好送到眼前來。
百度百科里介紹道:“由于糖料的流動性,即使相同的形象,亦不會出現雷同的造型。民間藝人在長期實踐掌握了糖料的特性,同時根據操作的特點,在造型上多施以飽滿、勻稱的線條,從而形成了獨有的風格樣式,給人以美的享受。”
正如斯格制作玻璃制品一般,糖人的制作大抵也是如此吧。當把糖料舀起,準備在那石板上“潑墨”時的心情,也就像拆開圣誕禮物前的那一份對未知的期待一樣。手一提一放,一揮一灑,刻意或是隨意,提放揮灑間,便又是一件藝術品。畫糖人這件事,永遠都是充滿未知的,是一個創造的過程。它對糖人師傅的眼手功夫要求很高,關鍵又是在一瞬間。手一抖,一斜,或許就偏了原來預想的模樣,但又可以恰巧順著這錯誤下去,再一抖,一斜,又創造出另一番藝術形象,正所謂“將錯就錯”。這是創造,一個屬于手藝人的創造。或者升華一些,這能不能算是小小程度上的創新呢?
其實說到創新,離平日里生活近一點的,還是民間藝術,就像畫糖人一樣。在我們身邊親切地存在著,也親切地創造著。盡管有時,我們未必能正確地定義創新的意義。
《門雕神匠高應美》中講高應美,是晚清的一位木匠,他以刀削斧斫下的木渣計工錢。從光緒末年直到去世,他完成的作品僅只三四件,還有一兩件下落不明,傳聞高價藏入他國博物館。他雕門,一雕十幾年。雕小新村三圣宮的格子門,花了十七年。他不急,一刀一斧,用盡功力,一刻就是十七個春秋。一百四十九個人物,形態各異,他就用他的手,生生雕出了一百四十九個栩栩如生。他學不會創新,依舊按著舊時代的內心法度生活,今天雕上一小會兒,先聽個小曲兒,喝個小酒,明天再接著雕,時間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什么要緊事。他的做法無疑是舊式的,他的做法也無疑是精致的。不過,這樣的人,結局如何呢?最后眼瞎了,餓死了。他生活在怎樣的一個時代呢?一個人們開始追求效益,精簡時間的時代,時代的潮流已經慢慢偏向天平的“效率”一端,時間不等人的概念逐漸深入了晚清人的心。當然,那個時代的門,應該沒有一扇到今天還能像出自他手的一般精美、完好。
時代不會等人。當時代改變了,時代創新了,人們漸漸崇尚時間就是金錢,認為浪費一秒就會落后的時候,高應美他依然遵循著內心的法度生活。難道時代整體觀念的進步不是進步,不是創新嗎?不,是的。難道高應美的做法就是逆著時代潮流,不創新所以注定是錯的?不,不是的。
所以啊,我們應該懷著畫糖人一樣的心情向一切未知的事物發聲,因為前方未知,所以會有期待,會有創新的余地。那么像高應美一樣勇敢地不迎合世俗去面向未來,就一定不可取嗎?創新生來好像就被賦予了褒義詞的功能,倘若沒有創新卻精致地活著,也許不一定會像他一樣被世俗淘汰,但是你想,漫長的歲月,如果前方不存在著值得等待的事物,還有什么價值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