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些不甘心的青春
致那些不甘心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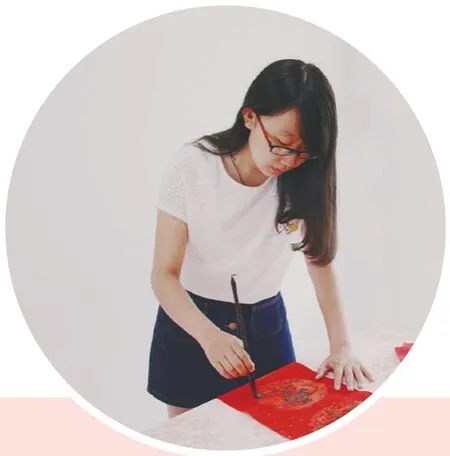
既禾
一手寫現實、一手寫青春的分裂青年,混跡在荒蕪又盛大的西北,夜里寫詩,白天做夢。新浪微博:@既禾
覺眠來北京的那天,我們約在黃昏時見面。北國的夏天漸漸來了,燥熱的空氣里,北京城依舊車水馬龍。這座批量生產繁華與夢想的城市,日復一日地運轉著,并沒有用什么特別的儀式,迎接這異鄉的來客。
漫長的沉默后,我試圖打破冷清,端起奶茶,祝她開啟全新的生活。覺眠只是苦笑,托著下巴不說話。
或許,劈頭蓋臉砸過來的新生活,她根本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談何慶祝與期許。
那段時間,覺眠大學畢業在即,卻面臨諸多不順,所有能想象到的麻煩,似乎無一例外地找上門來:剛剛經歷了考研的失敗,租房時又被黑中介坑走了幾個月的生活費,和喜歡的男孩維持了一段若即若離的感情,最終還是無疾而終。
她喜歡做記者,對新聞有滿腔熱情,考研失敗后決定到傳媒業發達的北京闖蕩,但最先迎面而來的,恰恰是最親密的人的反對——父母不愿她顛沛,托關系為她在老家找了一份銀行的工作,希望她能一生安穩。
最終還是一腔孤勇勝了一切,覺眠帶上最簡單的行李,從那座偏遠的西北小城來到了偌大的北京,掛著濃重的黑眼圈坐在我面前,咬著奶茶的吸管,長久地發呆。
她說,自己已經在師姐的幫助下,找到了一份新媒體工作,那是一家很牛的互聯網公司,傳播著無數國人閱覽的資訊,有足夠優秀的同事和足夠豐厚的待遇,但工作內容無腦而枯燥。
“我不喜歡,但是簽了。”她說。
毫無疑問,這是應對父母催逼返鄉的最有效手段。
那一天,在北京濃重的夜色下,我們一步一步朝前走著。最后站在十字路口,看紅燈變綠,綠燈變紅,眼前的路似乎綿長得沒有盡頭,唯一可以預知的就是,生活安排在其中的荊棘、無常和變數。
過去的日子里,我們一起曬過月光,行過沙漠,爬過高高低低的山,走過長長短短的路。我深知她的堅持、她的夢想,但如今面對紛雜的一切,祝福的話一句也說不出。
臨別時,途經小公園,大媽們還在熱火朝天地跳舞。覺眠自嘲地嘟囔了一句:“說什么新聞理想,幾十年后還不是去跳廣場舞?”隨后又自言自語道,“可是我還有一口氣啊。”
我在一旁驀地笑了,看到她的眼睛里有光,就知道她能戰勝一切頹喪。
果然,那之后沒多久,我便接到了她的電話,當同學們陸續有了各自的工作,我親愛的覺眠辭職了。
再見面時,她伸著手指為我一一列舉:女警給違章男司機送玫瑰花,同時宣傳法律法規;服裝廠員工報警稱車間出現恐龍,實為蜥蜴;父親生前打賭慘敗,至死不服,兒子為父報仇,砸破鄰居腦袋……
“這也叫新聞?”這句是總結語。
我不知道那段日子,她的生活到底有多糟糕,但最直觀的感受是,曾經那個溫婉嫻靜的女孩學會了爆粗口。
辭職后的她跑去了一位敬重的媒體前輩那里,從頭做起,成了一個沒有薪資,甚至沒有固定工位的實習生。見到前輩的第一面,她沒有炫技也沒有寒暄,只真誠又堅定地說了句:“我不在乎能不能轉正,先讓我跟著您做新聞就行。”
面對所有人拋出的“何必”與“何苦”,她都酷酷地回應:“我愿意啊。”
理想主義的光重新噴薄出來,那些叫囂著不信、不服、不甘心的青春,真是沖動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