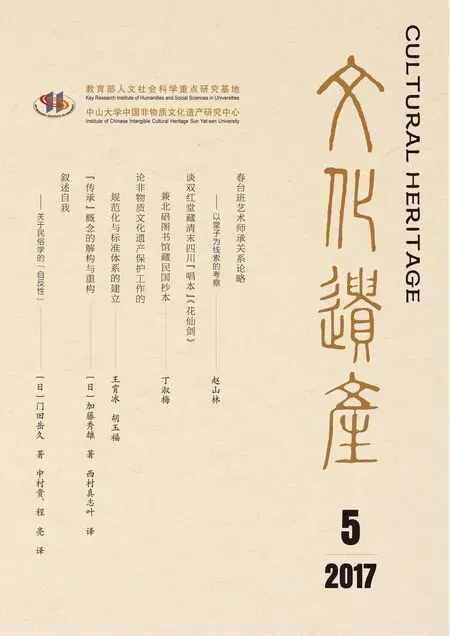“避難—登高—尊高年”與詩意人生*
——關于重陽節(jié)俗文化創(chuàng)新的思考
黃意明 秦惠蘭
“避難—登高—尊高年”與詩意人生*
——關于重陽節(jié)俗文化創(chuàng)新的思考
黃意明 秦惠蘭
傳統(tǒng)重陽文化的形成,和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念及早期原始信仰有關,重陽文化在其歷史發(fā)展流變過程中,又被賦予了新的內(nèi)涵與功能,尤其是在和禮文化結(jié)合后,報本反始的敬老功能得以在節(jié)日中深化。此外,傳統(tǒng)重陽節(jié)又是一個詩意和休閑的節(jié)日,無數(shù)文人雅士構筑起的重陽詩性文化,代表著中國人閑逸曠達的人生觀。這一特點與春節(jié)文化、清明文化或端午文化之功能均有所不同。今天重建重陽等節(jié)日文化,必須注重原有的歷史資源。
重陽節(jié) 避難 登高 敬老 菊文化 內(nèi)涵創(chuàng)新
一、重陽節(jié)的起源及早期原型
在傳統(tǒng)節(jié)日中,重陽節(jié)的民俗特征較為特殊。歷史上的這一天,人們通常都要外出登高游樂、佩茱萸、飲菊酒、食重陽糕、求長壽等。重陽習俗的起源很早,有戰(zhàn)國起源說、漢代起源說等說法。《西京雜記》記載:漢高祖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以前在宮內(nèi)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頁。。可見后世節(jié)俗中的一些主要內(nèi)涵漢代已都有了。史載后來一些地方還有食菊花糕和菊茶的習俗。南朝《太清記》載:“九月九日采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令人不老。”*(南朝)王韻之:《太清記》,見《古今圖書集成·歷象匯編·歲功典》卷76第22冊,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34年版,第1頁。唐代皎然《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云:“九日山僧院,東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
重陽節(jié)為何要舉行這些活動呢?這是和古人對此節(jié)日的理解有關。
“重陽”的名稱一般認為來源于《易經(jīng)》。易以陽爻為九,將九定為陽數(shù),兩九相重為重九,日月并陽為重陽,故名重陽。
據(jù)南朝吳均《續(xù)齊諧記》載: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大災厄,宜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飲菊酒,此禍可免。”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斃。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花酒,婦人帶茱囊,是也。*(梁)宗懔:《荊楚歲時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7頁。
這一傳說雖未必可信,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它揭示出登高飲菊酒習俗來之于對災難的恐懼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逃避死亡和災難的活動。更深一層說,它或許反映了遠古人民對于某種災難的記憶。有學者從《夏小正》“九月內(nèi)火”,即“大火星不見了”的描述中,認為古人的神秘思維是,火星的休眠自然地與萬物的死亡聯(lián)系起來,因而存在著一種隱層結(jié)構(三月三——復活節(jié),九月九——死亡節(jié))并認為這種重陽登高活動是上古洪水災難的反映。*參見張君:《九九重陽節(jié)——中國傳統(tǒng)的死亡節(jié)、升仙求壽節(jié)和酒神節(jié)》,《求索》1993年第5期。也有人認為登高是為避火災*丁世良 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頁:“九日飲菊酒,佩茱萸,登高,以為避火災。”火屬陽,故以陽九日避火災。。

而古人重陽之所以要佩茱萸、食菊花,開始也是因為菊花與茱萸都有辟邪延壽的功能,如西晉周處《風土記》載:
漢俗九日飲菊花酒,以祓除不詳。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shù)九,俗尚此日折茱萸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御初寒。*《古今圖書集成·歷象匯編·歲功典》卷七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34年版。第22冊,第1頁。
宋人吳自牧《夢粱錄》云:
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飲之,蓋茱萸名‘避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宋)吳自牧:《夢粱錄》,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
其實,茱萸和菊花都可以入藥。茱萸又名“越椒”或“艾子”,香味濃烈,可以驅(qū)蚊殺蟲,而菊花久服則“利血氣,令人輕身耐勞延年”,具有養(yǎng)生延命功能,即可得高壽。
不過,隨著這一習俗的節(jié)日化,重陽日避災祛邪的神秘意識逐漸淡化,而漸漸演變成了人們祈求長壽、強身健體、祝福兒女、欣賞美食及外出登高野游等尋求美好生活的民俗活動了。例如后世有重陽吃菊花糕的習俗,“糕”即“高”的諧音,據(jù)明代高濂《遵生八箋》記載:九月九日,人們把菊花糕切成薄片,搭在未成年人額頭上,祝福道:“愿兒百事俱高!”由此可知食菊的含義已由辟邪,求壽高而引申為“百事俱高”,這與其原始意義相去甚遠。又如可能由登高演變而來的野宴,也是重陽的一大景觀。在梁代宗懔的《荊楚歲時記》也有記載:“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飲宴。”隋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世來未改。”*(梁)宗懔:《荊楚歲時記》,第127頁。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四里橋、愁臺、梁王城、硯臺、毛駝崗、獨樂崗等處宴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八,重陽,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6頁。清代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云:重九“都人結(jié)伴呼從,于西山一帶看紅葉,或于湯泉坐湯,謂菊花水可以卻疾。又有治肴攜酌、于各門郊外痛飲終日之俗,謂之‘辭青’”*(清)潘榮陛:《帝京歲時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伴隨著登高和野宴的,還有插茱萸、賞菊花,飲酒、賦詩等活動,這就使得重陽節(jié)完全變成了一個全民游賞性的節(jié)日了。
由于士大夫的廣泛參與,有些活動,尤其是由愛菊、賞菊而形成的菊文化,逐漸成為重陽節(jié)的重要載體,大大豐富了重陽節(jié)的內(nèi)涵,使得重陽節(jié)又具有了思鄉(xiāng)念親、抒發(fā)懷抱、修身養(yǎng)性等內(nèi)涵和身心調(diào)節(jié)的功能。唐寅的《菊花》詩云:“多少天涯未歸客,盡借籬落看秋風。”即屬于思鄉(xiāng)念親的主題;而杜牧的《九日齊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則告訴了我們重陽登高賞菊還有心理調(diào)節(jié)的功能;蘇軾“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和鄭谷的“露濕秋香滿池岸,由來不羨瓦松高”等名句,則抒發(fā)了志士仁人的懷抱;至于陶淵明《飲酒》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則體現(xiàn)出隱逸者獨善其身的理想。這樣,重陽節(jié)的內(nèi)涵便愈來愈豐富了。
由重陽節(jié)的演變可知,正是人文因素的興起和雅文化的滲入,使得重陽逐漸擺脫了原始思維和早期信仰的形態(tài),內(nèi)容更加豐富,格調(diào)更加高雅。
二、重陽節(jié)敬老活動的歷史內(nèi)涵
今天,重陽節(jié)仍是一個重要的節(jié)日。二十多年前,政府將重陽正式定為老人節(jié),從而讓這一節(jié)日的內(nèi)涵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一行為可以說是有根據(jù)的。在我們的傳統(tǒng)語言中,就有“松菊延年”、“杞菊延年”等祝壽語,因為菊花是重陽的時令花卉,又是重陽文化的重要載體。更重要的是,歷史上農(nóng)歷八、九月的秋季,就是傳統(tǒng)的敬老時間。
史書上有關秋季敬老的記載較早見于《禮記·月令》。該篇記載,先秦時期每年的仲秋之月,天子都要“養(yǎng)衰老,授幾杖,行糜粥飲食”*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頁。。這里的“幾”,為“古人憑坐者”(《說文》),即幾案;“杖”,手杖、拐杖。意思就是說天子對于年老力衰的老人,要授以幾、杖,賜以飲食。關于授杖,史書中常稱“高年授王杖”。因所授之杖,乃當朝皇帝所賜故稱王杖。這個王杖的杖頭飾鳩,故又稱王杖為鳩杖,象征著老人飲食如鳩,咽而不噎,這是一種健康長壽的祝福。這些都是敬老的國家儀式。
西漢初年,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頒布了敬老養(yǎng)老詔令,凡八十歲以上老人均可享受“養(yǎng)衰老、授幾杖,行糜粥飲食”的待遇。建始元年九月,漢成帝劉驁即位。在當年所頒布的王杖詔書內(nèi),提到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人所尊敬也”;問候八十歲以上的老人“生日久乎?”將享受這種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齡降到了七十歲。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對高齡老人進行登記造冊,舉行隆重的授杖儀式。如《后漢書·禮儀志》中記載:“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范曄:《后漢書·禮儀志第五》,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簡體字版,第2119頁。
唐開元二年(714年)九月,唐玄宗在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大宴京城父老,并舉行了隆重的授幾杖敬老儀式。此次賜幾杖遍及全國八十歲以上的所有老人,成為我國古代規(guī)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賜幾杖儀式。*《全唐文》卷二十六,轉(zhuǎn)引自謝元魯、王定璋《中國古代敬老養(yǎng)老風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頁。
另外據(jù)載,開元二十四年(736)八月初五,為唐玄宗五十一歲生日,他遂將此日定為千秋節(jié),賜宴父老并賜禮物。詔曰:
今茲節(jié)日,谷稼有成,傾年以來,不及今歲。百姓既足,朕實多歡。故于此時,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并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少物,宴訖領取。(《全唐文》:玄宗《千秋節(jié)賜父老宴飲敕》)*《全唐文》卷二十六,轉(zhuǎn)引自謝元魯,王定璋:《中國古代敬老養(yǎng)老風俗》,第77頁。
從以上這些史料中,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上國家敬老行為常發(fā)生在八、九月間,這應該和秋季對應于人生的晚年相關,但八月的節(jié)日較多,如中秋、迎潮神等。且中秋是個大節(jié),本身已有祭月拜月、家人團聚、慶豐收等內(nèi)涵,而九月重陽卻不同,正好有著延年益壽的祈愿。所以現(xiàn)在國家將敬老作為重陽節(jié)俗的重要內(nèi)容固定下來,這樣有所取舍,應該是較為合理的。
以上這些秋季養(yǎng)老敬老的國家行為,無疑和我國古代的尊老傳統(tǒng)有關,而尊老的禮儀則是傳統(tǒng)禮樂文化的一部分。先秦儒家認為禮是維持人倫日用、社會規(guī)范的有效手段,“禮者養(yǎng)也”。儒家提倡孝道,敬老的內(nèi)容在禮文化中也有大量的規(guī)定。《禮記·鄉(xiāng)飲酒義》有云:
鄉(xiāng)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yǎng)老也。*楊天宇:《禮記譯注》,第1066頁。
另據(jù)《禮記》的《王制》、《內(nèi)則》篇記載,遠古時代,舜每年用“燕禮”,禹用“饗禮”,殷商時則用“食禮”款待老人。周則兼而有之,分別宴請“國老”(有爵位和有德行的老年現(xiàn)任或退休官員)和“庶老”(庶民中的老者),并且“既養(yǎng)老而后乞言”,在敬老宴會上還要請老人們對國政發(fā)表意見。除了設宴敬老,當時還有很多具體的養(yǎng)老措施。
這些都構成了重陽節(jié)敬老的歷史資源。
三、今日重陽節(jié)與文化創(chuàng)新
筆者以為,民俗節(jié)慶中留存了大量的傳統(tǒng)文化因子,而在時代變遷,節(jié)慶觀念趨淡,節(jié)日原義漸失的今天,重新開發(fā)節(jié)慶功能,事實上是在進行文化重建的工作。但是,任何文化重建,都不可能是向空杜撰,閉門造車,而應重視挖掘已有的資源,重陽節(jié)的重建工作也應如是。
從功能上講,重陽節(jié)自古至今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即從最初的祛災避難之登高逐漸演化為祈求長壽和敬老,它的吉祥物“茱萸”和“菊花”就曾被人們廣泛地稱為“避邪翁”和“延壽客”。皇帝賜予年老的臣子和百姓中的壽星手杖或衣食物品則是敬老行為的儀式化。
從文化上講,由于文人愛菊的緣故,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孟浩然、蘇東坡、陸游、李清照……數(shù)不清的騷客文人留下了數(shù)不清的重陽詩文,從中反映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深厚的,也是其他傳統(tǒng)節(jié)日難以企及的。
因此,重陽節(jié)的文化重建與文化創(chuàng)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重陽敬老內(nèi)涵需要深化。
在今天政府已將之正式定義為敬老節(jié)并取得廣泛社會共識的情況下,重陽節(jié)的主要內(nèi)涵已變成尊敬老人和關心老人。這樣,它的主要功能就指向已超過2億的60歲以上的老人、占全國人口15.5%比例的一個銀發(fā)社會。既然是一個全民敬老的節(jié)日,就需要創(chuàng)造一個全民表達敬老、愛老情感的環(huán)境和條件,但就多年來的現(xiàn)狀而言,重陽節(jié)“特殊”的節(jié)日功能并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據(jù)調(diào)查顯示,過半的年輕人不知道重陽節(jié)在哪天,不知道重陽節(jié)是傳統(tǒng)節(jié)日,更不知道“重陽節(jié)”與“敬老日”同為一天。而知道重陽節(jié)的除了將其與“敬老日”簡單劃等號以外,絕大多數(shù)又并不知道重陽節(jié)還有什么特殊意義。
調(diào)查還顯示,絕大多數(shù)報紙傳媒在重陽節(jié)那天報道的中心話題是“工會”、“領導”“送溫暖”,“看望孤老獻愛心”。而大部分老年人對重陽節(jié)的期待僅僅是單位的“慰問”。這其實是一種“別無選擇”。重陽節(jié)也僅僅成為單位退管會一年一度的“一項工作”。這與封建時代的慰勞模式相比,實在有著天壤之別。
我們認為,在重陽節(jié)到來之際,其實地方基層政府、公益組織、社區(qū)民眾、居委會等有很多工作可做,完全可以營造一種年輕人尊老,政府與社會敬老,老年人安老的氛圍。例如政府及民間組織可以在重陽前后(逢雙休日),舉辦游藝民俗和文藝演出活動,提倡祖孫三代共同參與,強化祖孫隔代之間的感情,增強報本反始的感恩意識。也可以在重陽節(jié)那天,在中小學舉行一些手工制作和新媒體創(chuàng)意設計,作為禮物送給家中的老人。此外,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平時應多去社區(qū)舉辦講座。在秋日重陽時節(jié),則宜涉及晚境的主題,畢竟,人生的有些美好,要到晚年才能體會。醫(yī)務工作者也可在重陽時期進行公益養(yǎng)生講座,以應對老年社會的健康需要。
應該說,近年來的中國,由于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有相當數(shù)量的老年人依然保持著積極投入生活的熱情,他們有的走出國門,有的繼續(xù)學習,有的仍在工作。但也應看到,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老年人缺乏生活的熱情,總是被動地并習慣地等待著他人的關愛。因此,營造重陽節(jié)的假日氣氛,豐富重陽的文化內(nèi)涵,設計一些普適老人的文化活動,通過一些特定的儀式彰顯人生晚年的價值,客觀上能夠激發(fā)起千百萬的中國老人熱愛生活、珍惜生活、享受生活的美好情懷;煥發(fā)他們的青春、活力、“稚氣”;重新啟迪他們的心智、勇氣、力量。總之,鼓勵老年人共同參與構建和諧社會,體驗美好人生,同圓中國夢,這也是重陽的另一種解釋吧!
因此,從以人為本、老有所樂、老有所為和建構敬老文化的角度而言,深化重陽節(jié)的節(jié)日功能自有其特殊意義。
第二,重陽登高與文化提升。
重陽節(jié)之特殊性,可表現(xiàn)在與清明、端午、中秋諸節(jié)的對比上。
以傳統(tǒng)形式而言,春節(jié)、中秋是講究親情團圓、以小家為核心的家庭回歸型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清明、端午等是以祭悼緬懷為主的家庭祭奠或公祭型的節(jié)日;而重陽節(jié)的特點卻是外出休閑型的登高游樂,這一點比較符合現(xiàn)代社會人們對生活質(zhì)量的要求,符合現(xiàn)代人放松心情的需要,但是今天,登高旅游卻普遍較難實現(xiàn)。一方面,重陽節(jié)并不放假;另一方面,現(xiàn)在城際交通已經(jīng)很擁堵,大量出行勢必更給交通添堵。因此,如何將這一傳統(tǒng)模式轉(zhuǎn)化,就顯得很重要。筆者以為,歷史上登高可以有幾重含義,既可以是外出登高,也可以是祝福老人高壽,還有祝福兒女快快長大等意義。故今天我們也可以將登高引申轉(zhuǎn)化為文化水平與文化境界的提高,例如祝賀孩子升入高一等級學習,祝賀自己或他人達到某種新境界,反思自己在價值追求上有沒有年年進步等等。
從具體內(nèi)容上講,重陽節(jié)除了傳統(tǒng)的外出登高外,民間老百姓還普遍保留著賞菊活動。“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是家喻戶曉的千古名句,也是人們心中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菊花如端人,獨立凌冰霜”,則是陸游頌揚的人格,也是中華民族的格言;面對“東籬”,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憶起“南山”,就有望精神脫俗一番。有關部門和民間機構、學校、社區(qū)及個人均可在重陽辦菊展。因為在傳統(tǒng)菊文化中,有著思鄉(xiāng)念親、君子人格、回歸自然、贊頌生命等多個主題,因此可以結(jié)合不同的主題辦菊展,通過普及文化知識來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還可舉辦重陽詩會和文化講座等等。
進入21世紀后,很多人在談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但文化是有其符號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化特征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確定各個節(jié)日的文化符號和文化象征方面,我們做得并不夠。通過對鄰國的民俗文化考察可知,他們在重陽節(jié)及其相關的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方面做得比我們好。例如從節(jié)日的象征性符號來說,重陽節(jié)自古有著它“特殊”的物質(zhì)載體:菊花酒、重陽糕。可惜這一節(jié)日載體偏偏被我們遺忘了,很多人不知道重陽節(jié)該吃什么!倒是我們的鄰國韓國還延續(xù)著這千年的節(jié)令食品。這些也可以成為重陽經(jīng)濟乃至創(chuàng)意文化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講,一些重陽食物如菊花酒、重陽糕等完全可以重新研究開發(fā)。
所以,重陽節(jié)與其他傳統(tǒng)節(jié)日相比,并不缺少可以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地方;同時,它也更符合現(xiàn)代假日的理念。可以這樣說,當代重陽節(jié)是一個各方面最能體現(xiàn)節(jié)日要素、并被賦予積極意義的傳統(tǒng)節(jié)日。
第三、對重陽節(jié)列為法定假日的建議
重提將重陽節(jié)列為法定假日的建議,是因為不在周六、周日的重陽節(jié),人們是不可能請假去看望父母、祖父母的。以筆者為例,也不可能不上課去探望父母親,當然更談不上在這一天陪同父母外出走走。所謂登高望遠,賞菊秋游,也總是一個不太可能實現(xiàn)的美好愿望。
筆者認為,要使今日之重陽節(jié)真正實現(xiàn)其作為一個有“特殊”意義的節(jié)日,突出其歷史內(nèi)涵,彰顯其文化功能,就在于將重陽節(jié)列為“法定假日”——在重陽節(jié)到來的這一天,全民放假,使兒女能夠放下工作探望父母,兒孫可以暫停學習問候爺爺,鄰家的孩子可以知道樓下的阿婆要過節(jié)了。人們也可以放下手中的活計,放飛心情,提升思想文化水平。這其實都有助于家庭的和諧、鄰里的和諧、社區(qū)的和諧乃至整個社會的和諧。
倘若重陽節(jié)作為法定節(jié)日,就有機會與周末相接,形成一個三天的小假期,特別適合探親訪友,或作短途參觀旅游。而重陽節(jié)外出登高游樂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特點,也正是現(xiàn)代旅游的最基本的要素。
從假日的時間分配上來看,春節(jié)(加上除夕、元宵),清明、端午,都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只有中秋,而中秋還可能與國慶重合。因此增加一個重陽節(jié),也顯得均衡;從假日經(jīng)濟拉動國民消費、特別是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角度出發(fā),顯然也是利大于弊。有時機才會有商機。
現(xiàn)在,政府已將傳統(tǒng)節(jié)日清明、端午、中秋定為國家法定假日,但卻將“重陽節(jié)”遺漏了,致使目前的重陽節(jié)仍是一個亟待關注而又缺乏關注、冠之以美名而又缺少內(nèi)涵、流于形式的節(jié)日。其實,當重陽節(jié)被賦予一個現(xiàn)代節(jié)日的“特殊”內(nèi)涵后,是一個完全可以做到精神文明與物質(zhì)文明“雙贏”的節(jié)日。當代重陽節(jié)在推陳出新、傳承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方面,符合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具有得天獨厚的發(fā)展優(yōu)勢。
此外,重陽節(jié)在國外也是一個有影響的節(jié)日,日韓東南亞,至今還或多或少地保留著一些民風古跡,倘若某日某國再來一個重陽“申遺”,教我們愧對祖先愧對子孫。“端午”之爭是前車之鑒,重陽節(jié)列入法定假日的建議,理應引起我國政府的重視與早日實施。
四、重陽節(jié)慶文化的開發(fā)建設思路
最后以重陽節(jié)為例,總結(jié)一下節(jié)慶文化建設的總體思路。
第一是提升人氣。得益于數(shù)年前出臺的“法定假日”政策,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tǒng)節(jié)日迅速聚集了人氣,尤其是在年輕人中提升了知名度。相比之下,重陽節(jié)就很寒酸了。數(shù)年前我們曾在重陽節(jié)前后調(diào)查過大學一年級學生“最近有什么節(jié)日?”學生多半不知,有的回答“萬圣節(jié)”(萬圣節(jié)在10月31日)。湊巧問到一個剛畢業(yè)參加工作的文科博士,竟也不知哪天是重陽節(jié)!缺少了年輕人的參與,文化傳承就是一句空話。重陽節(jié)是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的文化財富,如果先設為法定假日,就可能讓年輕人記住這個特殊節(jié)日并積極參與到這個節(jié)日中來。一味指責年輕人“崇洋節(jié)”是不客觀的。
第二是突出符號。端午的節(jié)日符號是粽子、賽龍舟等,其指向是懷念先賢的內(nèi)涵;中秋節(jié)的節(jié)日符號之一是月餅,其指向是團圓平等的理念。重陽節(jié)的節(jié)日符號是什么?也許有人會說“重陽糕”,可這一天有幾人在吃重陽糕?此糕與平日我們所吃的糕有何區(qū)別?古代的重陽糕,有“獅蠻栗糕”、“春蘭秋菊”、“食祿糕”、“菊花糕”等多種,別具含義。除了重陽糕,重陽節(jié)還有別的節(jié)日符號嗎?這些符號和重陽的文化內(nèi)涵有何關系?這些都值得我們重點把握以便突出。
第三是強調(diào)儀式。但凡節(jié)日,必有儀式。重陽節(jié)的傳統(tǒng)儀式是登高遠游和敬老祝壽。但就今日而言,與春節(jié)等傳統(tǒng)節(jié)日儀式相比,重陽之儀式已經(jīng)被國人淡忘得差不多了。且不說這天登高遠游對絕大多數(shù)人而言是難以實現(xiàn)的奢望,就是以單位、機構的“工會”、“領導”向老人“送溫暖”、“獻愛心”而完成的儀式,也是一種別無選擇的儀式,已經(jīng)淪落為一種“形式”。它與我們大多數(shù)人無關。
第四是重建功能。重陽節(jié)之功能除了突出“敬老”之外,還應重建其他功能。例如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祈求平安健康,每個未成年人都可以接受父母賜予的“愿兒百事俱高”,每個已出嫁的女兒都可以回家食糕謂之“歸寧”。又如怎樣發(fā)揚傳統(tǒng)菊文化抒發(fā)君子懷抱的正能量,挖掘調(diào)節(jié)身心健康的功能等,同樣也值得我們研究。歷史上的重陽節(jié)早就演化成了一個多功能的傳統(tǒng)節(jié)日。
第五是積極創(chuàng)新。當代中國社會面臨人群的大遷移,試問月圓之夜,一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蟬娟”能否扛起幾千萬打工仔、農(nóng)民工千里之外的思念之情?如果這是中秋文化功能的創(chuàng)新問題,那么面對老齡社會的到來,重陽節(jié)之“敬老”,就應圍繞老年人的需要開發(fā)老年文化和老年經(jīng)濟等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共同構建和諧的老年社會。
第六是享受詩意。既是節(jié)日,本該不同于平日的瑣碎與匆忙,尤其是重陽這樣原本就充滿了詩意的節(jié)日:登高、賞菊、飲酒、賦詩、看望父母,還有插茱萸、吃重陽糕等等。孟浩然的“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每每把我們帶到古人對重陽賞菊的無限憧憬和期待的意境中,“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更是叫我們領略了古人在重陽那天的浪漫與詩情畫意!可是今天的我們像完成任務似的過節(jié)。在這個動輒奢言創(chuàng)意的時代,筆者卻以為就節(jié)日而言,真正的創(chuàng)意應來自于詩意,而詩意的出現(xiàn)需要閑暇的心情和高雅的文化。
[責任編輯]蔣明智
黃意明(1963-),男,上海人,哲學博士,上海戲劇學院公共課教學部教授。(上海,200040)秦惠蘭(1962-),女,上海人,文學碩士,上海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副教授。(上海,200234)
* 本論文為文化部項目“學校社區(qū)家庭結(jié)合的新禮俗建設:以慶典為例”(項目編號:14DH59)的階段性成果。
K890
A
1674-0890(2017)05-1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