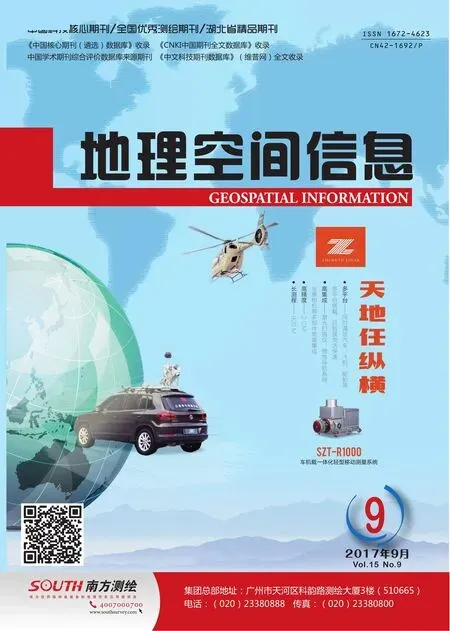汕頭市潮南區洪澇災害風險區劃研究
王 航,鐘丹秀,朱 筠
(1.韓山師范學院 旅游管理與烹飪學院,廣東 潮州 521041;2.河南大學 環境與規劃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汕頭市潮南區洪澇災害風險區劃研究
王 航1,2,鐘丹秀1,朱 筠2
(1.韓山師范學院 旅游管理與烹飪學院,廣東 潮州 521041;2.河南大學 環境與規劃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以區域系統災害論為理論基礎,綜合考慮生態環境和人類經濟活動因素,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評價指標,構建評價模型。運用GIS技術和空間統計方法,對汕頭市潮南區進行致災因子危險性﹑孕災環境敏感性和承災體脆弱性分析,得到潮南區洪澇災害區劃圖和潮南區各鄉﹑村風險指數表。結果表明,陳店鎮﹑雷嶺鎮和井都鎮洪澇風險系數最大,風險區域呈塊狀和條狀分布,受河網和地形因素影響較大;中度風險區域多零星分布于次級風險區域內,受人口影響明顯。通過實地驗證可知,風險區劃結果與災情分布基本吻合。另外,細化到村級的風險系數表,也可為實施村級災害治理提供參考依據。
GIS技術;洪澇災害;汕頭市

在全球變暖影響下,各種極端天氣頻發,氣象災害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呈明顯上升趨勢[1]。據統計,在全球各類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中,洪澇災害占據了40%[2]。在中國,每年平均要發生12次范圍較大的強降水天氣過程,最高年份達18次(1998年),由此引發的洪澇災害平均每年為5.8次。僅2015年1~8月,已有29省(區﹑市)1 810個縣5 932萬人遭受洪澇災害[3]。目前,國內外在大尺度洪澇災害形成機理﹑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災害風險區劃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成就[4-9],但鮮有區縣﹑鄉鎮級別的洪澇災害研究成果。近年來普遍發生的中小型洪澇災害,其孕災環境多為區縣﹑鄉鎮地貌單元復雜區域,災害誘因多具有區域典型性,災害區劃和風險管理仍是困擾災害治理的難題。因此,有必要進行小尺度的洪澇災害風險區劃研究。
本文在分析洪澇災害發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了人類活動規律,以村為評價單元,利用GIS技術和綜合指數方法對災害指標進行量化處理與評價,得到研究區洪澇災害風險區劃圖和村級風險指數表。細化到村級的洪澇風險評價方法,一方面便于探討與發現災害前期演變機理;另一方面有利于決策人員從微觀尺度上把握洪澇災害防治工作,便于把災害風險區劃工作落到實處,提升洪澇災害防治工作的執行力度。
1 區域概況
汕頭市潮南區是廣東省汕頭市西南部的一個城區,西接普寧市,多臺地與階地;南部為大南山,多為高丘與坡地;北部練江自西向東橫亙全境,形成練江平原;東部為南海,自東向東南由海積平原漸變為海邊陡崖。整體地勢北低南高,海洋性氣候明顯,降雨多而集中,年均降雨量超過1 700 mm,每年4~9月雨量占全年雨量的78%~83%。轄區內有峽山街道﹑陳店鎮﹑司馬浦鎮等11個鎮。以陳沙公路為界,路北為練江平原區,聚集著潮南區87.5%的人口,人口密度最高的峽山街道達到5 651人/km2;路南為大南山區,人口稀疏。潮南區經濟增長主要以密集型加工業為主,產值占全區GDP的60.1%。
2 數據來源及技術路線
2.1 評價指標選擇和權重確立
區域災害系統論認為:災害是社會與自然綜合作用的產物,區域災害系統是由致災因子﹑孕災環境和承災體共同組成的地球表層異變系統,災情是這個系統中各個子系統相互作用的結果[4]。洪澇災害的誘因很多,對潮南區而言,暴雨洪澇最常見﹑且威脅最大。暴雨洪澇的形成過程劃分為產流和匯流兩個部分,產流通過徑流分布得以體現,匯流則主要取決于河網密度和地形特征。孕災環境的敏感性和承災體的脆弱性也是災害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并與人類經濟活動密切相關。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和現場取證的基礎上,本文以降水﹑河網等一級和二級指標要素構建了洪澇災害風險評價模型(見表1)。評價指標確定后,采用層次分析法獲得權重值。

表1 風險評價指標選取與權重表
2.2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所用氣象數據主要來源于廣東省水利廳汛情發布系統,人口及經濟數據來源于潮南區統計年鑒,ASTER DEM數據和影像數據源自地球科學數據共享平臺。其中,氣象數據采用2012年8月~2014年12月潮南區區內及周邊11個水文站29個月的日降雨數據﹑3 h內降雨量大于50 mm的降雨頻度數據;地圖基礎信息為以粵S(2012)051號為底圖矢量化所得。
借助遙感影像處理平臺Erdas 2014,對2014年12 月的ETM+影像進行解譯與分類;再運用GIS的空間數據管理和空間分析功能,進行洪澇災害影響因子數據的編輯與處理;最后采用綜合指標法構建風險評價模型。

式中,H為綜合危險性指數;Hi為各影響因子的危險性指數;Wi為各影響因子的權重;n為影響因子的類別數。
3 風險性評價
3.1 致災因子危險性評價
汕頭市潮南區每年4~9月會受到約3.5個熱帶風暴影響,該時期降雨量占全年的82%以上。據以往資料顯示,強降水和持續降水是造成洪澇災害的主要誘因。選取11個水文站29個月的降雨總量作為各站點總降雨強度。另外,3 h內降雨量大于50 mm屬于中國暴雨橙色預警信號第三級別,在廣東屬第 二 級別,故以11個站點29個月中每3 h內降雨量大于50 mm為1次,依次累加獲得降雨頻度數據。根據兩個指標創建空間數據庫,運用Kriging插值法生成10 m×10 m柵格數據,經標準化處理后,得到降雨強度圖和降雨頻度圖(圖1﹑2)。根據表1權重指標,依照綜合指標思路,對兩幅圖進行空間疊合分析,得到致災因子危險性區劃圖(圖3)。
由圖1可知,潮南區各鎮降雨強度在空間上呈顯著的遞變規律,以雷嶺鎮為中心向內陸輻射遞減。降雨頻度的分布規律基本與圖1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英鎮處有一明顯凸出,降雨頻度陡增,該現象為受兩英鎮秋風水庫影響所致。從圖3可知,致災因子的危險性大致表現為由南向北遞減﹑由沿海向內陸遞減。雷嶺鎮危險性最大,峽山街道危險性最低。通過查閱歷年汕頭地質災害資料和對比引起汕頭潮南區洪澇災害的臺風“海貝思”﹑“尤特”相關材料,可驗證圖3的正確性。

圖1 降雨強度圖

圖2 降雨頻度圖

圖3 致災因子危險性區劃圖
3.2 孕災環境敏感性評價
3.2.1 地形影響度
地形因子對洪澇災害的影響主要通過海拔和地形起伏度兩個指標來反映。海拔用高程值表示;地形起伏度用高程標準差表示,高程標準差越小,地形起伏度就越小,對洪澇災害的影響就越大(圖4)。

圖4 地形起伏度圖

圖5 地勢圖
潮南區的地勢表現為南高北低(圖5),南部為山地,系大南山一支,延伸至南海。地質構造屬燕山運動以來的深度斷裂帶,至今仍在活動。潮南區南部除雷嶺鎮(中心區域)外,其他區域地勢都處于40 m以上,成為潮南區的主要產流地。練江西北部為低矮山地,東南部為海岸陡崖,使得練江中下游平原形成類似U 型的谷地,成為潮南區的主要匯流區。實地測量發現,練江中游司馬浦和峽山(除峽山塔外)沿岸的海拔為0~-9 m,下游井都沿岸海拔為-5 m,出海口海拔僅為-3 m,河道流經地區地勢高于河流入海口,是造成雨澇災害的直接原因。
3.2.2 徑流影響度
徑流是指在重力作用下沿著地表或地下流動的水流。地表徑流又分河槽流和坡面流兩種。降雨落到地面時經過植物截留﹑下滲﹑填洼和蒸發后,剩下的雨水就沿著地表坡面向低處流下,形成坡面流;而植物截留﹑下滲與地表的土地利用類型有關。河槽流則與河網水域有關,故徑流因素選取河網水域和地表土地利用類型進行分析。
根據潮南區土地利用類型圖,以濕潤土壤曲線系數CN[10]為參考值(表2),結合區域河網水系,得到水系影響度圖(圖6)。對圖6和土地利用類型影響圖進行地圖代數計算,得到孕災環境敏感性區劃圖(圖7)。

表2 土地利用類型CN系數分級

圖6 水系影響度圖

圖7 孕災環境敏感性區劃圖
3.2.3 孕災環境敏感性
潮南區中部及雷嶺河流域,建國以來修建有19座水庫,主要用于潮南區及周邊淡水供給和蓄洪,經實地調查已有11座水庫干枯,剩下的8座也因管理缺失,多處崩堤,因此仙城﹑兩英﹑成田﹑紅場4鎮水庫所在區域均為孕災環境敏感性較大的地區。實地調查發現,由于平原區人口密集,經濟活動頻繁,生活﹑生產垃圾堆入河道岸邊,導致河泊水體富營養化嚴重,常年浮生植被茂密;同時高度密集的城鎮及人類工程建設,造成許多人工邊坡,水土流失嚴重。每年汛期,河網排水不暢﹑泄洪口阻塞等情況經常發生。由圖7可知,沿練江的6個鎮土地利用類型多以水田﹑建設用地為主。因水田土壤水分飽和度較高,下滲能力差,所以水田的敏感性較大;而建設用地的地表為水泥地,雨水不易下滲,容易形成積漬。其他鄉鎮也因水庫﹑坑塘等原因,孕災環境敏感性強。
3.3 承災體脆弱性評價
致災因子危險性和孕災環境敏感性反映了洪澇災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大小和空間分布狀況,而實際造成的危害還與承災體的承受能力有關。洪澇災害造成的損失度取決于當地經濟價值的密集程度[11]。同樣的洪澇災害,在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地區造成的傷害遠遠高于人煙稀少﹑經濟落后的地區。本文選用人口密度和每km2的GDP定量表示承災體的脆弱性。

圖8 承災體脆弱性圖
由圖8可知,峽山街道和陳店鎮的脆弱性最高,其次是兩英﹑司馬浦和臚崗3個鎮。峽山街道和陳店鎮地少人稠,人口密度和地均GDP均分別居潮南區的第一﹑二名,是潮南區的經濟重鎮(街道),密集型企業多,勞務人口多。南部的紅場鎮﹑雷嶺鎮和成田鎮均屬地廣人稀的山區,基本以第一產業為主。
4 風險性評價
對洪澇災害致災因子危險性﹑孕災環境敏感性和承災體脆弱性進行地圖代數計算,得到潮南區洪澇災害風險區劃圖(圖9);并統計了潮南區各鄉鎮﹑行政村的洪澇災害風險指數(表3),風險指數越大,風險性越高。

圖9 洪澇災害風險區劃圖
從圖9﹑表3可以看出:雷嶺鎮﹑井都鎮﹑陳店鎮和隴田鎮的部分地區危險指數最高。雷嶺鎮以雙溪為中心的15個村風險性最高。這15個村是雷嶺鎮地勢相對較低的區域,與雷嶺峰的落差達到515 m,同時又是雷嶺河3條支流的交匯地,即為產流﹑匯流交叉地帶,暴雨洪澇時易造成較大災害。由圖9可知,雷嶺河流域最危險的區域呈帶狀分布,該分布與15個村的條狀分布格局相吻合。

表3 潮南區各鄉鎮洪澇災害風險指數表
井都鎮所有村落都位于風險性最高的3個級別里。這與井都鎮靠近海邊﹑地勢低洼(全鎮海拔基本處于1 m以下)相關。暴雨時練江1 346.6 km2的集水區匯向這唯一的入海口,易因排水不暢和海水倒灌形成洪澇。隴田鎮東部鄰接井都鎮危險性較高的8個村,也極易受井都鎮災情影響。因此,井都鎮產生洪澇的原因主要在于入海口瘀積,河道排水不暢。
陳店鎮除了溝湖﹑福潭和三合3個村外,其他村都處于風險性最高的3個級別里。陳店鎮因地勢低﹑水網密集﹑人口密度大而導致綜合風險性較大。司馬浦鎮﹑峽山街道北部和兩英鎮西南部主要因河網水域多而導致風險性較大。司馬浦鎮和峽山街道北部為練江及其分支,地勢低平﹑河道曲折﹑湖泊密集。兩英鎮東部為兩英溪與秋風嶺水庫,水量大﹑水流急;兩英溪是練江最大的支流;秋風嶺水庫是潮南區最大的水庫,也是調控兩英溪流量的主要水庫,若雨量過大,易給兩英溪下游帶來較大的危害。
紅場鎮的風險性最低,風險指數為3.849~5.126。紅場鎮是一個純農業山區鎮,海拔高﹑河網密度低﹑植被覆蓋率高,豐富的植被分布能調節徑流﹑涵養水源,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削弱洪峰,延緩洪峰的到來,為下游洪水的排泄爭取更多的時間。
綜上所述,通過圖9可以發現,潮南區洪澇災害危險級別最高的區域在陳店鎮﹑峽山街道﹑兩英鎮和隴田鎮,呈塊狀分布并沿塊狀中心呈輻射狀,危險等級依次降低。究其原因,風險性最高的塊狀區域多為水庫﹑人口聚集區,致災能力強而承災能力弱,加劇了洪澇風險暴發的可能性。另外,風險級別最高區域在井都﹑雷嶺兩鎮呈明顯的帶狀分布,在司馬浦鎮也存在較小的帶狀分布,這種空間分布表明該區域受地表徑流影響嚴重,而河道在產流﹑排水方面功能弱化,使得孕災因子指數增大。通過實地調查發現,河道兩岸因地勢相對平緩,成為人類活動集聚地,同時產生的垃圾也成為阻礙河流排水﹑泄洪的不利因素。
5 結 語
本文運用區域災害系統理論,借助GIS和RS技術,進行了致災因子﹑孕災環境和承災體3部分的計算,得到潮南區洪澇災害風險區劃圖和潮南區各村風險指數表;并通過實地調查與取證研究證實,風險區劃圖能真實客觀地反映潮南區洪澇災害現狀。細化到村級的風險評價,在災害區劃評價方面尚屬新的嘗試。以村為評價單元的風險區劃為進一步實施“誰受益﹑誰出資﹑多受益﹑多出資”的多級防災減災方案,提供了一定的技術支撐和參考依據。
[1] 黃榮輝,杜振彩.全球變暖背景下中國旱澇氣候災害的演變特征及趨勢[J].自然雜志,2010,32(4):187-195
[2] 彭廣,劉立成,劉敏,等.洪澇[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3:1-35
[3] 蔣琪.國家防總:今年全國已有154個城市因暴雨發生內澇 [EB/OL].(2015-08-19)[2016-04-22]. http://env.people. com.cn/n/2015/0819/c1010-27482438.html
[4] 史培軍.三論災害研究的理論與實踐[J].自然災害學報,2002,11(3):1-9
[5] 周成虎,萬慶,黃詩峰,等.基于GIS的洪水災害風險區劃研究[J].地理學報,2000,55(1):15-24
[6] 于文金,閆永剛,呂海燕,等.基于GIS的太湖流域暴雨洪澇災害風險定量化研究[J].災害學,2011,26(4):1-7
[7] 曹瑋.洪澇災害的經濟影響與防災減災能力評估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13:7-15
[8] Esteves L S .Consequences to Flood Management of Using Differe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to Estimate Extreme Rainfal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3,115(3):98-105
[9] Favre A C,Adlouni S E, Perrault L, et al. Multivariate Hydrological Frequency Analysis Using Copulas[J].Water Resources Research,2004,40(1):290-294
[10] 郭昳,程曉莉,張全發,等.陜西佛坪土地利用對徑流變化的影響分析[J].人民長江,2009,40(24):26-28
[11] 田國珍,劉新立,王平,等.中國洪水災害風險區劃及其成因分析[J].災害學,2006,21(2):1-6
P208
B
1672-4623(2017)09-0049-05
10.3969/j.issn.1672-4623.2017.09.016
2016-05-12。
項目來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31470021);河南省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遙感解譯與應用資助項目;潮州市科技支撐資助項目;韓山師范學院青年資助項目(LQ201303)。
王航,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遙感生態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