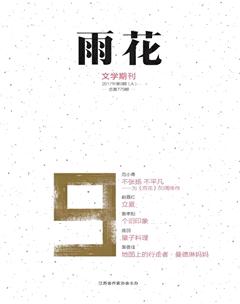立夏
趙荔紅
1
薔薇拼盡最后氣力,吐放出濃郁而頹敗的香氣。一夜風雨,滿地花瓣,半落了花的花萼掛著水珠,呆呆裸呈著;她們的花房會變胖,過些時日,會變成紅色。我掃盡花瓣,傾入泥中,從哪里來,歸哪里去吧!梅花、杏花、油菜花,櫻花、桃花、垂絲海棠,漸次開過了。希臘神話中,春夏之交,少女們要祭祀阿多尼斯送春;中國傳統則是要到芒種節,少女們才將絲線纏繞在花樹上,又用柳條花瓣編成轎馬,祭祀花神送春。立夏時節,花神還在大地徘徊,那些米碎小花,是她漸薄漸淡的衣裙碎片。而所謂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如果說四月是女性的、陰柔的、未定型的;緊接而來的五月,則是男性的、陽剛的,一切都豎起、挺立,一切都在生長,力量回升,血脈擴張,骨骼噼噼啪啪爆響,萬物已悄悄做成了胚胎,一切都定型了。
不必為嫵媚之繁花四月的流逝悲嘆。樹木是五月的主宰。薔薇花盡,枝葉卻洶涌地覆上短垣,與回綠的爬墻虎錯疊;新竹終于停止拔節,分出枝杈,過不了幾天,就綴滿新葉了。四月里樹們伸出毛毛小手、粉紅小拳頭,微張著小眼睛,他們那些有白絨毛的小葉片,在五月初的暖陽中,盡情呼吸、舒張、伸展。早安,我的樹兄!眼前所見,是怎樣色彩富麗的樹木啊:明紅、橘紅、赭紅的紅楓、槭樹與紅葉李;銀杏頂著滿頭滿腦平庸綠大半年,只為了十二月那數日的明黃絢爛;梧桐送走最后一批絨毛種子,嫩葉已有巴掌那么大,明凈透亮的綠,不帶一點銹斑;還有香樟的鵝黃嫩綠,松柏的積年暗綠……層層染染的綠,光影閃爍中,又變化出多少層次呢?
向復旦走去,國順路兩邊的香樟樹,熱情地迎上來,又沉默地退向我身后。當我腰肢纖細身穿碎花連衣裙時,他們也還是小樹,蓬著童花腦袋站立路邊看西洋景,每天我歡欣問候:早安,我的香樟樹!他們就報以快樂的搖曳。如今他們已長成大樹,而我常是行色匆匆、心思重重,許多時間竟完全忽略他們的存在。但今天,是鵝黃嫩綠,喚醒了我;青澀香氣,充盈著我。香樟樹渾身上下枝葉樹干原是香的,而立夏前后幾日,香氣尤盛。仔細看,原來繁茂枝葉間,正開著一叢一叢米碎花,呈總狀花序,每朵也有六片花瓣,微雕一般,花與葉都是青黃色,不留心觀察,很容易忽略過去,遠看不過是一樹的鵝黃葉子。五月涼風,枝葉搖曳,米碎的花,雨一般落下,滿地點點青黃,眨眼就與塵泥混同了。這些五月的米碎花,在八九月結成青色果子,十一二月轉成了黑色漿果,被鳥啄食了,掉落了,或只是干干地掛在枝上,直到來年春天……
一年一年,多少重大事件流過,我記得的只是一個個瞬間,那些瞬間,因了一個物件、一絲香氣、一種景象,過去時光,埋藏于記憶深處的,便會如沉渣泛起,影像閃回,發黃而明晰—某年,去麗水看三國李冰造的通堰渠,十幾棵巨大香樟樹臨溪而立,溪水潺潺,我與友人緩緩而行,他一路叫“好香”,我一路嗅著掌心捋下的青黃小碎花。又某年,我和土豆在南潯嘉業藏書樓,河邊也有數十棵百歲香樟樹,見證著藏書樓主人,是如何傾三代財富,藏書百萬,印刻無數,藏書樓又是如何躲抗戰躲文革,僥幸地保存下來;當時我們坐在樹下讀書,我讀的是《仲夏夜之夢》,河岸邊有人唱昆曲《牡丹亭》:“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當時,香樟花不停地落,那米碎的一地青黃,那五月涼涼的風,風中的香氣,水面的清疏,婉轉之歌吟,流水落花春將逝,仲夏之夜尚未至……
2
光華樓敞亮的教室里,土豆在上盧梭的《懺悔錄》。我熟悉的愛人,站在講臺上,似乎是另一個人;他沉思地望著前方某個點,微微向前傾著身子,將思維層層推進,間或問學生:“你們說是不是?”這個問句,僅僅是一個逗號,一個休止符,一下喘息,并不影響他的思維的邏輯推進。黑板右側有他板書的幾個字——“改造思想”,這是他附帶講的《論戲劇》開頭一章所涉內容,盧梭批評,啟蒙思想家與他們所批判的教會,有著共同特征,都試圖改造人的思想。土豆說他開這門課,只想引導學生如何去讀一部經典,像盧梭一般,學會自我學習與獨立思想,他說,大學首先是培養一個人,其次才是傳授知識。學生們豎著耳朵靜聽,我分明看見,那個我,那個瘦弱的、迷惘而愛幻想的18歲女孩,也正坐在其中……當時的我們,正值生命的春天,如今已邁入秋季;當年的學生,成長為老師,當年的老師,都在哪里呀?
“叮——”陌生、幾乎難以覺察的下課鈴聲,克制、清冷、簡潔,這種鈴聲,不是我的小瑪德蓮餅干,我的記憶里沒有光華樓,他那灰色結實的身影當年還沒可怕地聳立在草坪上……劃痕桌椅,泛潮黑板,粗野嘶啞的鈴聲,昏暗的宿舍走道,亂糟糟的廣告招貼,經典電影,實驗話劇,“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八九十年代大學校園,留存下的那些肌理毛糙、思緒紛雜、激情四射的未定型的東西,已紛紛進入現代“改造”“規制”中,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被強有力的手反復擦拭、重新書寫,只留下模糊的痕跡,以為是幻覺——21世紀的今天,矗立在我們眼前的只有這一幢整潔明凈、一絲不茍、內臟精密、無所不有的光華大樓,在這個現代城堡面前,一切終歸于寂靜,萬事皆中規中距。這當兒,土豆還在講18世紀盧梭的自我學習、獨立思想,真好似一只秋蟬,盡力地拖長沙啞的、聲嘶力竭的最后鳴叫。
秋蟬聲嘶力竭地鳴叫,是慕戀夏日那盛大、浩蕩、洶涌的激情吧?
我先到光華樓前的草坪等土豆。修治整齊的小葉女貞,開著細密如雪的白花,等到潔白的花變成淺咖啡色時,梔子花又將開了……土豆從光華樓的陰翳門洞下走出來,深藍衣服褲子,陽光將他的面容照耀得很光潔。他朝我走來,思維卻停頓在盧梭那里。他坐下來,意猶未盡,繼續對我講《懺悔錄》的結構,講章節間的奇妙承接,說是像交響曲的一個個樂章;講他對某個細節的理解,研究者的一些錯誤認識。他講這些的時候,眼神深邃、發亮,凝結著多么深切的熱愛啊!
去年,正是立夏后一周,我和土豆從法國里昂到尚貝里去,因為盧梭說,在尚貝里,他度過了一生中短暫而幸福的時光。我們從尚貝里城區出發,步行前往沙爾麥特——當年盧梭與華倫夫人隱居的郊外農莊,如今是盧梭博物館。盧梭這樣描寫在沙爾麥特的生活:“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見媽媽,我感到幸福;離開她一會兒,我也感到幸福;我在樹木和小丘間游蕩,我在山谷中徘徊,我讀書,我閑暇無事,我在園子里干活兒,我采摘水果,我幫助料理家務——無論到什么地方,幸福步步跟隨我;這種幸福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確指出的事物中,而完全是在我的身上,片刻不能離開我。”endprint
五月的法國原野,真是色彩炫麗的油畫,我因此很理解印象派畫作并非主觀之印象,恰好是現實主義,畫家捕捉到了瞬間之現實印象,正如中國水墨畫也是現實主義,只要你到桂林山水或霧中的廬山、黃山去看看。早晨十點,光線明麗如水,走過幾幢光影鮮亮的房子,拐上盧梭路,越過一條平緩寬闊的河流,在小徑分叉之際停下來,路標指明,右邊上山的泥石小路就是去往沙爾麥特的。這條泥石小路,是否與當年一模一樣?這是盧梭反復走過的神奇之路啊!若如《懺悔錄》描繪,每天清晨,他就是從這條路一邊走一邊大聲地祈禱?我們在大路上走得一身熱汗,過分通透的日照,將頭臉烤得火辣辣的,拐進泥石小路,如飲冰泉,通體清涼。越往山上走,樹木越是蔥郁,兩邊又是葡萄園,一條蜿蜒小溪隱蔽在濃密樹木中,有時露出一段清流,有時只聽見潺潺水聲。周身流溢著樹木草葉的芳香,腳下是我不認識的花草。第一次去沙爾麥特過夜那日,華倫夫人半途下轎,和盧梭慢慢走著山路,突然指著籬笆邊一朵藍色小花說:“瞧!長春花還開著呢!”長春花學名catharanthus roseus,她說的應是藍珍珠,花瓣藍色,中間白眼,四五月間開,華倫夫人嘆息它“還開著”,和盧梭第一次前往沙爾麥特,正是初夏吧?三十多年后,歷經艱辛的老盧梭,再次看見那種花,高興地叫起來,他想起的是“媽媽”說這種花的聲音、姿態,以及在沙爾麥特的生活與思想的全部吧?我一路搜尋這種藍色長春花,對每棵樹、每枝花都報以敬意,他們或曾獲得過盧梭的注目(不死的植物哦,你的種子四處飛撒,生命也循環再生)。土豆在前面走得遠了,小小的沉思背影,忽而隱在樹影里,忽而顯現在光亮中,我快步跟上,如同盧梭說的,“那一天正是雨后不久,沒有一絲塵土,溪水愉快地奔流,清風拂動著樹葉,空氣清新,晴空萬里,四周一片寧靜氣氛一如我們的內心”。我們一路走,一路聽水聲鳥鳴雙重奏,真渴望這條神奇、充滿香氣的路一直延伸下去。
幾乎錯過!一塊路牌,字跡很小。對面一條岔道,拾階而上,小徑幾被花草遮蔽,蘚苔覆蓋石階(花徑不曾緣客掃?)。走了十來米,幾棵高大樹木掩映下,露出一幢二層樓房,這就是盧梭博物館了。打開木柵欄,進門(蓬門今始為君開?),樓下靠左一間,坐了一位老婦,賣些盧梭照明信片;另外兩間,是盧梭的臥室、工作間,掛些盧梭及華倫夫人不同時期畫像,沒有生平年譜,沒有遺物、著作版本等,與這位偉人的貢獻地位比,實在太過簡陋。木樓梯上到二樓,有一間擺設精致些,是華倫夫人的臥室。咯吱響的木地板,斑駁圓鏡,陳舊的美婦畫像。家具是否為舊物?靠窗一張雙人床,垂著碎花蚊帳,那個名垂后世、單純熱心的婦人就是在此輾轉她多汗豐腴的身子?盧梭每天早晨散步回來,看見樓上百葉窗打開了,就知道“媽媽”起床了,立即飛奔上來。
房子左側有個敞開涼亭,門前全地散擺些桌椅供人休憩,右側有條小徑。小徑上方是弧形的花藤枝葉拱廊,穿過藤花廊,可繞到后花園,與葡萄園、果樹林連成一片,想來當年都是華倫夫人買進的田產。花園呈長方形,有個圍著的小苗圃;中間一條直道通向房子后門,分割出兩塊齊整草坪,散放著幾把鮮艷的帆布躺椅。一對中年夫婦偎坐在右邊,戴著遮陽鏡,笑著,小聲說著話。我們就坐在另一邊。空氣澄明,陽光直射,明亮得幾乎睜不開眼睛,風從山丘上的葡萄園吹來,向山谷的果樹林一層層擴散,極目馳騁,開闊至極,阿爾卑斯山好似近在眼前,兩個山峰,像是中國的山水筆架,又如兩個駝峰,常年白雪的山頭被陽光映得閃閃發亮。萬籟俱靜。盧梭也是這樣與華倫夫人在此閑話,吹著山上的風,與蜜蜂、蝴蝶、花樹、蟲鳥一起?真想與土豆隱居于此。回望那幢素樸靜立的房子,陽光勾勒出發亮的屋脊,面朝阿爾卑斯山的墻體隱藏在青幽陰影中。于是我體會到盧梭在《懺悔錄》第六章引的賀拉斯詩句:
我的愿望是:不大的一塊田地,
宅旁有一座花園,一個水聲潺潺的泉眼,
再加上一片小樹林。
而諸神所創造的,
當然不止此。
3
河岸植著許多楊樹,每棵都有十幾米高,密集排列,但那蕭蕭疏疏的姿態,使得這片林子并不憋悶,倒極有風致。樹下草地,年輕的青綠,鋪一層白色野花。是什么花開得如此繁盛?
原來滿地鋪的,是一層薄薄“白絮”,如雪卻不冰冷,似鹽又不堅硬,比蠶絲要白一些,并不結成橢圓蠶蛹,較蒲公英花密實些,手感極柔綿,卻不及棉花厚實……她們從何而來啊?一陣風過,點點“白絮”又飄飄揚揚下來。我揀拾起一小團白絮,搓捏,柔棉中有一點堅硬,是楊樹的種子。白絮來自小而硬的黃綠果子,果子開裂,白絮就爆出來。種子躲在白絮中,大膽地從十幾米高的樹上往下跳,順風飄蕩,落在泥土中,掉在石子路上、荊棘叢里的,順著水漂流,或被人的頭發、衣裳糾纏,帶到街市,化作浮塵……可惜!并沒有幾顆種子會長成參天大樹。便是如此,種子還是每年生長,每年掉落。
擇了一棵最大的楊樹,躺在樹蔭里。那些白茸茸花種,貼著我的鼻尖、嘴唇。頭上的天空,異乎尋常無限透明的藍,只描畫幾條枝椏、幾簇葉片,再無別的物事了,世界是那么簡單!一棵楊樹,竟能分叉出那么多枝椏,每一條枝椏,又生長出多少簇葉片?這些心形葉片是著綠裙的少女,有細細的脖頸,她們十幾片、十幾片聚在一起,站在柔軟枝椏上,甩著綠袖子,上下左右搖晃著,跳躍著,舞蹈著,唰啦唰啦鬧熱地議論著、喧笑著。樹干則一動不動,如穩重肅穆的老者,靜聽少女們沒心沒肺的笑鬧。亞里士多德在《動物志》中說:“植物無法移動,沒有感覺,許多動物則不能思考。”但我分明看見了楊樹的精魂。有哲人說,一棵樹的心,是在樹干與根的交界。那么這些心形葉片呢?是樹的頭發?手腳?抑或那萬千葉片,就是樹的心靈的無數反應,是他的精魂的萬千幻化。俄耳甫斯另有一種說法:靈魂源于外界,通過呼吸深入到生命體內,對此,風起了循環作用。如今風舞動著萬千葉片,正是將靈魂從外輸入楊樹體內吧?那些葉片呼呼叫喊著,喋喋大笑著,激烈訴說著,都是樹之靈發出的悲喜吧?奇怪的是,當我這邊的楊樹在舞動歡叫時,離我不遠的幾棵楊樹,卻一動不動緘默著;我這邊沉靜下來,激動的顫栗,漣漪一般,開始在那邊傳開,一開始輕微的戰栗,擴展為層層疊疊的起伏。風在樹林間穿行,將靈魂從這到那循環傳送,我的心也漣漪般戰栗起來。伴隨著風,是光的運行。光從這棵樹運行到那棵,背光的葉片墨黑,黯淡,是暮晚歸林的鳥兒;面光葉片,則有雪的光芒,白亮耀眼,不能逼視;唯有光暗重疊的葉片最為生動,在風的帶動下,光影晃動、交疊更替,沒有一絲穩定。一切皆變,一切如幻。我微微闔上眼瞼,也能感知枝葉上的光晃動不停。若是風將一條枝椏扯得過了,光就直接落在臉上,刺眼的白亮帶來一小塊熱度,轉瞬,又被密集的陰涼取代了。endprint
風停頓的間隙,楊樹喘息著,種子們撐著降落傘密密麻麻從天而降,將我的身子、身邊的草地當作著陸點。躺上一天,我就會如蠶蛹般裹在白絲里了。河流在眼前,淺淺地流,平整的河面,細密波紋上抖動著白色天光。多么緩慢,還是在流動。泰勒斯說,水生萬物,萬物歸復于水。這水畔,該會徘徊著怎樣的水澤女仙、花樹女仙、樹木青草和種子的精靈?剛巧是五月,剛巧在楊樹飛絮的時日,我們剛巧走到這片恰當的草地!換個辰光,又會遇到怎樣的風景?在這起風的下午,思緒隨風、隨水,穿行、流轉,神秘的感覺如那些白絮種子,此處彼處掉落……一切皆流,無物永駐。土豆在身邊看書,讀斯特勞斯,幾小團白絮種子掉落在他頭上,就笑說,那是靈感的種子。他終于想通了一個問題,便在白紙上寫下風傳送來的神諭。我繼續讀《在少女們身旁》,普魯斯特第一卷寫了少女希爾貝特,第二卷寫了少女阿爾貝蒂娜。從沒有一個人,如他,不注重情節推進,似乎任由一切緩慢流動,頭緒紛雜。普魯斯特的詞匯集中在:小徑,臉頰,花朵,衣裳,房間,教堂,音樂,繪畫,幻象,睡夢,夜晚,回憶,時間,譬喻,色彩,差異性,個體性。沒有固定概念,沒有固定不變的人,色彩、表情隨時間流動,在“我”的幻象中,一會兒流動到過去,一會兒延展到未來;停滯的時刻,一個少女,或者說一個名字上的少女,會演變成許多個不同少女,這個與那個,又呈現鮮明的差異性,具有獨特個性。懸崖、大海、樹木,在不同天氣,不同視角,不一樣時間里,因不同心情,發生著奇特的變化。但這僅僅是開始——直到我讀到最后一卷,才看清楚他那哥特式教堂般恢宏的、交響樂般精心構筑的完美結構。
河流在眼前,淺淺的,緩緩的,草樹盡力俯向河面,顯得河水又窄又曲折。這條河我是熟悉的,有多少時間,我們在此徘徊。20世紀末,那幫和土豆一樣年輕的博士,才剛留校任教,每周有一二天在我家聚會,一起讀書、清談、下棋、聽音樂……讀經典,談無用之事。有一回,讀莎士比亞,天氣是那樣晴朗舒爽,大家就說,到野外去。我們八個人雇了兩條船,帶了葡萄酒、咸雞、鹵牛肉、各樣零食。坐在船上,舉著紙杯笑著叫著亂碰,小船任性地飄在河上。微醺。兩岸草坡,開滿酢漿花和美女櫻,一團團粉紅云朵,要從草地升上天空。將船綁在一棵苦楝樹下,各自掏出《威尼斯商人》,分派角色……“巴薩尼奧”仰躺在大石上,拿書闔著臉,是聽鳥鳴還是遐想?戴墨鏡的光頭“夏洛克”,一手拿書,一手拽著韁繩;“安東尼奧”手指頭夾著煙,忙著說話,煙灰長長而不落;頭發微卷的“朗斯洛特”,像只猴子蹲坐在樹杈上……朗誦老是中斷,大笑,插話,糾正……當時,苦楝樹開滿紫藍色小花,那種紫藍色,有一種淡淡的憂郁,很合乎年輕的多愁善感的心,后來我也一直很喜歡這種樹,因為它叫“苦楝”,這兩個字是特別好看且令人傷感的……十幾年流逝,當年的讀書人都長大了,如每一片花瓣、每一條枝椏,伸向各自不同的方向;風,吹斷了共同價值之鏈;我們,也再難坐在同一條船上,讀同一本書了!
那天,應是立夏前后,我們的年紀,也正處于生命流年中的立夏,真如喬叟老頭唱的,我們這些年輕的——
他寧可床頭堆上二十本書,
也不要提琴、豎琴和華服;
書外裝著紅黑兩色的封皮,
書內是亞里士多德的哲理。
可是,盡管他是一位哲人,
但他的錢箱內卻殊少金銀。
——節自《坎特伯雷故事集·總引》
4
一彎新月,夾在兩幢樓房間,被燈光漂白,如失血唇色、拔細眉毛;在山中,她會是片利刃,尖新,光芒銳利。北斗七星,瞌睡著,昏昏沉沉、含義不明地指向北方。古書說立夏:“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城市中已不明所以,只是出行時,看鐵道沿線農家,屋前垣后,搭著架子,藤葉曼生,五月間開著黃花,王瓜是小小的,如彈丸。
今天是立夏,我笑。土豆說,立夏有什么特別呢?是呀!今日我也不過是去學校接土豆,下午一起到公園讀書,和許多日子一樣。每年都有立夏。時間是線性流動的,又是循環往復的。今年的立夏不是去年的,去年又不是前年的。明明白白看著時間流逝,我再不是那個我,你也再不是過去那個你。眼睛、脖子的痣、頭發顏色、皮膚上的褶皺,一切,悄然發生變化。但是為什么,你還是那個你,我還是那個我。
我點了立夏必要吃的幾樣小菜:春筍、蠶豆、雞蛋,說是筍能健腿腳,蠶豆明亮眼睛,雞蛋能強健心臟。五月是毒月,萬物生長,百蟲也不例外,吃了這些,強健自身,避免災害。但不知吃什么,能夠強健大腦?“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在一個精神疲敝蒼白的時代,如何可稱為“君子”?如何能“自強不息”?
春筍,呼朋引伴,一夜間,呼啦啦冒出許多。竹子是極富生命力的,給點水,就盡力冒出來,一日拔三節,幾天不理,已經長到二層樓那么高。新筍掐著嫩,立夏前后,也有沒長到二層樓那么高的,尾部還嫩著。我小時在山上,就是對著未老的竹小伙,奮力撞過去,末梢啪嗒掉下來,撿回去炒著吃,照樣是嫩。母親說,炒竹筍要配花豬肉,既能吊出春筍的鮮,又去掉新利、生澀感。今夜我點的小菜,卻是油悶春筍——將嫩春筍切片干煸,加水、醬油、白糖燜后收汁,鮮且入味,加糖也是為了去澀味。蘇州、無錫、上海一帶的油燜春筍,真是極甜,要甜而不膩方好。但有時候,我就是喜歡吃春筍的青澀氣,便只是切片干煸,加些蔥花,金黃點翠的好看,以鈷藍鈾盆盛上來,極誘人的。還有將極嫩的春筍,連殼切短,置白水中擱點鹽煮熟,這就是手剝筍,單為了吃時新氣。在江南,還有一道咸篤鮮,我在家鄉不曾吃過,當了上海媳婦,我才學會——將咸肉、春筍、鮮肉或排骨燉在一起,三種鮮味調和,鮮美異常。第一次吃這道菜,是在我婆婆上海新永安路的弄堂房子,爬上咿呀作響的木樓梯,黑暗中摸索著打開木門,隔壁廂人家與婆婆家只隔薄薄一層木板,臨街開四扇木窗子,我婆婆立在窗口洗春筍、切春筍、切咸肉鮮肉,煤爐子燒滾滾開水,咸肉、鮮肉、春筍通通放進鋼精鍋子,汆一汆,再換水,大火燒開小火燉,二三個小時下來,香味彌漫小小房間,鉆過木板縫隙,漫溢到隔壁人家去,站在樓梯上都聞得著……endprint
蠶豆。四月里蠶豆苗矮矮趴在田頭,撥開葉子,才能看見紫藍小花,蠶豆花實在不起眼,蠶豆莢子也難看,剝過后,指甲會染上黑汁。常見老婆婆,坐在小區樓房門洞,一邊聊天一邊剝蠶豆,腳下一堆咧嘴殼子。母親,你在家鄉也是如此度日吧?剝好的蠶豆,頭頂有一條眉毛,倒光蠶豆,籃子中會落下好些孤單的眉毛。我今夜點的,是土豆喜歡吃的清炒蠶豆,只將嫩蠶豆連皮滾油熱爆,皮炸開,撒一把蔥花,就可上碟,吃的是時新氣。但我母親非但要剝掉蠶豆外殼,還要去蠶豆皮,剝盡的叫豆瓣,油爆后加水燒開,然后,將洗凈的牡蠣調入淀粉,以筷子撥進豆瓣湯中,燒滾,勾芡,加點醋,就是很好吃的海蠣豆瓣湯了。我每每回家鄉,母親總要做這個湯,說要燙燙的喝才不會腥氣,她一邊說,一邊看著我喝下去;我說好喝,她就單手撐著腰,呵呵呵地笑。母親,寫下這幾行字,我是多么想念你的海蠣豆瓣湯啊,即便有豆瓣,我又能到哪里去買家鄉海邊無比鮮美的野生牡蠣呢?也無論如何,都做不出母親的味道。
至于雞蛋,我要了一份香椿炒蛋,香椿是紫紅色的,短短嫩葉一捆捆扎著,切細了炒蛋,極香。我小時候沒吃過香椿,雖覺得好,也不甚想念。傳統立夏節,得吃整個水煮蛋,小孩子們喜歡玩斗蛋,就是比試誰的蛋立得穩、不易碎,這些都與成長相關。母親用五色絲線編成蛋兜子,將染成紅色黃色的熟蛋,裝進彩色蛋兜,二三個掛在胸襟,跑起來,有意無意磕破了蛋,就吃掉了。端午節的蛋是黃色的,用艾草水煮的,連同樟腦丸、粽子,一起掛在胸前,累贅得很;我不記得吃掉多少雞蛋,只記得極討厭聞雄黃氣味,又死活不肯用艾草水洗澡,媽媽就哄,洗完澡才可以穿花裙子哦。我小時對立夏節不感興趣,因為只有雞蛋,花裙子還藏在衣柜里,要等到端午節才能穿。
一邊吃飯,一邊和土豆絮絮地說這些。步出小店,隔壁水果攤頭果子甚是誘人,又立住了看:草莓整整齊齊碼在籃子里好似匹諾曹的鼻子;青白膚色的甜瓜姑娘散發出甜香,誘你撲上去咬一口;枇杷,橘黃皮膚上蒙著白霜,流著蜜汁,口感沙甜,我小時就好奇何以難看的枝葉能長出這般完美的果子?但我偏愛芒果,他們像滿月嬰兒的胳膊,肉肉的,排著隊擠在一起睡……夜的街,浮動著各種香氣,水果的、陽光的氣味,新割草地的腥澀之氣,白日所見的香樟樹、苦楝樹、女貞樹的花香,還有一種俗而甜的香味,是含笑花。時間,會在花色上印下牙痕,又附著在花香上,顫抖地一脈脈傳遞……走過一幢高樓,又嗅到一種沁人心脾的香氣,青檸的?柑橘的?原來樓前有兩株不高的桔子樹,微弱燈光下,暗綠葉片間,成團成簇聚生著小小的青白色五瓣花,屈大夫喜桔樹,蘇東坡到宜興買房,也曾想如屈原種500畝桔樹,想想,單是嗅聞桔子花的香氣也是美事吧?這立夏夜,若是在鄉野,蚯蚓正埋頭掘土,蝌蚪變成了青蛙,一眉新月,數點小星,桔子花香氣陣陣,又該是怎樣的清新宜人呢?
盧梭說的:“我必須在冬天才能描繪春天,必須蟄居在自己的斗室中才能描繪美麗的風景。”寫下這些文字時候,立夏已過,梅雨來臨。綿綿不絕、悶熱煩擾的梅雨季。熬過這幾天,蟬聲就該大噪起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