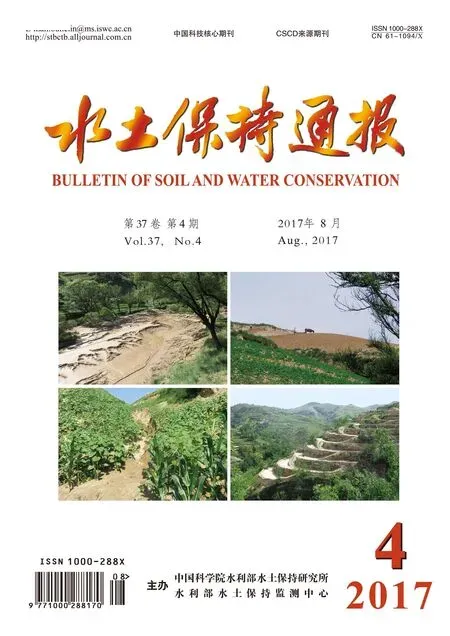不同人工植物配置對排土場邊坡水土流失的影響
楊漢宏, 張 勇, 鄭海峰, 吳麗萍, 吳國璽, 王鐵軍
(1.神華準格爾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內蒙古 鄂爾多斯 010300; 2.內蒙古自治區水利科學研究院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
不同人工植物配置對排土場邊坡水土流失的影響
楊漢宏1, 張 勇1, 鄭海峰1, 吳麗萍2, 吳國璽2, 王鐵軍2
(1.神華準格爾能源有限責任公司,內蒙古鄂爾多斯010300; 2.內蒙古自治區水利科學研究院內蒙古呼和浩特010050)
[目的] 揭示人工植被配置對露天礦排土場邊坡水土流失的影響,為半干旱地區露天礦區排土場邊坡水土流失控制提供依據。 [方法] 以不同植物配置和對照(未治理)邊坡為研究區,于2014年和2015年的5—10月,對邊坡徑流和土壤侵蝕量與降雨量的關系進行了統計學分析。 [結果] (1) 控制坡面徑流。喬灌草和灌草配置是較好選擇,其坡面徑流僅為對照的42.9%和52.6%,二者無顯著性差異。 (2) 控制邊坡土壤侵蝕。3種植物配置措施都與對照區存在顯著性差異,其土壤侵蝕量僅為對照區的2.3%~6.7%。日降雨量與坡面徑流和土壤侵蝕量之間都存在顯著線性關系。 [結論] 不同植被配置對邊坡侵蝕控制優于徑流深,與對照區相比侵蝕量減少93%以上,而徑流深僅減少了28%~57%。
降雨量; 徑流深; 侵蝕量; 半干旱地區
文獻參數: 楊漢宏, 張勇, 鄭海峰, 等.不同人工植物配置對排土場邊坡水土流失的影響[J].水土保持通報,2017,37(4):6-11.DOI:10.13961/j.cnki.stbctb.2017.04.002; Yang Hanhong, Zhang Yong, Zheng Haifeng, et al. Impacts of different artificial plant collocations on soil and water loss at side slope in mine dump[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7,37(4):6-11.DOI:10.13961/j.cnki.stbctb.2017.04.002
礦產資源開采過程中廢棄物處理是影響礦區及周邊地區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在大型露天開采區[1]。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其一是開采造成的環境問題,如成為局地沙塵源區、水土流失區和植被嚴重退化地區等;其二是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2]。我國是全球最大煤炭開采國家之一,而且多數大型露天煤礦大多分布在生態環境脆弱干旱、半干旱交錯區[3]。尤其在內蒙古草原區分布著中國最主要的露天礦區,如分布在鄂爾多斯地區的黑岱溝露天煤礦、神府東勝和大唐露天煤礦,分布在內蒙古東部草原區的霍林河礦、伊敏露天煤礦等,這些礦區的開發面積甚至遠遠超過了一些中小型城鎮的規模,露天開采對礦區土地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壓力日趨嚴重[4]。大型露天礦各種施工活動所產生的人工排土堆是礦區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地貌單元,是一種典型的由土壤、不同粒徑碎石組成的松散土石混合物,其與原地貌、土壤或均質巖土體存在較大差別。在降雨條件下,土石混合體邊坡會發生較為明顯的水土流失,與原地貌侵蝕方式或程度存在差異[5-6]。從目前該領域研究特點來看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 (1) 針對排土堆的侵蝕與產沙規律、平臺與邊坡土壤侵蝕特征等開展的研究較多[7-9]; (2) 針對排土場堆積平臺和邊坡的工程堆積體物理力學性質、侵蝕過程及邊坡穩定性等方面進行研究[10-13]; (3) 針對排土場穩定性評價方法進行探討[14-15]。在這些研究中,排土場平臺或邊坡的性質被予以了高度的關注并有較完整的研究結果,但是對于排土場人工植被恢復中喬灌草配置對邊坡土壤侵蝕的研究相對較少,已有的研究涉及到了植物與土壤侵蝕關系研究,但也是以排土場年限表征植被狀況進行分析,而缺少了植物配置對土壤侵蝕影響的研究[16]。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不同植被配置方式對排土場邊坡土壤侵蝕進行研究,主要擬驗證的科學問題是不同生長型植物(喬木、灌木、草本)配置對邊坡土壤侵蝕的影響機制,為干旱、半干旱地區大型露天礦區排土場基于水土流失控制的人工植被恢復最佳模式選擇提供依據。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東部的黑岱溝露天煤礦。地理坐標為東經111°10′—111°25′,北緯39°25’—39°59′,面積55 km2。該區地形地貌屬于晉、陜、蒙接壤的黃土高原地區,是中國也是世界上土壤侵蝕最嚴重地區之一。研究區氣候屬于中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冬季嚴寒而漫長,夏季溫熱而短暫,晝夜溫差較大。年平均氣溫為5.3~7.6 ℃,多年平均降水量408 mm,其中60%~70%集中在每年的7—9月;降水量約占全年的60%~70%;年蒸發量為1 824.7~2 896.1 mm;日照3 119.3 h。礦區內地帶性土壤不明顯,非地帶性土壤(黃綿土)分布廣泛,其中粉粒占64%~73%,黏粒占17%~20%;土質疏松,抗侵蝕能力弱,水土流失嚴重。礦區內地帶性植被屬暖溫型草原帶,天然植被稀疏低矮,蓋度在30%以下。人工植被以油松(Pinustabuliformis)、小葉楊(Populussimonii)、檸條(Caraganaintermedia)和沙棘(Hippophaerhamnoides)為主,林間坡地主要草本植物有鐵桿蒿(Artemisiagmelinii)、茭蒿(Artemisiagiraldii)、白藜(Chenopodiumalbum)、本氏針茅(Stipabungeana)和白羊草(Bothriochloaischaemum)等為優勢種。
黑岱溝露天煤礦1992年建成投產。在開采近24 a里,礦區共設有北排土場、東排土場等6處。排土場標高為分布在1 200~1 320 m,每15 m高程設一平臺,邊坡坡度在34°~38°之間。在排土場復墾過程中主要以防止水土流失為目標,采用喬、灌、草不同混交配置。主要有油松、沙棘、山杏、無芒雀麥(Bromusinermis)和紫花苜蓿(Medicagosativa)等。本試驗布置在北排土場,該小區從1995年開始復墾,到2003年完成,累計完成復墾面積147.96 hm2,分布在1 200~1 245 m邊坡上。無植被對照區設置在陰灣排土場,坡底標高為1 450 m處。
2.2 研究方法
運用坡面徑流小區研究天然降雨與水土流失關系是目前常用的研究方法。在本文的研究中,不同人工植被徑流小區設置在北排土場的西坡面(1993年開始植被恢復重建),標高選擇在1 200~1 275 m坡面上,徑流對照區設置在陰溝排土場(表1)。在每種植被類型和對照區上設長20 m、寬5 m徑流小區3個,共12個。徑流小區用PVC板材做隔離材料,在坡地平臺用磚砌混凝土抹面做匯水池并配有塑料遮布,匯水池長、寬、高分別為3,2和1 m,最大容量6 m3,可容納最大徑流量為60 mm。為了與氣象站日降水數據對應,在徑流小區入池口設分流調節閥,如降水過程超過晚12:00,則關閉入池閥,打開側閥將徑流小區水量排到池外,同時用塑料遮布蓋住匯水池。在匯水池最低處設排水口,一次降水過程測定后,將水、泥沙排干。由于研究區集中在很小范圍內且經過標準化排土堆砌,地形(坡度、坡長)、土壤類型(擾動黃綿土)基本一致,不同地是植被(人工配置)和降雨量的差異。因此,選取不同人工植被類型(表1)和日降雨量進行坡面水土流失特征分析。其中,降雨量采用2014,2015年5—10月數據(11月到羿年4月多有降雪,故不進行觀測),期間如果發生連日降水事件,則只選擇最完整一天的測定數據參與分析;水土流失特征用坡面徑流深(mm)和土壤侵蝕量(kg/m2)2個參數來表征。日降雨量數據源于距黑岱溝最近的薛家灣氣象站數據,不同治理措施對之間的顯著性差異分析采用ANOVA方法在SPSS中完成。

表1 不同人工治理坡面植物配置與優勢種
3 結果分析
3.1 研究期間降水量日變化特征
在2014年5—10月和2015年5—10月的觀測期內,發生降水天數2014年為64 d,2015年為60 d(表2)。從不同級別降水發生的頻率和降水量大小特點來看,<5 mm降水概率最高,在57%以上;>25 mm降水概率最低,不足2%;5~10和10~25 mm發生頻率在11.7%~21.9%之間。從累積降水量來看,10~25和5~10 mm所占比率較高,分別在23.0%~25.7%和43.6%~52.2%;>25 mm降水雖然每年只發生了一次,但所占比例分別為9.0%和12.1%;<5 mm降水盡管發生頻次較多,但所占比率僅為13.1%和21.3%。

表2 研究期間降水統計學特征
需要補充說明地是在2014年6月24—25日,8月12—13日,9月22—23日和2015年的6月28—29日,9月29—30日發生了連續降水事件,因此在上述時段只選擇最完整一天的測定數據參與分析。在2 a的監測期中共獲得有效監測天數為38 d,其中2014年為23 d,2015年為15 d。監測頻率最高的雨量在5~25 mm,共30 d(表2)。
3.2 不同人工植物配置對邊坡侵蝕的影響
在本文測定的38 d(次)中,小于5 mm降雨量收集到的雨水量和水沙樣品較少,沒有納入分析。收集到可準確度量樣品的起始降雨量為5.1 mm,最大降雨量為35.8 mm。從表3可以看出,在研究時期內對照區徑流深比喬灌草、灌草區和草本區分別多92.56,76.79和46.71 mm,是3種植被配置區的1.4~2.3倍。說明人工植被坡面治理對降雨產生徑流具有極大減少功能。從效果來看,喬灌草配置效果最好,灌草次之,單一草本效果相對最低。進一步ANOVA分析表明,對照區和草本治理區徑流深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p=0.020);灌草治理區與喬灌草治理區(p=0.342)、草本治理區(p=0.002)之間也沒有顯著性差異。從降雨量對邊坡侵蝕量的影響分析中可以看出,對照區侵蝕量比喬灌草、灌草區和草本區分別多62.62,62.30和59.77 kg/m2,是3種植物治理區的14~44倍。說明不同人工植被坡面治理措施對降雨產生的邊坡土壤侵蝕量具有極大得減少功能,從效果來看不同植物措施效果都比較好。進一步ANOVA分析表明,對照區與其他3種治理措施都存在顯著性差異(p<0.001);不同植被治理措施中,灌草治理區與喬灌草治理區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p=0.321)。
從降雨量與徑流深的關系來看(圖1),無論是未
治理的裸坡還是經過22 a不同植物措施治理的坡,二者之間都有較好的線性關系。從R值顯著性檢查結果來看,對于降雨量達到6.4 mm才測到有效數據的喬灌草治理區,R0.001,27=0.580,其他3個區R0.001,30=0.554,都小于擬合回歸方程R值,說明它們擬合趨勢可信。 從變化趨勢(回歸方程斜率)特點來看,對照區(0.361)大于植被治理區;在3種治理措施中喬灌草區(0.277)與灌草區(0.229)相差無幾,但草本治理區較低為0.219。

表3 不同人工植物配置與邊坡土壤侵蝕特征(日降雨量5.1~35.8 mm)
注:累計值上角字母有相同者,表示二者無顯著性差異(p>0.001)。

圖1 研究區日降雨量與坡面徑流深的關系
從降雨量與侵蝕量的關系來看(圖2),在對照區和3種不同植物措施治理區中,二者之間同樣有較好的線性關系。從R值顯著性檢查結果來看,都小于擬合回歸方程R值,說明它們擬合趨勢可信。從變化趨勢(回歸方程斜率)特點來看,變化特點與降雨量和徑流深有所不同,對照區(0.151)大于植被治理區;在3種治理措施中喬灌草區(0.003)與灌草區(0.004)相差無幾,草本治理區較高為0.015。

圖2 研究區日降雨量與坡面侵蝕量的關系
4 討 論
土壤侵蝕敏感性是水土保持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17]。露天煤礦排土場邊坡土壤侵蝕不僅與水土流失所涉及的因子有關[9,18],而且與排土場堆積平臺和邊坡的工程堆積體物理力學性質也密切相關[6,11]。特別是對于排土場所導致的水土侵蝕過程研究,不僅對露天煤礦及周邊地區環境治理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因為工程施工形成的坡度、坡長一致和土壤性質高度相似特點,對區域土壤侵蝕研究提供了較好的典型案例[6,18]
從本文研究的半干旱草原區黑岱溝露天煤礦排土場植被恢復22 a的邊坡土壤侵蝕特征來看,引起邊坡土壤徑流最小日降雨量大于5.1 mm。雖然在2 a的試驗觀測中,在降水量小于5 mm的情況下監測到6次(占該級別的7.4%)徑流現象,但所產生的徑流量很小,可以忽略。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發生原因與雨型有關,因為在降雨量小于5 mm的情況下,如果降雨集中(陣雨)同樣可產生坡面徑流。這一點可以從控制試驗是為研究報告中得到旁證[16,18]。從產生土壤侵蝕的降雨量天數來看以10~25 mm為主,發生概率在43.0%~43.5%;其次為5~10 mm,在33.3%~39.2%;而大于25 mm降雨量每年只發生了1次(表2)。
從日降水量與邊坡徑流深的特征來看(表3),油松+山杏+無芒雀麥組成的喬灌草配置具有最佳減少邊坡徑流深的作用,在2 a的觀測期內產生徑流僅為對照區42.9%;由山杏+無芒雀麥為主的灌草區為52.6%;以無芒雀麥為主的草本區為71.2%。其中對照區與草本區之間無顯著性差別(0.001水平),說明從減少坡面徑流角度來看,單一草本治理坡面效果較差不宜采用;而喬灌草區和灌草區之間同樣無顯著性差異,表明在水保措施實施中考慮到資金約束,這二種措施可以相互代替。從控制土壤侵蝕量角度來看,由喬灌草區僅為對照區2.3%,灌草區為2.8%,草本區為6.7%。其中對照區與不同植物配置區之間都存在顯著性差異(0.001水平),說明從減少坡面土壤侵蝕量角度來看,3種配置模式都可起到較好效果。從日降雨量與徑流深和侵蝕量的關系來看(圖1—2),對照區和3種植物配置區都有較好的正相關線性關系(最小R值為0.871,0.001水平上顯著)。這一結果與朱高立等[17]在模擬控制坡度、覆蓋度和降雨量條件下獲得的結果基本相似,即在坡度一定的條件下,面產流時間與覆蓋成正相關。而不同地是降雨量與徑流深的變化趨勢大于降雨量與侵蝕量,二類線性斜率分別變化在0.219~0.361,0.003~0.151之間,這表明坡面徑流對降雨量變化的響應要快于土壤侵蝕量。從變化趨勢來看二類共同點是斜率都為正值,說明隨降雨量(降雨侵蝕力)增加,土壤侵蝕加劇。這一結果與陳海遲等[16]的模擬降雨控制試驗結果相比較,在變化趨勢上一致,但在在擬合回歸表達上有所區別。因為在模擬降雨試驗中,降雨量與徑流深、土壤侵蝕量的關系最佳擬合關系為冪函數,其特點是在降雨量較低時徑流深和土壤侵蝕量的變化較小,當達到某一值時變化增加。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與控制試驗降雨量是在設計的時間內完成的(控制試驗以30和45 min為時間尺度設定降雨量),這直接導致與本文以天為單位的研究結果之間存在一些細節差異。
5 結 論
不同植被配置方式對排土場邊坡土壤侵蝕有顯著的影響。從控制坡面徑流來看,喬灌草和灌草配置是較好選擇,其產生的坡面徑流僅為對照的42.9%和52.6%,二者無統計學顯著性差異。從控制坡面侵蝕量來看,3種植物配置措施都與對照區存在顯著性差異,土壤侵蝕量僅為對照區的2.3%~6.7%。日降雨量與坡面徑流和土壤侵蝕量之間都存在顯著線性關系,但與徑流深的關系的線性變化斜率大于與土壤侵蝕量。
[1] Modak M, Pathak K, Ghosh K K.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outsourcing decision using a BSC and Fuzzy AHP approach: A case of the Indian coal mining organization[J]. Resources Policy, 2017, 52: 181-191.
[2] 馮建宏.我國露天煤礦開采環境問題及防治對策研究[J].中國礦業,2002,11(6):61-64.
[3] World Coal Association. The coal resourc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coal[EB/OL]. (2005-01-03)[2016-05-06].World coal association∥http:∥www. worldcoal. org.2005.
[4] 馬建軍,張樹禮,李青豐.黑岱溝露天煤礦復墾土地野生植物侵入規律及對生態系統的影響[J].環境科學研究,2006,19(5):101-106.
[5] Peng Xudong, Shi Dongmei, Jiang Dong, et al. Runoff erosion process on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 from disturbed soil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ina[J]. Catena, 2014,123:215-224.
[6] 史東梅,蔣光毅,彭旭東,等.不同土石比的工程堆積體邊坡徑流侵蝕過程[J].農業工程學報,2015,31(17):152-161.
[7] 閆云霞,許炯心.黃土高原地區侵蝕產沙的尺度效應研究初探[J].中國科學(D):地球科學,2006,36(8):767-776.
[8] 梁宏溫,馬倩,溫遠光,等.不同造林撫育管理下桉樹幼林地水土流失特征[J].水土保持通報,2016,36(6):26-30.
[9] 杜忠潮,賀寶園.五陵塬邊坡侵蝕地貌發育及其影響因素[J].水土保持通報,2014,34(3):316-322.
[10] Fredlund D G, Krahn J. Comparison of slope stability methods of analysis[J].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1977,14(3):429-439.
[11] Morgenstern N R. The evaluation of slope stability: A 25 year perspective[J]. Chemistry, 2010, 10(13):3241-51.
[12] 李樹武,聶德新,劉惠軍.大型碎屑堆積體工程特性及穩定性評價[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06,25(2):4126-4131.
[13] 王自高,胡瑞林,張瑞,等.大型堆積體巖土力學特性研究[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13,32(S2):3836-3843.
[14] 曹陽,黎劍華,顏榮貴,等.超高臺階排土場建設決策研究與實踐[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02,21(12):1858-1862.
[15] 汪海濱,李小春,米子軍,等.排土場空間效應及其穩定性評價方法研究[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11,30(10):2103-2111.
[16] 陳海遲,丁占強,楊翠林.降雨特性與排土場邊坡水力侵蝕的關系[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11,32(2):103-108.
[17] 朱高立,肖澤干,劉曉靜,等.模擬降雨條件下崩積體坡面產流產沙特征及其響應關系[J].水土保持通報,2016,36(6):1-7.
[18] 張樂濤,高照良,李永紅,等.模擬徑流條件下工程堆積體陡坡土壤侵蝕過程[J].農業工程學報,2013,29(8):145-153.
Impacts of Different Artificial Plant Collocations on Soil and Water Loss at Side Slope in Mine Dump
YANG Hanhong1, ZHANG Yong1, ZHENG Haifeng1, WU Liping2, WU Guoxi2, WANG Tiejun2
(1.Shenhua Group Zhungeer Energy Co., LTD., Erdos, Inner Mongolia 010300, China; 2.Water Conservancy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er Mongolia,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50, China)
[Objective] It is a foundational mechanism to indicate different impacts of artificial vegetation collocation on the runoff deepth and soil erosion amount at the side slope of mine dump in semi-arid zone. [Methods] Based on three artificial plant collocations(tree with shrub and grass, shrub with grass, and grass) and contrast plot(no vegetation), we employed statistics method to analyz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de slope erosion(including side slope runoff and soil erosion amount) and rainfall in daily scale from May to Sep. in 2014 and 2105. [Results] (1) For controlling effect of the runoff, tree with shrub and grass, and shrub with grass performed better in three types and its runoff amount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ir values were 42.9% and 52.6% of the contrast ones , respectively. (2) For the erosive controlling effec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types and the contrast plot were found, the amounts of the three types were 2.3%~6.7% of the contrast. There were linear relation between daily rainfall and the side slope erosion. [Conclusion] Vegetation collocations had better effects in erosive control than in runoff prevention, and over 93% of erosion control and 28%~57% of runoff prevention were obtained in comparison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st.
rainfall;runoffdeepth;erosionamount;semi-aridregion
A
: 1000-288X(2017)04-0006-06
: S157.1, S157.2
2016-12-13
:2017-02-24
神華集團科技創新項目“現代露天煤礦水土保持生態修復關鍵技術及其應用研究”(SHJT-04-02-5)
楊漢宏(1960—),男(漢族),陜西省綏德縣人,碩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主要從事礦山建設與復墾技術研究。E-mail:yanghanhong_001@163.com。
吳麗萍(1961—),女(漢族),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人,碩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主要從事水土保持與生態恢復研究。E-mail:huanpingwlp@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