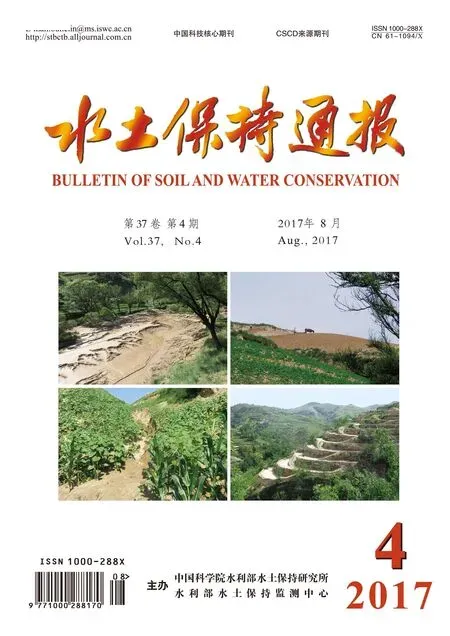基于多源地空耦合數據的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評價
郭 兵, 姜 琳
〔1.山東理工大學 建筑工程學院, 山東 淄博 255000; 2.東華理工大學江西省數字國土重點實驗室, 江西 南昌 330013; 3.區域開發與環境響應湖北省重點實驗室(湖北大學), 湖北 武漢 430062; 4.地理國情監測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重點實驗室, 湖北 武漢 433079〕
基于多源地空耦合數據的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評價
郭 兵1,2,3,4, 姜 琳1
〔1.山東理工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山東淄博255000; 2.東華理工大學江西省數字國土重點實驗室,江西南昌330013; 3.區域開發與環境響應湖北省重點實驗室(湖北大學),湖北武漢430062; 4.地理國情監測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重點實驗室,湖北武漢433079〕
[目的] 分析和探討青藏高原凍融侵蝕成因及其空間分布格局,為研究區水土保持研究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數據支撐和決策參考。 [方法] 引入凍融侵蝕動力因子(凍融期降雨侵蝕力和凍融期風場強度)和凍融期降水量(表征凍融期土壤相變水量)構建凍融侵蝕評價模型,進而對青藏高原凍融侵蝕狀況開展了定量評價和空間格局分析。 [結果] 構建的凍融侵蝕評價模型在青藏高原地區具有較高的適用性,總體評價精度為92%;青藏高原凍融侵蝕面積分布廣泛,占總面積的63.68%,而非凍融侵蝕區則主要分布于柴達木盆地、雅魯藏布江流域下游以及橫斷山區;凍融侵蝕強度隨著坡度的上升而增加,15°~24°和≥24°坡度帶上凍融侵蝕劇烈,而≤3°坡度帶凍融侵蝕強度相對較小;不同植被類型區的凍融侵蝕強度空間分布格局差異顯著,其中草甸的凍融侵蝕強度最小。 [結論] 青藏高原凍融侵蝕狀況總體上屬于中度侵蝕,其空間分布格局受地形、植被類型和氣候影響顯著。
凍融侵蝕; 多源數據; 遙感; 凍融日循環天數; 降雨侵蝕力
文獻參數: 郭兵, 姜琳.基于多源地空耦合數據的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評價[J].水土保持通報,2017,37(4):12-19.DOI:10.13961/j.cnki.stbctb.2017.04.003; Guo Bing, Jiang Lin. Evaluation of freeze-thaw eros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7,37(4):12-19.DOI:10.13961/j.cnki.stbctb.2017.04.003
凍融侵蝕是土壤侵蝕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僅次于風蝕、水蝕的第三大土壤侵蝕類型,其中我國凍融侵蝕區域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17.97%[1],侵蝕最嚴重的地區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肅、內蒙古、黑龍江等省份[2]。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日益加劇,凍融侵蝕研究已經引起廣泛重視[3]。凍融侵蝕的形成過程十分復雜,其主要動力來源于寒凍風化(物理風化、化學風化、生物風化)和雪蝕的作用,前者表現為水分相變引起的土體或巖石的破碎,后者則表現為不同礦物與水分結合后體積變化引起的土壤或巖石的破碎[4]。冬末春初時期,由于溫度的頻繁變化而造成的凍融交替所引起的巖石、土壤性質發生變化,進而造成的凍融侵蝕作用[5]。凍融侵蝕作為青藏高原水土流失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改變和破壞著土壤的物理性質,降低了耕地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河流的泥沙來源[6-7]。由于凍融過程破壞了土壤的物理結構和化學屬性,使水土流失的物質來源增加,加速了土壤中有機質以及氮、磷、鉀等元素的流失,極大威脅了耕地資源、草地資源[8-9]。當前,國外研究學者針對凍融侵蝕發生機理以及凍融侵蝕過程定量描述開展了大量研究[10-12]。雖然國內的凍融侵蝕研究起步較晚,但是許多學者已開展了一系列相關的研究工作:吳萬貞等[13]分析了三江源地區凍融侵蝕動力,并結合凍融發生的條件,進行了凍融侵蝕強度的分析與評價;景國臣等[14]對凍融侵蝕的作用形式和危害程度進行了分析和探討,認為凍融侵蝕加快了土壤侵蝕速率;李瑞平等[15]基于野外實測數據分析了季節性凍融土壤水鹽運移特征,構建了凍融期氣溫因子與土壤水鹽運移的關系模型;施建成等[16]利用AMSR-E(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meter-earth observing system)亮溫數據產品計算相鄰兩日發射率變化來判斷一日之內是否發生凍融循環過程,獲取了全國每年的凍融日循環天數;盛煜等[17]利用緯度、高程、太陽輻射等數據對疏勒河流域上游進行了流域尺度的輻射調整模型、等效高程模型和區域多年凍土分布模型的研究。然而當前多數研究中構建凍融侵蝕評價模型多考慮地形(坡度、坡向、氣溫年較差)、植被(植被覆蓋度)、降水(年降雨量)等地理環境背景因子,而對凍融侵蝕形成的驅動力因子考慮較少[3,6-8]。此外,凍融侵蝕的作用機理相比水力侵蝕更為復雜,青藏高原嚴酷的地理環境造成該區域地理信息觀測數據較匱乏,導致針對該地區的大尺度凍融侵蝕定量評價研究相對不足[4,7]。凍融侵蝕在中國分布廣泛,而青藏高原及其附近高山區是中國凍融侵蝕最集中和最強烈的區域[7]。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引入凍融侵蝕動力因子(凍融期降雨侵蝕力和凍融期風場強度)構建凍融侵蝕評價體系,開展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的定量研究,并對凍融侵蝕空間分布格局進行分析和探討,為該地區的水土保持研究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重要的數據支撐和決策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青藏高原地處中國西南部,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橫斷山脈,南自喜馬拉雅山脈南緣,北到昆侖山—祁連山北側,東西長2 945 km,南北寬達1 532 km(26°00′12″—39°46′50″N,73°18′52″—104°46′59″E),面積為2.57×106km2,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26.8%,包括西藏、青海2省區的全部和新疆、甘肅、四川、云南4省區的部分地區[4,7]。在青藏高原分布著眾多的高大山脈,主要有喜馬拉雅山脈、念青唐古拉山脈、昆侖山脈、唐古拉山脈、祁連山脈、岡底斯山脈、橫斷山脈等。該區太陽福射強烈,氣溫的較差大,氣溫低,年際變化較小,干濕季節分明[9]。夏季,由于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風和印度洋的濕潤氣流的影響,高原大部分區域降水較多。而冬季,由于青藏高原受干燥的西風帶的影響,多大風(部分地其至達到了200 d),降水稀少。青藏高原植被類型復雜多樣,高原水平帶譜依次出現森林、草甸、草原、荒漠等植被,垂直自然帶也由東南部的海洋性濕潤型遞變為高原腹地的大陸性干旱型[4]。
巖石或土體的破壞程度就越大,凍融侵蝕強度就越大[1]。一天內最高溫度大于0 ℃并且最低溫度小于0 ℃則定義為一個凍融日循環[4]。年凍融日循環天數則是指一年中凍融日循環發生的天數[11]。該指標基于青藏高原及周邊160個氣象站點(755站點)近15 a的0 cm地溫數據計算獲取的,然后用克里金內插法得到凍融日循環天數分布圖,空間分辨率為1 000 m。
1.2.2 凍融期降水量 降水量作為影響凍融侵蝕的主要因素,已經成為土壤侵蝕學科的共識[5]。降水主要通過巖石和土體中水分含量來影響凍融循環作用。在凍結過程中,由于水從液態凍結為固態時體積約增加1.1倍,因而降水量越大使得土體中含水量越大,水體液固態轉化對巖土體的機械破壞作用就越明顯[1,3]。在融化過程中,降水量則可以通過改變土體的物理性質從而改變土壤的抗蝕性[12]。該指標基于青藏高原及周邊323個氣象站點(755站點及基于TRMM數據的降水插值點)的近15 a的降水數據計算獲得,然后利用克里金內插法得到凍融期降水量分布圖,空間分辨率為1 000 m。
1.2.3 凍融期降雨侵蝕力 凍融侵蝕中,降水量不僅可以增加巖土體中的含水量影響凍融侵蝕作用,而且還通過雨滴擊濺和地表徑流為凍融侵蝕提供直接動力因素[7]。降雨量越大,降雨侵蝕力越大,水流對土壤的搬運作用就越強。因而,降雨侵蝕力是影響凍融侵蝕強度的直接動力因素之一[4]。該指標基于青藏高原及周邊323個氣象站點(755站點及基于TRMM3 B42數據的降水插值點)的近15 a的降水數據計算獲得,然后用克里金內插法得到凍融期降雨侵蝕力分布圖,空間分辨率為1 000 m。降雨侵蝕力計算公式為:

(1)

1.2.4 凍融期風場強度 青藏高原凍融侵蝕過程多發生于冬春兩季(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月),而該時段的大風日數是剩余時段的十幾倍。高原許多地方一年之中大風數超過了100 d,部分地區甚至達到200 d[4,7]。半干旱、干旱凍融侵蝕區,風力作用能夠影響巖土體的凍化速率和凍融侵蝕物質的搬運過程,因此風力大小是影響凍融侵蝕強度的重要動力因素之一。相關研究表明[4],6 m/s的風速是土壤顆粒的移動的臨界值,因此,本研究計算了凍融期>6 m/s的風速日數作為表征青藏高原凍融期風場強度的指標。該指標基于青藏高原及周邊160個氣象站點(755站點)近15 a的風向風速數據計算獲取,然后利用克里金內插法得到凍融期風場強度分布圖,空間分辨率為1 000 m。
1.2.5 坡度 坡度是影響凍融侵蝕數量和侵蝕位移大小的重要因素[14]。坡度越大,巖土體表面失穩得可能性越大,被凍融作用破壞的巖土體發生滑動、崩塌、翻滾、跳躍的可能性顯著增加[4]。此外,隨著坡度的增加,凍融侵蝕的物質輸移量增加,輸移的距離也增大[11]。因此,坡度對凍融侵蝕也十分重要。坡度指標基于90 m分辨率的SRTM-DEM 利用ArcGIS 10.2的slope工具計算獲取。
1.2.6 坡向 坡向是反映不同地形條件下坡面接受太陽輻射能力強弱的重要因素之一[15]。陽坡太陽輻射光照時間長,地面接受的太陽輻射量就越多,因而白天地表溫度劇烈升高至0 ℃以上。而陰坡由于接受太陽輻射能量少,導致白天和黑夜的溫度均在0 ℃以下,造成陰坡的凍融作用明顯弱于陽坡[6]。坡向指標是基于SRTM-DEM 重采樣數據利用ArcGIS 10.2的Aspect工具計算獲取。
1.2.7 植被 植被通過根系對土壤產生固結作用,提高土壤的穩定性,還能通過截留降水和阻礙地表水的沖刷進而直接保護地表,降低土壤侵蝕量[16]。此外,植被的存在能較大程度減小地表溫度的變化程度,減小巖土體的溫差,從而減弱凍融循環作用強度及其對土體的破壞。因此植被蓋度較大的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弱凍融侵蝕作用[4]。植被蓋度的計算采用1 000 m分辨率的MODIS NDVI數據(2000—2015年)。本研究中植被覆蓋度計算公式為:
(2)
式中:FVC——植被覆蓋度; NDVIveg——全植被覆蓋情況下像元值(置信區間為0.995); NDVIsoil——全裸土情況下像元值(置信區間為0.005);l——經驗因子,在此取值1.1。
1.3 數據來源
DEM數據采用90 m分辨率的STRM-DEM數據,該數據集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國際科學數據鏡像網站(http:∥datamirror.csdb.cn);風向風速、降水量、氣溫數據來自氣象站點數據(755氣象站點),該數據集來源于中國氣象科學數據共享服務網(http:∥cdc.cma.gov.cn /home.do),而降水插值站點數據則基于TRMM3 B42數據獲取,該數據集空間分辨率為0.25°×0.25°,數據格式為NetCDF,來自美國NASAGoddard數據分發中心DAAC(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http:∥trmm.gsfc.nasa.gov/);MOIDS NDVI數據空間分辨率為1 000 m,該數據集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國際科學數據鏡像網站(http:∥datamirror.csdb.cn)。
1.4 研究方法
1.4.1 凍融侵蝕區范圍界定方法 凍融侵蝕區是指具有強烈凍融作用的寒冷氣候條件,同時有典型的凍融侵蝕地貌形態表現的區域,并且該區域的凍融作用非常普遍[5,10]。
當前,關于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區范圍確定的研究方法很多,其中得到普遍認可的方法是取冰緣區的下界作為凍融侵蝕區的下界,取年平均溫度-2.5 ℃線作為多年凍土帶的下界,并認為冰緣區下界比多年凍土區下界低200 m左右[8]。本研究基于青藏高原及周邊160個氣象站點(755站點)30 a氣溫觀測數據和SRTM-DEM數據(緯度、經度及海拔)利用回歸方程計算出年均溫-2.5 ℃的海拔,進而得出凍融侵蝕區的下界海拔,最后提取準凍融侵蝕區的基本范圍,再從中剔除沙漠化區和冰川區,就可得到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區的范圍。所得回歸方程(通過p=0.05的顯著性檢驗)為:

(3)
式中:H——凍融侵蝕區下界海拔高度(m);X——緯度(°);Y——經度(°)。
1.4.2 凍融侵蝕強度評價方法 綜合指數評價法是將不同的評價指標進行疊加進行綜合計算,得到一個綜合性的評價指數[3-4,7]。國內外針對土壤凍融侵蝕定量研究多采用分級賦權重評價模型,該評價模型首先選取不同的指標構建一個綜合評價體系,然后對選取的各凍融侵蝕因子進行等級劃分,確定體系內不同指標的權重值,最后疊加計算形成一個加權綜合指數[4],其計算公式為:
(4)
式中:FT——凍融侵蝕綜合評價指數; Wi——各指標權重; Ii——分級后凍融指標; n——采用凍融侵蝕評價因子數量。評價指數越大,凍融侵蝕越強烈。
2 凍融侵蝕強度評價
2.1 凍融侵蝕評價指標分級及其權重確定
選取凍融日循環天數、凍融期降水量、凍融期降雨侵蝕力、凍融期風場強度、坡度、坡向和植被覆蓋度7個指標構建了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評價體系,然后根據各指標數據的直方圖分布與取值情況,參照前人的研究成果[3-4,7,13]和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凍融侵蝕研究調查評價方法,基于AHP層次分析法確定了各指標的等級賦值標準和權重賦值方案(表1)。

表1 各指標的等級賦值標準和權重賦值
2.2 凍融侵蝕評價結果驗證
基于ArcGIS10.2軟件利用綜合指數評價法對各評價指標分級數據進行加權求和,得到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指數。為了便于后續的凍融侵蝕空間格局分析,本文基于凍融侵蝕強度指數的直方圖分布結合野外觀測數據,利用ArcGIS10.2的NaturalBreaks方法對計算數據進行分級處理,分級標準詳見表2,最終得到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的分級圖(圖1)。

表2 凍融侵蝕強度分級

圖1 青藏高原凍融侵蝕強度的分級
從不同土地利用、不同植被類型、不同地形地貌上(保證野外實測數據的有效性)選取了278個野外實測(2013年)(表3)與評價結果構建了錯誤矩陣,分析了凍融侵蝕評價結果的精度,分析發現(表4):不同凍融侵蝕強度等級的評價精度略有差異,但是總體評價精度較高,為92%;其中,微度侵蝕區的評價精度最高,為96%,其次為輕度侵蝕區,評價精度為93%,而劇烈侵蝕區的評價精度最低,為79%,其原因在于在劇烈侵蝕區和重度侵蝕區的野外驗證點較少,影響了該侵蝕等級評價結果的驗證精度。綜上分析,總體的評價精度表明本研究所構建的凍融侵蝕評價模型在青藏高原地區具有較高的適用性。

表3 野外驗證點分布

表4 各侵蝕級別評價精度 %
3 凍融侵蝕強度空間格局分析與討論
青藏高原凍融侵蝕面積分布廣泛(詳見圖1),其面積為1.64×106km2,占青藏高原總面積的63.68%,主要分布于昆侖山、喀喇昆侖山、藏北高原、雅魯藏布江流域中上游、阿里高原、岡底斯山、巴顏喀拉山、祁連山等地區:其中輕度侵蝕區面積最廣,面積為5.124×105km2(圖2),主要分布于那曲縣中北部、治多縣北部、噶爾縣北部以及庫爾勒市南部,其主要原因在該地區地勢較為平緩,地形坡度較小,草地、草甸廣布,植被蓋度較高,降水稀少,土壤含水量低,導致凍融循環作用較弱;其次為重度侵蝕區,面積為3.614×105km2,主要分布于噶爾縣的中西部、日喀則市北部以及烏蘭縣的北部和南部邊緣地區,這與以上地區的地形、氣溫和植被覆蓋度相關;微度侵蝕區和中度侵蝕區面積分別為3.444×105km2(分布于瑪沁縣、康定縣北部、治多縣南部、門源回族自治縣),3.161×105km2(分布于噶爾縣西部、那曲縣南部);劇烈侵蝕區面積最小,為1.051×105km2,主要分布于阿圖什市西部、喀什市、和田市北部、日喀則市北部以及林芝縣北部,其分布格局主要受地形和植被覆蓋狀況影響。而非凍融侵蝕區則主要分布于柴達木盆地、雅魯藏布江流域下游以及橫斷山區,其原因在于主要是以上地區海拔高度較低,年平均氣溫較高,凍融侵蝕特征不明顯。

圖2 研究區不同侵蝕強度級別面積
3.1 不同流域凍融侵蝕侵蝕強度分析
為了更深入分析青藏高原的凍融侵蝕空間分布特征,本研究選取了6個典型二級流域探討了凍融侵蝕在流域尺度上的空間分異格局(表5)。結果表明: (1) 羌塘高原內陸河流域的凍融侵蝕面積最廣,面積為6.726×105km2;其次為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面積為1.604×105km2;隨后為雅魯藏布江流域,侵蝕面積為1.087×105km2;而凍融侵蝕分布面積最小的流域則為藏南諸河流域,面積為2.400×104km2。從
侵蝕區占流域總面積比例上分析:羌塘高原內陸河流域的侵蝕面積百分比最大,為91.89%,主要原因在于該流域平均海波較高,氣溫低,氣溫較差大,寒凍風化剝蝕和融凍泥流等凍融侵蝕作用普遍;其次為金沙江石鼓以上和塔里木河河源流域,其面積百分比分別為75.88%和69.85%,主要原因在于以上兩個流域內山地廣布,地勢陡峻,坡度較大,凍融侵蝕過程較強烈;而凍融侵蝕區所占面積比例最小的流域是藏南諸河流域,為16.97%,與該流域內植被蓋度較高,氣溫較差低,坡度較小相關。 (2) 通過對比青藏高原的6個典型二級流域的侵蝕強度可以發現各流域的凍融侵蝕構成比例存在顯著差異(圖3):其中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的微度侵蝕和輕度侵蝕面積分布最廣,占侵蝕面積的比例分別為36.28%,29.27%;藏南諸河流域的劇烈侵蝕和重度侵蝕面積比例最大,分別為40.42%,36.25%;瀾滄江流域的微度侵蝕和輕度侵蝕面積最廣,所占比例分別為34.41%,32.80;塔里木河河源流域中的重度和劇烈侵蝕區分布面積最廣,占侵蝕面積的比例分別為44.21%,24.21%;羌塘高原內陸河流域的輕度和中度侵蝕區面積所占比例最大,分別為36.66,22.55%;而雅魯藏布江流域的重度和劇烈侵蝕區面積分布最廣,所占面積比例分別為39.74%,20.42%。綜上分析發現,微度和輕度侵蝕區面積所占比例較大的流域為瀾滄江和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上流域的植被蓋度高,氣溫年較差較小,凍融循環作用較弱。重度和劇烈侵蝕區所占面積比例較大的流域為藏南諸河、雅魯藏布江和塔里木河河源流域,其主要原因在于藏南諸河流域和雅魯藏布江流域的地形起伏度較大,坡度陡峻,凍融期降雨和降雨侵蝕力大,凍融侵蝕地貌發育顯著,而塔里木河河源流域的凍融期風場強度較大,植被覆蓋度低,巖土體表面白天在太陽輻射下強烈升溫融化,夜間急速降溫凍結,導致該區域凍融侵蝕強度較高。

表5 不同流域侵蝕情況對比 104 km2
注:*表示該流域在青藏高原內部的部分。
3.2 不同坡度凍融侵蝕強度分析
不同坡度上的凍融侵蝕構成比例差異顯著。由圖4可以知道,15°~24°和≥24°坡度帶上劇烈侵蝕區占絕對優勢,其所占侵蝕總面積百分比分別為64.37%,94.55%;而8°~15°坡度帶上重度侵蝕區分布面積最廣,其面積百分比為51.79%,其次為劇烈侵蝕區,其面積百分比為21.57%,微度和輕度侵蝕區分布面積較小;3°~8°坡度帶上重度侵蝕區所占面積比例最大,其次為輕度侵蝕區,其比例分別為32.83%,29.07%;微度和輕度侵蝕區在≤3°坡度帶上分布面積最大,分別為37.38%,43.02%。綜上分析發現,青藏高原凍融強度隨著坡度的上升而增加,坡度越大,重度和劇烈侵蝕區所占侵蝕面積百分比越大,其原因在于坡度與凍融侵蝕量和侵蝕位移的大小具有較大的正相關性,坡度越大,凍融侵蝕產物被輸送的就越多越遠[14]。因此,在降水和重力的綜合作用下,坡度較大的地區其凍融侵蝕程度會大大提高。

圖3 各流域不同等級侵蝕強度對比
3.3 不同植被類型凍融侵蝕強度分析
植被可以保護地表,減弱凍融作用的強度及其對土體的破壞,因此不同植被類型區的凍融侵蝕強度空間分布格局差異顯著,分析結果發現(圖5),針葉林區的微度和輕度侵蝕區分布面積最廣,所占面積百分比分別為23.4%,29.36%;闊葉林的重度和輕度侵蝕區的面積百分比最大,分別為27.03%,21.62%;灌叢的輕度侵和重度侵蝕區面積較大,而劇烈侵蝕區分布面積較小;荒漠和草原的輕度和中度侵蝕區占絕對優勢,其面積百分比(輕、中之和)分別為55.09%,56.07%;草甸區的微度和輕度侵蝕區面積分布較大,占侵蝕總面積的62.17%,而劇烈侵蝕區分布面積最小;農作物的輕度侵和重度侵蝕區面積較大,其面積百分比分別為26.09%,30.43%。綜上分析發現:草甸的凍融侵蝕強度最小,其原因在于該區的植被覆蓋度較高(植物根系對土壤的固結作用、冠層阻礙地表水的沖刷作用),加上草甸區的坡度平緩,因而凍融侵蝕強度較弱;而闊葉林和農作物的凍融侵蝕強度相對較大,其原因在于闊葉林區地形起伏較大,降水較多,凍融期降雨侵蝕力較大,加行人類活動強度日益增大(亂砍亂伐等),植被遭到較大的破壞,因而該區凍融侵蝕強度較大,而農作物區的凍融侵蝕強度較大則主要是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如開挖邊坡等,一系列的開發活動形成的凍融侵蝕常引發大型滑塌。

圖4 各坡度帶不同等級侵蝕強度對比

圖5 各植被類型區不同等級侵蝕強度對比
4 結 論
(1) 改進后的凍融侵蝕評價模型在青藏高原具有較高的適用性,其總體評價精度達到92%,其中微度侵蝕區的評價精度最高,為96%。
(2) 青藏高原凍融侵蝕面積分布廣泛,為16.394×105km2,占總面積的63.68%,而非凍融侵蝕區則主要分布于柴達木盆地、雅魯藏布江流域下游以及橫斷山區。瀾滄江和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的微度和輕度侵蝕區面積所占比例較大,而藏南諸河、雅魯藏布江和塔里木河河源流域的重度和劇烈侵蝕區面積分布最廣。
(3) 凍融侵蝕強度隨著坡度的上升而增加:15°~24°和≥24°坡度帶上劇烈侵蝕區占絕對優勢;微度和輕度侵蝕區在≤3°坡度帶上分布面積最大。
(4) 不同植被類型區的凍融侵蝕強度空間分布格局差異顯著:草甸的凍融侵蝕強度最小,而闊葉林和農作物的凍融侵蝕強度相對較大。
(5) 盡管本研究構建的凍融侵蝕評價模型在青藏高原具有很好的使用性,然而凍融侵蝕機理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特別是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及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凍融侵蝕理機理和評價體系研究的需求日益迫切,后續的研究需要從理論上有所突破,為凍融侵蝕區的水土保持和生態環境建設等提供科技支撐。
[1] 劉淑珍,劉斌濤,陶和平,等.我國凍融侵蝕現狀及防治對策[J].中國水土保持,2013(10):41-44.
[2] 張建國,劉淑珍.西藏凍融侵蝕空間分布規律[J].水土保持研究,2008,15(5):1-6.
[3] 史展,陶和平,劉斌濤,等.基于GIS的三江源區凍融侵蝕評價與分析[J].農業工程學報,2012,28(19):214-221.
[4]GuoBing,ZhouYi,WangShixin,etal.Anestimationmethodofsoilfreeze-thawerosionintheQinghai-TibetPlateau[J],NaturalHazards, 2015,78(3):1843-1853.
[5] 范吳明,蔡強國.凍融侵蝕研究進展[J].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03,1(4):50-55.
[6] 王隨繼.黃河中游凍融侵蝕的表現方式及其產沙能力評估[J].水土保持通報,2004,24(2):1-5.
[7] 李輝霞,劉淑珍,鐘祥浩,等.基于GIS的西藏自治區凍融侵蝕敏感性評價[J].中國水土保持,2005(7):44-46.
[8]ZhangJianguo,LiuShuzhen,YangSiquan.Theclassificationandassessmentoffreeze-thawerosioninTibet[J].JournalofGeographicalSciences, 2007, 4(2):165-174.
[9]ZhangJianguo,YangYonghong,LiuShuzhen.Classificationandassessmentoffreeze-thawerosioninTibet,China[J].WuhanUniversityJournalofNaturalSciences, 2005,10(4):635-640.
[10]DemidovVV,OstroumovVY,NikitishenaIA,etal.Seasonalfreezingandsoilerosionduringsnowmelt[J].EurasianSoilScience, 1995,28(10):78-87.
[11]EigenbrodKD.Effectsofcyclicfreezingandthawingonvolumechangesandpermeabilitiesofsoftfinegrainedsoils[J].CanadianGeotechnicalJournal, 1996,33(4):529-537.
[12]SharrattBS,LindstromMJ,BenoitGR,etal.RunoffandsoilerosionduringspringthawinthenorthernU.SCornBelt[J].Journal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2002,55(4):487-494.
[13] 吳萬貞,劉峰貴.三江源地區凍融侵蝕動力分析及其分布特點[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26(1):57-61.
[14] 景國臣,任憲平,劉丙友,等.黑龍江省凍融侵蝕形式及其危害[J].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03,1(3):99-101.
[15] 李瑞平,史海濱,赤江剛夫,等.凍融期氣溫與土壤水鹽運移特征研究[J].農業工程學報,2007,23(4):70-74.
[16] 施建成,蔣玲梅,張立新.多頻率多極化地表輻射參數化模型[J].遙感學報,2006,10(4):502-514.
[17] 盛煜,李靜,吳吉春,等.基于GIS的疏勒河流域上游多年凍土分布特征[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0,39(1):32-39.
[18] 李成六,馬金輝,唐志光,等.基于GIS的三江源區凍融侵蝕強度評價[J].中國水土保持,2011(4):41-43.
[19]ZhaoTianjie,ZhangLixin,JiangLingmei,etal.Anewsoilfreeze/thawdiscriminantalgorithmusingAMSR-Epassivemicrowaveimagery[J].HydrologicalProcesses, 2011,25(11):1704-1716.
[20] 張建國,劉淑珍,范建容.基于GIS的四川省凍融侵蝕界定與評價[J].山地學報,2005,23(2):248-253.
Evaluation of Freeze-thaw Eros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GUO Bing1,2,3,4, JIANG Lin1
〔1.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Civil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Zibo, Shandong 255000, China; 2.Key Laboratory for Digital Land and Resources of Jiangxi Provinc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3.Hubei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e(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 4.Key Laboratory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Census and Monitoring,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Surveying, Mapping and Geoinformation, Wuhan, Hubei 433079, China〕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cause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freeze-thaw(FT) eros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o provide important data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 and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is region. [Methods] The driving force factors of FT erosion(the rainfall erosion and wind field strength during FT period) and the precipitation during FT period(indicating the soil water content) were introduced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FT erosion and the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T eros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FT erosion had high applicability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with the overall evaluation accuracy of 92%. The FT erosion area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covering 63.68% of the total area; and the non-FT erosion zon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Qaidam Basin and the Hengduan mountains. The intensity of FT eros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lope. The erosion intensities of 15°~24° and ≥24° slope zone were severe while that of ≤3° slope zone was relatively sligh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FT erosion intensity among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FT erosion intensities of broad leaved forest and crops were relatively severe while that of meadow was slighter. [Conclusion] The FT erosio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belonges to the level of moderate erosion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errain, plant types and climate factors.
freeze-thawerosion;multi-sourcedata;remotesensing;numberofdaysoffreeze-thawcycles;rainfallerosion
A
: 1000-288X(2017)04-0012-08
: P642.14
2016-11-16
:2017-01-26
東華理工大學江西省數字國土重點實驗室開放基金項目“南嶺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生態脆弱性驅動因子定量分析研究”(DLLJ201709); 區域開發與環境響應湖北省重點實驗室開放研究基金項目[2017(B)003]; 地理國情監測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重點實驗室開放基金項目(2016NGCM02); 山東理工大學博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4041/416027); 國家重大科技專項(00-Y30B14-9001-14/1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501425)
郭兵(1987—),男(漢族),山東省高青縣人,博士,講師,主要從事生態環境與災害遙感的研究。E-mail:guobingjl@163.com。
姜琳(1987—),女(漢族),山東省文登區人,碩士,主要從事環境遙感的研究。E-mail:linlin2006199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