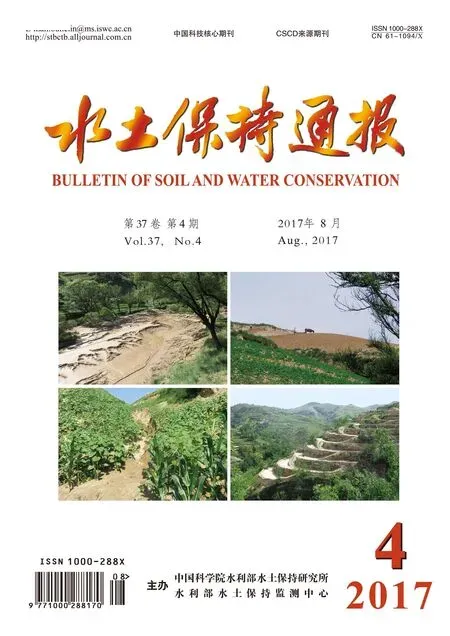添加生物質(zhì)炭對旱地紅壤中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的影響
韓召強(qiáng), 陳效民, 陶朋闖, 靳澤文, 張曉玲, 黃欠如
(1.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資源與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院, 江蘇 南京210095; 2.江西紅壤研究所, 江西 進(jìn)賢 331717)
添加生物質(zhì)炭對旱地紅壤中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的影響
韓召強(qiáng)1, 陳效民1, 陶朋闖1, 靳澤文1, 張曉玲1, 黃欠如2
(1.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資源與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院,江蘇南京210095; 2.江西紅壤研究所,江西進(jìn)賢331717)

生物質(zhì)炭; 紅壤; 硝態(tài)氮; 水平運移

氮素是作物生長發(fā)育的必需營養(yǎng)元素,在作物生長發(fā)育過程中,氮素參與作物新陳代謝的所有過程。施肥是農(nóng)業(yè)增產(chǎn)的重要措施,隨著農(nóng)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和集約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氮肥的施用量近年來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氮肥中的氮素主要以銨態(tài)氮的形式存在,雖然土壤對銨態(tài)氮有很強(qiáng)的吸附作用,但銨態(tài)氮可轉(zhuǎn)化為不易被土壤所吸附的硝態(tài)氮[1],且硝態(tài)氮極易從土壤中流失,導(dǎo)致周邊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氮化合物含量不斷上升,并逐漸達(dá)到危險水平,從而引起水體的富營養(yǎng)化等問題[2]。因此,研究硝態(tài)氮在農(nóng)田土壤中的水平運移規(guī)律具有重要的意義。生物質(zhì)炭是由有機(jī)物料在厭氧條件下經(jīng)低溫?zé)峤猱a(chǎn)生的含碳豐富的固態(tài)物質(zhì),是黑碳的一種存在形式。生物質(zhì)炭孔隙度高、比表面積大、帶負(fù)電荷多、芳香化程度也高、且具有較高的穩(wěn)定性和吸附性[3]。另外,它具有改善土壤質(zhì)量和保持土壤肥力等諸多作用[4]。隨著生物質(zhì)炭用于改良土壤研究的深入,人們發(fā)現(xiàn)生物質(zhì)炭能夠提高土壤對氮素養(yǎng)分的吸附,降低土壤養(yǎng)分的流失[5]。生物質(zhì)炭通過固持土壤氮素養(yǎng)分,從而有效減少由于降雨造成的氮素流失,提高表土層養(yǎng)分固持能力。紅壤是我國熱帶和亞熱帶地區(qū)的地帶性土壤,在強(qiáng)烈的風(fēng)化和淋溶作用下其自然肥力低下[6],再加上長期不合理的耕作方式造成土壤質(zhì)地黏重,通氣透水性差。近年來,紅壤地區(qū)的農(nóng)民為了追求作物高產(chǎn)而大量施用化肥,而施用常規(guī)的化肥不但無法達(dá)到提高土壤肥力的目的,且過高的氮肥施用量造成了氮素的流失,污染了大氣和水體的環(huán)境[7],因此施用穩(wěn)定性高的生物質(zhì)炭可能是改善這類土壤肥力的重要方式。大量研究表明[8-9],生物質(zhì)炭作為土壤改良劑對緩解農(nóng)田氮素流失引起的面源污染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但是,目前仍缺乏生物質(zhì)炭施用對紅壤中硝態(tài)氮運移影響的研究。因此,本文以小麥秸稈制備的生物質(zhì)炭為對象,利用室內(nèi)水平土柱模擬試驗,探討不同量生物質(zhì)炭施入紅壤后對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的影響,從而揭示添加生物質(zhì)炭后紅壤中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規(guī)律,以期為該地區(qū)的農(nóng)田水分管理和環(huán)境保護(hù)等提供科學(xué)依據(jù)。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qū)概況
研究區(qū)設(shè)在江西省紅壤研究所(116°20′24″E,28°15′30″N),為典型低山丘陵紅壤區(qū),屬亞熱帶濕潤氣候,年均氣溫17.5℃,年均日照時間1 900~2 000 h,年無霜期282 d。年降雨量1 587 mm,年蒸發(fā)量1 100~1 200 mm,干濕季節(jié)明顯,降雨主要集中在3—6月,占全年雨量61%~69%;7—9月為旱季,蒸發(fā)量占全年蒸發(fā)量的40%~50%,供試土壤由第四紀(jì)紅色黏土發(fā)育而來。
1.2 供試土壤及生物質(zhì)炭
供試土壤采樣的土層深度為0—15 cm.土壤的基本性質(zhì)如下:土壤pH值4.54,全氮0.98 g/kg,陽離子交換量15.2 cmol/kg,有效磷13.26 mg/kg,有機(jī)碳7.98 g/kg,全磷0.45 g/kg,總孔隙度53.6%,容重1.23 g/cm3,黏粒含量316.0 g/kg,粉砂粒含量391.2 g/kg,砂粒含量292.8 g/kg。本研究采用的生物質(zhì)炭來自于河南商丘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原料為小麥秸稈,炭化溫度為500 ℃,小麥秸稈的35%被轉(zhuǎn)化為生物質(zhì)炭,生物質(zhì)炭的pH 10.35,陽離子交換量217.0 cmol/kg,有效磷4.7 g/kg,有機(jī)碳467.1 g/kg,全氮5.9 g/kg,容重0.45 g/cm3,比表面積8.9 m2/g。
1.3 測定方法
土壤基本理化性質(zhì)的測定方法[10]:土壤容重采用環(huán)刀法測定;土壤顆粒分析采用吸管法測定,質(zhì)地采用國際制分類;土壤有機(jī)質(zhì)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測定;硝態(tài)氮采用CaSO4浸提—紫外分光光度計法測定;陽離子交換量采用1 mol/L乙酸銨交換法測定;土壤水分?jǐn)U散率測定詳見參考文獻(xiàn)[11]。
1.4 土壤中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試驗
1.4.1 試驗裝置 室內(nèi)水平擴(kuò)散率儀裝置如圖1所示。采用長100 cm、寬20 cm、高10 cm的長方形有機(jī)玻璃擴(kuò)散槽,通過馬氏瓶控制水頭并以入滲土體懸殊的厚長比來消除重力勢和壓力勢對水分入滲的影響,使入滲水分在土樣基質(zhì)吸力作用下作水平入滲,以模擬田間水平入滲(圖1)。

圖1 土壤水分?jǐn)U散率裝置示意圖
1.4.2 硝態(tài)氮的水平擴(kuò)散試驗 采集不同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C0(0 t/hm2,不施用生物質(zhì)炭),C1(2.5 t/hm2),C2(5 t/hm2),C3(10 t/hm2),C4(20 t/hm2),C5(30 t/hm2),C6(40 t/hm2)〕土壤樣品(其中C1處理由于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太少,對試驗結(jié)果影響不顯著,因此本文沒有對該用量進(jìn)行分析),除去植物根系及石塊后將所采集的土壤風(fēng)干、研磨,并全部通過20目篩,按田間實測的容重稱取14.76,14.64,14.64,14.52,14.41,14.28 kg分別填裝入水平擴(kuò)散率儀中,各處理的土壤性質(zhì)詳見表1。配制濃度為200 mg/L的硝態(tài)氮溶液作為示蹤液,用馬氏瓶控制水頭,進(jìn)行硝態(tài)氮水平擴(kuò)散試驗。當(dāng)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的濕潤峰到達(dá)4,8,12,16,20,24,28,32,36,40,44,48,52,56,60 cm時,分別記錄時間。當(dāng)濕潤峰到達(dá)約60 cm左右時,停止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自濕潤峰處端開始將土柱分成4 cm的小段,立即用取樣器依次分段取樣,測定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樣品的硝態(tài)氮濃度,每個處理分別測定3次重復(fù)。
1.5 數(shù)據(jù)處理
采用Excel 2013軟件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處理和作圖,采用DPS數(shù)據(jù)處理系統(tǒng)進(jìn)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較(α=0.05)。采用SPSS 20.0統(tǒng)計分析軟件進(jìn)行相關(guān)性分析(α=0.05)。

表1 不同處理土壤基本理化性質(zhì)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生物質(zhì)炭對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速率的影響
水平擴(kuò)散率儀中的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受溶質(zhì)的濃度梯度、土壤基質(zhì)勢以及水勢梯度的多重影響。在硝態(tài)氮運移過程中,硝態(tài)氮的運移速率隨著運移距離的增加而逐漸減小,因此可以通過運移速率隨著運移距離變化的規(guī)律研究施用生物質(zhì)炭對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速率的影響。不同生物質(zhì)炭處理下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其運移速率與運移的距離呈冪函數(shù)關(guān)系(圖2)。

圖2 不同生物炭施用量硝態(tài)氮運移速率與運移距離關(guān)系
經(jīng)統(tǒng)計分析,6個處理下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速率與運移距離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均達(dá)到了極顯著水平(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r0=0.992 8**,r2=0.961 2**,r3=0.992 2**,r4=0.976 6**,r5=0.977 9**,r6=0.991 6**,n=15)。由圖2可知,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不同,各處理的硝態(tài)氮運移曲線也發(fā)生了分異。在4 cm 處,所有處理的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均較快,CK處理中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速率最小為0.44 cm/min,而C5處理中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速率最大為0.62 cm/min。與CK處理相比,施用生物質(zhì)炭的其他5個處理(C2,C3,C4,C5和C6)運移速率均顯著上升(p<0.05),其增幅分別為:10.72%,25.94%,42.39%,53.62%和40.65%,其中C5處理達(dá)到最大值為0.62 cm/min。在0—20 cm區(qū)間內(nèi),除了C6處理外,其他處理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速率均隨施炭量的不斷增加而呈增加趨勢,當(dāng)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達(dá)到40 t/hm2(C6處理)時,與C5處理相比,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速率整體出現(xiàn)降低的趨勢。所有處理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速率隨運移距離的整體變化基本一致,即在0—20 cm 區(qū)間內(nèi)6個處理硝態(tài)氮的運移速率迅速下降,在20 cm處,所有處理的硝態(tài)氮運移曲線基本接近并開始匯聚。20—60 cm區(qū)間內(nèi)硝態(tài)氮的運移速率趨于平緩,在60 cm處各處理的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速率最低,接近于零。
2.2 生物質(zhì)炭對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濃度的影響
土壤含水量、非飽和濃度梯度、土壤水?dāng)U散率和生物質(zhì)炭的吸附作用等對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濃度影響較大,其中,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濃度隨土壤含水量增加而降低。由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濃度和土壤含水量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更好的得出施用生物質(zhì)炭對硝態(tài)氮在土體的水平運移產(chǎn)生重要影響。不同生物質(zhì)炭處理下土壤含水量與硝態(tài)氮運移濃度關(guān)系的變化趨勢基本上一致,均呈負(fù)冪函數(shù)變化(圖3),二者的相關(guān)系數(shù)均達(dá)到極顯著水平(不同生物質(zhì)炭處理下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濃度與土壤含水量的相關(guān)系數(shù)r分別為r0=0.948 0**,r2=0.911 5**,r3=0.841 8**,r4=0.958 1**,r5=0.894 8**,r6=0.981 9**,n=15)。隨著土壤含水量的增加,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濃度不斷降低。由圖3可知,所有處理的硝態(tài)氮濃度最大值均出現(xiàn)在濕潤峰峰面上。C5處理的硝態(tài)氮濃度最大值為165.52 mg/kg,也是所有處理中的最高值,并且其整體硝態(tài)氮濃度也要比其他處理高;CK處理的硝態(tài)氮濃度最大值為145.23 mg/kg,是所有處理中的最低值。與CK處理相比,其它施用生物質(zhì)炭的5個處理(C2,C3,C4,C5和C6)的濕潤峰峰值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其增幅分別為:3.74%,10.61%,12.66%,13.97%和10.31%。在硝態(tài)氮運移濃度隨土壤含水量變化曲線中,C5處理的整體硝態(tài)氮濃度較其它處理表現(xiàn)為最高。

圖3 不同生物炭施用量土壤含水量對
2.3 生物質(zhì)炭對土壤水?dāng)U散率的影響
非飽和土壤水?dāng)U散率與土壤水分密切相關(guān),其隨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加。水平方向上的非飽和土壤擴(kuò)散率實際上反映了土壤水分在水平方向上運移的軌跡,即水流主要流動方向的擴(kuò)散狀況。硝態(tài)氮在土壤中水平運動時,其濃度受到非飽和土壤擴(kuò)散率的影響,隨土壤水分?jǐn)U散率的升高而下降,并呈對數(shù)曲線變化(圖4)。土壤水?dāng)U散率與對應(yīng)的硝態(tài)氮濃度相關(guān)系數(shù)在各處理中均達(dá)到極顯著水平(不同生物質(zhì)炭處理土壤水?dāng)U散率與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濃度的相關(guān)系數(shù)r分別為r0=0.854 8**,r2=0.939 8**,r3=0.859 9**,r4=0.850 2**,r5=0.827 9**,r6=0.688 7**,n=15)。由圖4可知:土壤水?dāng)U散率隨著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的增加呈逐漸降低的趨勢。當(dāng)土壤水?dāng)U散率小于2 cm3/min時,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濃度隨土壤水?dāng)U散率的增大而急劇減小,當(dāng)土壤水?dāng)U散率大于2 cm3/min時,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濃度隨土壤擴(kuò)散率的增大變化幅度趨于平穩(wěn)。

圖4 不同生物炭施用量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濃度與土壤水分?jǐn)U散率的關(guān)系
3 討論與結(jié)論
硝態(tài)氮是一種非吸附的溶質(zhì),不易被分配到土壤的吸附位點上,因此土壤孔隙、容重及質(zhì)地等物理特性是影響硝態(tài)氮在土壤中水平運移的主導(dǎo)因素。本試驗中,處理CK硝態(tài)氮的運移速率和運移濃度最小,這是因為CK處理無生物質(zhì)炭施入,紅壤自身容重大及孔隙度低的特點阻礙了硝態(tài)氮在土壤中的運移。而生物質(zhì)炭施入土壤后,由于生物質(zhì)炭顆粒較粗,可以改善紅壤質(zhì)地較為黏細(xì),結(jié)構(gòu)較差,大孔隙比例較低的特性,增加了樣品中大孔隙的比例[12]。并且其多孔高比表面特征,對土壤容重有降低效果。土壤中存在明顯的大孔隙時溶質(zhì)便會優(yōu)先穿越,此時吸附作用對溶質(zhì)運移的影響作用將會較小[13],致使硝態(tài)氮在土壤中運移速率和運移濃度增大,當(dāng)生物質(zhì)炭施入量為30 t/hm2時這種效果促進(jìn)最為明顯。另外,土壤基質(zhì)勢也是影響硝態(tài)氮在土壤水分?jǐn)U散裝置中運移的重要因素。土壤基質(zhì)勢是由土壤基質(zhì)的吸附力和毛管力造成的勢能,是硝態(tài)氮在土壤中水平運移的水平吸力,主要受到土壤容重和孔隙度的影響。生物質(zhì)炭的施入使土壤通氣狀況得到改善且土壤水分入滲率增大,這使得硝態(tài)氮在運移過程中所受到的土壤基質(zhì)勢和水勢梯度大大增加,導(dǎo)致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速率和濃度不斷提高。

非飽和土壤水?dāng)U散率,又叫擴(kuò)散度或擴(kuò)散系數(shù),它是運用土壤水動力學(xué)基本原理建立土壤水運動的數(shù)學(xué)模型。硝態(tài)氮在土壤中作水平運移時,其濃度受到非飽和土壤擴(kuò)散率的影響,隨土壤水分?jǐn)U散率的降低而增大。在本研究中,隨著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的增加,土壤水?dāng)U散率較CK呈不斷降低的趨勢,這是因為生物質(zhì)炭通過直接和間接作用影響了土壤水的擴(kuò)散過程。一方面,生物質(zhì)炭可以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孔隙度和飽和導(dǎo)水率,使土壤的通氣透水性得到改善,在相同類型的土壤中,土壤容重越小,孔隙度越大,土壤中的機(jī)械彌散作用就越小,從而導(dǎo)致土壤水?dāng)U散率變小。另一方面,生物質(zhì)炭發(fā)達(dá)的孔隙結(jié)構(gòu)使其存在著各種大小不一的孔隙,且其比表面積大,表面具有大量負(fù)電荷及高電荷密度的特點[18]增加了土壤膠體的含量。有研究[19]表明,土壤水分?jǐn)U散率受土壤膠體影響較大,土壤膠體的晶格表面容易與水分子結(jié)合形成氫鍵而束縛水的運動,其水分子也會被束縛在膠體表面,從而降低膠體表面水的活度。生物質(zhì)炭施入土壤后使土壤水在運動的過程中被束縛在膠體表面的水分子不斷增多,從而導(dǎo)致了土壤水?dāng)U散率不斷降低。
本研究采集不同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的土壤進(jìn)行室內(nèi)水平運移模擬試驗,以研究施用生物質(zhì)炭對旱地紅壤硝態(tài)氮的水平運移過程。研究結(jié)果表明,在旱地紅壤中,與CK處理相比,施用生物質(zhì)炭的5個處理的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速率和水平運移濃度均顯著提高(p<0.05)。當(dāng)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30 t/hm2時,隨著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的增加,硝態(tài)氮水平運移速率和水平運移濃度均表現(xiàn)為上升趨勢,C5處理的變化曲線整體表現(xiàn)為最大,當(dāng)生物質(zhì)炭施用量為40 t/hm2時(C6處理),與C5處理相比,這種促進(jìn)作用有所減弱。因此,在利用生物質(zhì)炭改良旱地紅壤理化性狀的同時,也要注意防范氮素流失對環(huán)境的影響,降低其對地表水的潛在污染風(fēng)險。
[1] 靖彥,陳效民,李秋霞,等.生物質(zhì)炭對紅壤中硝態(tài)氮和銨態(tài)氮的影響[J].水土保持學(xué)報,2013,27(6):265-269.
[2] 張福珠,熊先哲,戴同順,等.應(yīng)用15N研究土壤—植物系統(tǒng)中氮素淋失動態(tài)[J].環(huán)境科學(xué),1984(1):23-26.
[3] Renner R. Rethinking biochar[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41(17):5932-5933.
[4] Topoliantz S, Ponge J F, Ballof S. Manioc peel and charcoal: A potential organic amendment for sustainable soil fertility in the tropics[J].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 2005,41(1):15-21.
[5] 劉瑋晶,劉燁,高曉荔,等.外源生物質(zhì)炭對土壤中銨態(tài)氮素滯留效應(yīng)的影響[J].農(nóng)業(yè)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報,2012,31(5):962-968.
[6] He Yuangqiu, Li Zhiming. Nutrient cycling and balance in red soil agroecosystem and their management[J]. Pedosphere, 2000,10(2):107-116.
[7] 朱建國.硝態(tài)氮污染危害與研究展望[J].土壤學(xué)報,1995,32(S2):62-68.
[8] 王輝,王全九,邵明安.人工降雨條件下黃土坡面養(yǎng)分隨徑流遷移試驗[J].農(nóng)業(yè)工程學(xué)報,2006,22(6):39-44.
[9] 吳發(fā)啟,范文波.坡耕地土壤結(jié)皮形成的影響因素分析[J].水土保持學(xué)報,2002,16(1):33-36.
[10] 鮑士旦,江榮風(fēng),楊超光,等.土壤農(nóng)化分析[M].北京: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99:30-34.
[11] 雷志棟,楊詩秀,謝傳森.土壤水動力學(xué)[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1988:233-234.
[12] 靳澤文,陳效民,李秋霞,等.生物質(zhì)炭對旱地紅壤理化性狀和水力學(xué)特性的影響[J].水土保持通報,2015,35(6),81-85.
[13] 李文娟,顏永毫,鄭紀(jì)勇,等.生物炭對黃土高原不同質(zhì)地土壤中NO3-N運移特征的影響[J].水土保持究,2013,20(5):60-63.
[14] Glaser B, Lehmann J, Zech W. Ameliorat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highly weathered soils in the tropics with charcoal: A review[J]. Biology & Fertility of Soils, 2002,35(4):219-230.
[15] Mizuta K, Matsumoto T, Hatate Y, et al. Removal of nitra-nitrogen from drinking water using bamboo powder charcoal[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01,95(3):255-257.
[16] Ding Ying, Liu Yuxue, Wu Weixiang, et al. Evaluation of biochar effects on nitrogen retention and leaching in multi-layered soil columns[J]. Water, Air,& Soil Pollution, 2010,213(1):47-55.
[17] 劉玉學(xué),劉微,吳偉祥,等.土壤生物質(zhì)炭環(huán)境行為與環(huán)境效應(yīng)[J].應(yīng)用生態(tài)學(xué)報,2009,20(4):977-982.
[18] 靖彥,陳效民,李秋霞,等.施用生物質(zhì)炭對紅壤中硝態(tài)氮垂直運移的影響及其模擬[J].應(yīng)用生態(tài)學(xué)報,2014,25(11):3161-3167.
[19] 熊毅,陳家坊.土壤膠體,土壤膠體的性質(zhì)(第3冊)[J].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90:157-212.

HAN Zhaoqiang1, CHEN Xiaomin1, TAO Pengchuang1, JIN Zewen1, ZHANG Xiaoling1, HUANG Qianru2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2.Red Soil Institute, Jinxian, Jiangxi 331717, China)

biochar;redsoil;nitratenitrogen;horizontaltransport
A
: 1000-288X(2017)04-0047-05
: S153.3
2016-11-14
:2016-12-30
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項目“耕地地力影響化肥養(yǎng)分利用的機(jī)制與調(diào)控”(2016YFD0200305); 江西省科技支撐項目(20151BBF60060)。
韓召強(qiáng)(1992—),男(漢族),山東省濟(jì)寧市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水土資源利用及旱地紅壤改良。E-mail:2015103064@njau.edu.cn。
陳效民(1957—),男(漢族),江蘇省張家港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水土資源與環(huán)境物理過程研究。E-mail:xmchen@nj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