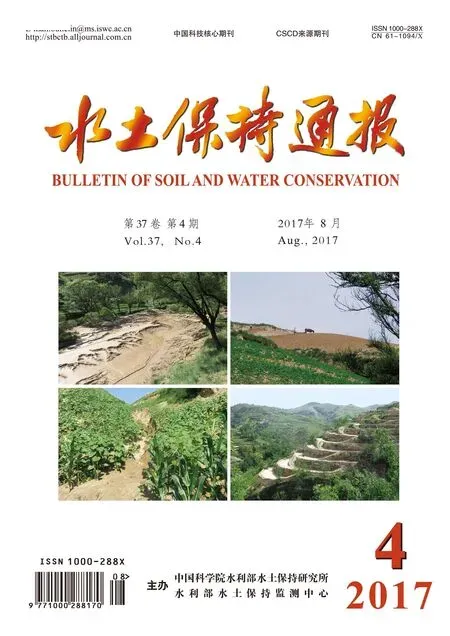1990-2014年甘肅省白龍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對人類活動響應
鞏 杰, 張金茜, 錢彩云, 馬學成, 柳冬青
(蘭州大學 資源環境學院 西部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甘肅 蘭州 730000)
綜合研究
1990-2014年甘肅省白龍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對人類活動響應
鞏 杰, 張金茜, 錢彩云, 馬學成, 柳冬青
(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西部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甘肅蘭州730000)
[目的] 綜合分析1990—2014年甘肅省白龍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及其對人類活動的響應,以期為該區未來的土地利用優化提供參考。 [方法] 基于1990年,2002年,2014年3期遙感影像解譯獲取的土地利用數據,計算土地利用變化速度、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和土地利用程度。 [結果] 1990—2014年流域的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從10.24%增長到17.59%;1990—2014年流域的土地利用類型變化以草地、耕地和林地的轉換為主;1990—2002年流域內各縣(區)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介于1.38~6.65,而2002—2014年流域內各縣(區)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介于-15.43~0.17。 [結論] 1990—2014年流域人類活動對土地的利用由簡單索取開發型轉變為保護與生態建設型,從破壞性、粗放式和低利用效率向保護性、集約式和高利用效率發展。
土地利用變化; 人類活動; 甘肅省白龍江流域
文獻參數: 鞏杰, 張金茜, 錢彩云, 等.1990—2014年甘肅省白龍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對人類活動響應[J].水土保持通報,2017,37(4):219-224.DOI:10.13961/j.cnki.stbctb.2017.04.037; Gong Jie, Zhang Jinxi, Qian Caiyun, et al. Response of land use change on human activities in Bailongjiang watershed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1990—2014[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7,37(4):219-224.DOI:10.13961/j.cnki.stbctb.2017.04.037
土地系統是理解人類—環境關系的紐帶和橋梁[1]。人類通過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改變著陸地表層環境,以追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2-5]。近幾十年來,隨著人口增加、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活動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逐步加深。土地利用變化為人類活動所驅動,是人類在變化環境下的主動選擇[6],并且土地利用變化是人類活動作用于陸地表層環境的一種重要方式和響應[3-5,7]。因此,區域土地利用變化分析可以有效揭示人類活動的方向和程度,在清楚人類活動方向和程度的基礎上,可為未來的土地利用優化提供建議,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應用價值。土地利用變化對人類活動程度的響應主要體現在土地利用變化的速度、轉移方向和土地利用程度3個方面[2,8],可以利用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和土地利用程度變化等指標表征。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針對土地利用變化與人類活動響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如:Eduardo Corbelle-Rico等[9]通過對1956—2005年西班牙西北部土地利用變化的分析,揭示出人類活動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因子因研究時段不同而不同。劉紀遠等[8,10]采用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和土地利用程度變化指標開展了中國土地利用變化的時空動態特征;并指出人類活動中的政策調控和經濟驅動是導致土地利用變化及其時空差異的主要原因。呂立剛[11]等采用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土地利用變化面積轉移矩陣和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對江蘇省1985—2008年的土地利用變化分析發現,追求凈產出(利潤)的增長是1985年以來土地利用變化的內在動力;王三等[12]采用土地利用程度變化和馬爾可夫土地利用變化矩陣指標對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研究結果表明,研究區域各土地利用類型間轉移明顯,耕地資源流失嚴重,這與人類活動相關的城市化進程有很大關系。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國和區域尺度,涉及西北山區以及流域尺度研究報道較少。流域是一個特殊的地理單元,流域生態系統及流域綜合管理等已成為國際研究熱點。中國在流域環境方面存在嚴峻問題,而它的快速社會經濟發展,更深刻地表明了流域生態系統研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從流域的角度來解決環境問題并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一條更有效地應用系統綜合的途徑[13]。因此,亟待開展流域土地利用變化與人類活動響應研究,研究對流域土地利用與人類活動優化、流域綜合管理等具有實際意義。甘肅省白龍江流域是長江上游的水源涵養林區、水土保持重點防治區和重要生態屏障。雖然自1999年以來國家推行了一系列促進區域生態恢復的工程,如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等,但由于區域人口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流域內林業資源被過度開發利用,過度放牧導致草場退化嚴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地質災害頻發,生態環境脆弱。故急需開展流域尺度研究以期為流域的土地利用方式改變以及綜合治理提供意見。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甘肅省白龍江流域(32°36′—34°24′N,103°00′—106°30′E)地處青藏高原向秦巴山地和黃土高原過渡的交錯地帶,是長江二級支流嘉陵江上游的水源涵養區和生態屏障,主要流經迭部縣、舟曲縣、武都區、宕昌縣和文縣,流長約475 km,流域面積約1.84×104km2。流域內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伏,海拔高差大,高山峻嶺和峽谷盆地相間分布、溝壑縱橫,地貌景觀多樣,主要有:山地地貌、河谷地貌、黃土地貌。流域內氣候類型復雜,夏季高溫多雨,冬季溫涼少雨,年均氣溫6~15 ℃,年均降水量400~850 mm,降水量季節變化大,7—8月間常有高強度短時暴雨,冬季降水量較少,且降水時空分布不均勻。
1.2 數據源及處理
采用的遙感數據來源于美國地質調查局和國際科學數據服務平臺的Landsat TM/ETM+影像,其分辨率為30 m,時段分別為1990,2002,2014年,月份為7—8月。使用ENVI4.7對影像數據進行幾何糾正、影像增強、影像鑲嵌與裁剪等預處理;解譯過程在ArcGIS 10.2平臺上完成,利用野外定點數據和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影像對解譯數據進行精度驗證,遙感影像的解譯精度為96.1%,最后進行拓撲檢查及錯誤修改,滿足相關研究分析的需要。根據LUCC分類標準[14]和白龍江流域實際情況,將土地利用類型分為草地、耕地、居民工礦用地、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共6類。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變化速度
(1)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是表征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在一定時間段內變化速度的指標,反映人類活動對單一土地利用類型的影響[15-17]。計算公式為:

(1)>
式中:i——土地利用類型;t1,t2——研究時間點;Ki——t1到t2時段內i類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Sit1,Sit2——t1,t2時間i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km2)。
(2) 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是表征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速度的指標,反映人類活動對流域土地利用類型變化的綜合影響[8,10]。以流域內各縣(區)為研究單元求得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并在ArcGIS中進行可視化分析,分級方法采用Natural Breaks。計算公式為:
(2)式中:i——土地利用類型,本研究中n=6;S——研究時段內流域的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 ΔSi-j——初期至末期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轉換為其他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的總和(km2);Si——初始時間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總面積(km2);t——土地利用變化時間段。
1.3.2 土地利用轉移方向 土地利用面積轉移矩陣可表征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結構特征,揭示人類活動下的土地利用變化方向和面積。該方法來源于系統分析中對系統狀態與狀態轉移的定量描述,可反映在一定時間間隔下,一個亞穩定系統從T時刻向T+1時刻狀態轉化的過程,從而可以更好地表述土地利用格局的時空演化過程[18],其數學表達形式為:
(3)
式中:Sij——研究初期與末期的土地利用狀態;n——土地利用的類型數。
1.3.3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程度以其綜合指數來表征,它可反映人類活動所影響的主要地類,揭示人類活動對土地的開發程度。研究以流域內的縣(區)為單元,計算1990,2002和2014年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和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并對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可視化分析,分級方法采用Natural Breaks。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計算公式為[15]:
(4)
同時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可定量表征流域內土地利用的綜合水平和變化趨勢,計算公式為[18-19]:
ΔIb-a=Ib-Ia=

(5)
式中:j——土地利用類型分等級數,本研究中k=4; I——研究區域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 Aj——第j等級土地利用程度分級指數; Cj——第j等級的土地利用程度面積百分比;ΔIb-a——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 Ia, Ib——時間a和時間b研究區域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 Cja, Cjb——時間a和時間b第j等級的土地利用程度面積百分比; 100——將指數擴大100倍,使差異變大,對比性變強。
其中,Aj取值根據劉紀遠[14]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的綜合分析方法,將土地利用類型整合為未利用地級、林草地水用地級、農業用地級和城鎮聚落用地級4級,分別將其指數設定為1,2,3,4,值越高,表示人類活動強度越高,反之則較低。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地利用變化速度
2.1.1 單一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速度 1990—2014年,各土地利用類型面積及其速度表現出不同的變化特點(圖1)。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積持續減少,且二者變化速度均呈增長趨勢:1990—2002年草地和未利用地的減少速度為0.2%和0.14%,而2002—2014年其減少速度為1.38%和0.99%;居民工礦用地面積增加,變化速度亦呈增長趨勢:1990—2002年居民工礦用地的增加速度為2.69%,而2002—2014年其增加速度已達5.55%,約為前一時段的2倍;耕地面積先增后減:增加速度為2.28%,減少速度為2.90%;林地和水域面積先減后增,減少速度分別為0.59%和1.44%,增加速度分別為2.57%和7.57%。

圖1 甘肅省白龍江流域1990-2014年各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速度
2.1.2 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速度 1990—2014年,流域的土地利用變化速度大幅增加,反映人類活動對土地利用類型變化的影響進一步加強(表1)。從各研究時段分析,1990—2002年的流域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為10.24%,而2002—2014年其增長至17.59%,與前一時段相比,增幅為71.77%。由于人類活動的區域差異性直接表現于土地利用變化上,而縣(區)可以集中反映人類活動的區域差異性,因此,流域內各縣(區)為單元探究土地利用變化對人類活動的響應更為重要。從圖2可知,1990—2002年,各縣(區)的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介于8.84%~13.08%(圖2);2002—2014年,各縣(區)的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介于13.60%~21.46%,各縣(區)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以不同程度增加,增加幅度由大到小依次為:文縣>宕昌縣>武都區>迭部縣>舟曲縣。

圖2 甘肅省白龍江流域1990-2014年各縣(區)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
2.2 流域土地利用類型轉移
1990—2014年,甘肅白龍江流域的土地利用類型變化以草地、耕地和林地的空間轉換為主,研究時段不同,表現出的土地利用類型轉移特點亦不同(表1)。具體到單個研究時段上來看,1990—2002年,草地的轉入和轉出面積分別為1 805.7和1 977km2,差值較小(171.3km2);耕地的轉入和轉出面積分別為1 113.98,376.95km2,差值最大(737.03km2);林地的轉入和轉出面積分別為1 051.57和1 615.04km2,差值較大(563.47km2),3種土地利用類型的主要轉移特點為:草地轉耕地,林地轉草地,耕地面積大增,林地面積大減,草地面積變動較小。同時居民工礦用地面積增加,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積減少。2002—2014年,草地的轉入和轉出面積分別為2 066.67和3 232.2km2,差值較大(1 165.53km2);耕地的轉入和轉出面積分別為638.24和1 834.82km2,差值較大(1 196.58km2);林地的轉入和轉出面積分別為2 993.56,725.67km2,差值最大(2 267.89km2),3種土地利用類型的主要轉移特點為:草地轉林地,耕地轉草地,林地面積大增,草地和耕地面積減少程度幾乎相等。同時居民工礦用地面積繼續增加,未利用地面積繼續減少,水域面積有所增加。
同時以縣(區)為單元的分析可知,流域內各縣(區)的土地利用類型轉移特點與整個流域的轉移特點基本符合,但各縣(區)的轉移程度差異比較明顯(附圖6)。
具體來看,1990—2002年,草地轉耕地主要分布在宕昌縣北部、武都區中北部以及文縣中北部;林地轉草地分布較為分散。2002—2014年,草地轉林地幾乎分布于流域內的所有縣(區),以文縣和迭部縣最為顯著;耕地轉草地主要分布在武都區,文縣次之(附圖6)。

表1 1990-2014年甘肅白龍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面積轉移矩陣
2.3 流域土地利用程度變化
1990—2014年流域的土地利用開發程度由強轉弱,各縣(區)表現不同,且差異逐漸變大。由圖3可知,1990—2002年,流域內各縣(區)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為正值,介于1.38~6.65,表明研究末期耕地和居民工礦用地面積增大程度大于林地和草地面積減少程度;2002—2014年僅有迭部縣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變化指數為正值(0.17),其余各縣(區)均為負值,介于-15.43~-1,表明研究末期耕地和草地面積減少程度大于林地和居民工礦用地面積增加程度,與1990—2002年相比,2002—2014年流域內縣(區)之間的土地利用開發程度差異明顯增加。

圖3 甘肅省白龍江流域1990-2014年各縣(區)土地利用程度變化
3 討論與結論
1990—2014年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甘肅白龍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速度大幅增加;1990—2002與2002—2014期間土地利用類型的主要轉移方向相反,由前期的草地轉耕地、林地轉草地轉變為后期的耕地轉草地、草地轉林地;土地利用開發程度先強后弱。這說明流域人類活動下的各土地利用類型間轉移明顯,人類活動對土地的利用由簡單索取開發型轉變為保護與生態建設型的利用方式,從破壞性、粗放式和低利用效率向保護性、集約式和高利用效率發展。
土地利用變化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產生,如1990—2002年,人口數量快速增長,在農業科技欠發達的條件下,人類僅能通過開墾荒地和毀林來進行農業擴張,以滿足人類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相應的也會出現過度放牧和濫砍濫伐的現象,在這樣的人類活動驅動下,流域土地利用呈現耕地面積增加,林地和草地面積減少的主要特點,如此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造成該時段流域內生態環境破壞嚴重;2002—2014年,人口數量雖繼續增加,但流域內生態環境卻逐漸恢復,這主要與退耕還林(還草)政策、天然林保護工程、長江流域防護林體系工程建設、公益林工程建設等大型生態建設工程的實施密切相關,此外,科學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調整、移民搬遷與安置、新農村建設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流域的人類活動,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流域土地利用呈現耕地面積大減,林地面積大增的主要特點。這與其他干旱區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因子是人口、政策、經濟和科技的結論一致[20-21]。
隨著國家政府部門對生態恢復工程的逐漸重視,以及近年來依舊出現的草場退化、土壤沙漠化和鹽堿化等生態環境問題,深入探討區域內土地利用變化與人類活動的響應關系成為土地利用變化研究中的重要分支。通過此研究,可以從土地利用變化角度定性分析某一時段的人類活動情況,在完全明晰人類活動對土地利用甚至是生態環境影響的前提下,所制定的一系列生態恢復政策才更具可操作性。值得一提的是,人類活動的定量化分析及人類活動的調控幅度研究將是下一步的深入探討突破的重點。
[1]RounsevellA,PedroliGBM,ErbKH,etal.Challengesforlandsystemscience[J].LandUsePolicy, 2012, 29(4):899-910.
[2] 吳琳娜,楊勝天,劉曉燕,等.1976年以來北洛河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對人類活動程度的響應[J].地理學報,2014,69(1):54-63.
[3]RamankuttyN,FoleyJA.Estimatinghistoricalchangesingloballandcover:Croplandsfrom1700to1992[J].GlobalBiogeochemicalCycles, 1999,13(4):997-1027.
[4]LambinEF,GeistHJ,LepersE.DynamicsofLand-useandland-coverchangeintropicalregions[J].AnnualReviewofEnvironmentandResources, 2003,28(1):205-241.
[5]GoldewijkK,RamankuttyN.Landcoverchangeoverthelastthreecenturiesduetohumanactivities:Theavailabilityofnewglobaldatasets[J].GeoJournal, 2004, 61(4):335-344.
[6] 蔡運龍.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研究:尋求新的綜合途徑[J].地理研究,2001,20(6): 645-652.
[7]JonathanAF,RuthDF,GregoryPA,etal.Globalconsequencesoflanduse[J].Science, 2005,309(5734):570-574.
[8] 劉紀遠,劉明亮,莊大方,等.中國近期土地利用變化的空間格局分析[J].中國科學(D):地球科學,2002,32(12):1031-1040.
[9]EduardoCR,VanButsic,VolkerC.Radeloff,etal.Technologyorpolicy?DriversoflandcoverchangeinnorthwesternSpainbeforeandaftertheaccessionto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J].LandUsePolicy, 2015, 45:18-25.
[10] 劉紀遠,張增祥,徐新良,等.21世紀初中國土地利用變化的空間格局與驅動力分析[J].地理學報,2009,64(12):1411-1420.
[11] 呂立剛,周生路,周兵兵,等.1985年以來江蘇省土地利用變化對人類活動程度的響應[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5,24(7):1086-1093.
[12] 王三,趙偉,黃春芳.基于遙感的重慶市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研究[J].中國農學通報,2010, 26(2):250-256.
[13] 魏曉華,孫閣.流域生態系統過程與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26.
[14] 劉紀遠.中國資源環境遙感宏觀調查與動態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15] 王秀蘭,包玉海.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研究方法探討[J].地理科學進展,1999,18(1):81-87.
[16] 宋開山,劉殿偉,王宗明.1954年以來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變化及驅動力[J].地理學報,2008, 63(1):93-104.
[17] 馮永玖,韓震.基于遙感的黃浦江沿岸土地利用時空演化特征分析[J].國土資源遙感,2010(2):91-96.
[18] 全斌.土地利用覆蓋變化導論[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19] 劉紀遠,布和敖斯爾.中國土地利用變化現代過程時空特征的研究:基于衛星遙感數據[J].第四紀研究,2000,20(3):229-239.
[20] 馬晴,李丁,廖杰,等.疏勒河中下游綠洲土地利用變化及其驅動力分析[J].經濟地理,2014, 34(1):148-156.
[21] 雷誠,張永福.土地利用變化及驅動因素分析:以新疆烏蘇市為例[J].新疆農業科學,2009, 46(2):403-409.
Response of Land Use Change on Human Activities in Bailongjiang Watershed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1990-2014
GONG Jie, ZHANG Jinxi, QIAN Caiyun, MA Xuecheng, LIU D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Objective]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response to human activities wer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in Bailongjiang Watershed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1990—2014,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land use optimization in the future. [Methods] Based on the land use data interpreted from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1990, 2002 and 2014, 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rate of land use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gree of land use in Bailongjiang watershed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1990—2014. [Results] The integrated dynamic degree of land use of the whole watershed increased from 10.24% to 17.59%. The change of land use types was mainly in grassland, arable land and forestland of the watershed during 1990—2014. Comprehensive change index of land use degree of all districts ranged from 1.38~6.65 during 1990—2002 to -15.43~0.17 during 2002—2014. [Conclusion] It proved that land use by human activities had converted from simple development to ecology prone one. Land use shifted from the types of destructiveness, extensive-type and low efficiency to the ones of conservation, intensive-ways and high efficiency in Bailongjiang watershed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1990—2014.
landusechange;humanactivities;BailongjiangwatershedofGansuProvince
A
: 1000-288X(2017)04-0219-06
: P951
2016-12-07
:2017-02-10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甘肅白龍江流域景觀格局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時空變化研究”(41271199); 甘肅省民生科技計劃項目(1503FCME006)
鞏杰(1975—),男(漢族),甘肅省寧縣人,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景觀生態學、土地變化科學、環境遙感與生態評價、生態系統服務等方面的研究。E-mail:jgong@lz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