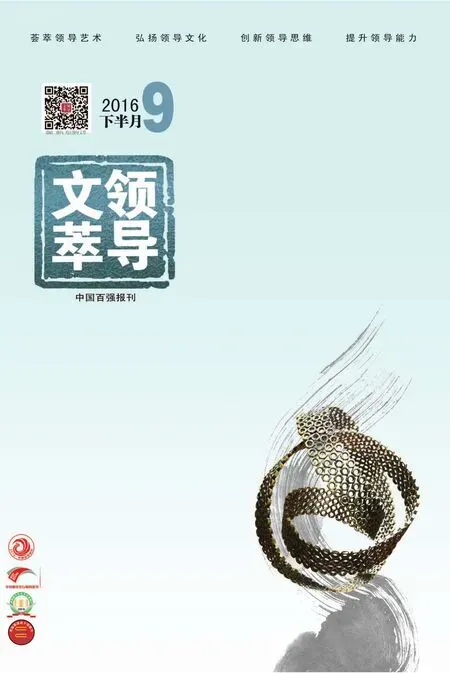開元名相姚崇
孟憲實(shí)
姚崇是陜州人,又名元崇,后來(lái)武則天為他改名為元之。讀《資治通鑒》,姚崇第一次出現(xiàn)在歷史的視野中,是在武則天萬(wàn)歲通天元年(696年),當(dāng)時(shí)大唐與契丹在河北發(fā)生了戰(zhàn)爭(zhēng),當(dāng)時(shí)姚崇是夏官郎中(兵部郎中),每天要處理大量文件,“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又快又好。武則天看了以后,大加贊賞,立刻提拔為兵部侍郎(副部長(zhǎng))。
武則天曾經(jīng)用酷吏政治來(lái)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周興、來(lái)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家破人亡成千上萬(wàn)。后來(lái)武則天清除了酷吏,又想推卸自己的責(zé)任,說(shuō)過(guò):為什么受害人自己要承認(rèn)呢?派了近臣去核實(shí),近臣為什么也不說(shuō)實(shí)話呢?現(xiàn)在,來(lái)俊臣等酷吏死了,再也聽不見有什么反逆案件,是不是當(dāng)時(shí)就有很多冤枉呢?武則天還是一個(gè)頭腦清醒的皇帝,能這么看,證明有反思能力。但群臣卻不知道如何回答。這時(shí)姚崇答道:當(dāng)然都是冤枉的,他們要翻案,會(huì)更遭毒手,所以寧可選擇死。近臣去核實(shí),他們的人身安全也沒(méi)有保障,也不敢了解真情,所以冤案重重。有告狀反逆的案件發(fā)生,皇帝只要知情但不推問(wèn),就不會(huì)有冤枉出現(xiàn)。姚崇所說(shuō)的推問(wèn),就是拿當(dāng)事人催問(wèn),唯一的辦法自然是屈打成招,結(jié)果凡是調(diào)查者想要的案情都能被當(dāng)事人證實(shí)。屈打成招是中國(guó)審案的絕招,簡(jiǎn)單快捷,馬到成功。姚崇說(shuō)了實(shí)話,武則天也給予表?yè)P(yáng),還賞賜白銀千兩。說(shuō)實(shí)話,要冒風(fēng)險(xiǎn),尤其面對(duì)皇帝曾經(jīng)的過(guò)錯(cuò),通常的情況是人人忌諱如深。姚崇敢于講出實(shí)話,不能不稱其勇敢。
長(zhǎng)安四年(704年),姚崇因?yàn)槟咐希丶茵B(yǎng)親,同時(shí)擔(dān)任了相王府的長(zhǎng)史,相王就是睿宗李旦。不久,武則天又任命姚崇擔(dān)任兵部尚書,相當(dāng)于國(guó)防部長(zhǎng)。姚崇立刻上書回絕:“作為相王的長(zhǎng)史,知兵馬不便,非臣惜死,恐不益相王。”兵部尚書,只有皇帝信任的人才能擔(dān)任,掌管軍事,也是最重要的權(quán)力。這是皇帝的信任,怎么會(huì)拒絕呢?因?yàn)橐Τ缤瑫r(shí)擔(dān)任相王府的長(zhǎng)史,屬于相王的臣下,如果再兼任兵部尚書,很容易引發(fā)人們對(duì)相王權(quán)力過(guò)大的猜想,這樣就會(huì)導(dǎo)致相王的政治安全發(fā)生問(wèn)題。姚崇護(hù)主,拳拳之心清晰可見。武則天表示理解,讓他改官禮部尚書。這一年,文武雙全的姚崇,又被任命為靈武道大總管,前往北方領(lǐng)兵,守衛(wèi)北方。
武則天晚年,“二張”問(wèn)題十分突出,作為武則天信任的情人,張易之、張昌宗兄弟過(guò)分弄權(quán),引起朝臣的極大反感。神龍?jiān)辏?05年),張柬之、桓彥范等五位大臣決定發(fā)動(dòng)政變,為唐朝奪回政權(quán)。政變發(fā)生之前,正好姚崇回京述職。據(jù)說(shuō),姚崇被派到前線領(lǐng)兵,正是“二張”的主意,說(shuō)明姚崇也是討厭二張的。于是張柬之等聯(lián)系姚崇,姚崇因而成為神龍政變的預(yù)謀者。神龍政變雖然以“二張”為口實(shí),其實(shí)是針對(duì)武則天的,這一點(diǎn)天下共知。為了更好地防范武則天,新朝廷決定把武則天移居上陽(yáng)宮。中宗率領(lǐng)文武百官為武則天送行。史書記載,“王公以下皆欣躍稱慶”。武則天下臺(tái)了,唐朝恢復(fù)了,彈冠相慶的表現(xiàn)是普遍的,也是正常的,不僅是心情,還包括政治正確。于是,姚崇的表現(xiàn)就顯得太突出,太有問(wèn)題了,“元之獨(dú)嗚咽流涕”。在人人稱快的場(chǎng)景中,只有姚崇一個(gè)人在獨(dú)自流淚。桓彥范、張柬之看在眼里,自然很不高興,他們對(duì)姚崇說(shuō):“現(xiàn)在是哭泣的時(shí)候嗎?你的麻煩恐怕已經(jīng)開始了。”
很快,姚崇就被貶官外地,先是任亳州刺史,后來(lái)又轉(zhuǎn)為常州刺史、許州刺史等。當(dāng)時(shí),正是張柬之、桓彥范這些神龍政變的功臣執(zhí)掌朝政,為首的五位領(lǐng)導(dǎo)人,也被中宗封為郡王,號(hào)稱“五王”。但是,歷史的戲劇性從來(lái)都出人意表,誰(shuí)會(huì)想到,朝局的變化很快就發(fā)生了。唐中宗與“五王”分道揚(yáng)鑣來(lái)得太快,“五王”先是離開政治中心,接著也遭遇貶官,最后都是死非其罪,結(jié)局都不好。姚崇人在地方,反而沒(méi)有受到什么牽連,一直太平無(wú)事。政治戲劇中的塞翁失馬故事,真是比比皆是。在地方刺史崗位上,姚崇沉靜多年,這為他后來(lái)的重新崛起儲(chǔ)備了足夠的力量。
通過(guò)唐隆政變,李隆基和父親睿宗、太平公主的力量擊敗韋皇后的勢(shì)力,睿宗第二次成為唐朝的皇帝。這時(shí),朝廷的宰相班子重新組建,有中宗時(shí)期的宰相,據(jù)說(shuō)都是太平公主推薦的;也有姚崇、宋璟這樣的新人,他們兩人的背景,很可能是當(dāng)時(shí)擔(dān)任太子的李隆基。
睿宗時(shí)期,從后來(lái)的歷史進(jìn)程看,依然是一個(gè)過(guò)渡時(shí)期的狀態(tài),而姚崇代表著新的希望。因?yàn)槌⒅嘘P(guān)系復(fù)雜,姚崇能做的工作有限,但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果敢的政治家氣魄。
姚崇在朝廷的最高層斗爭(zhēng)中,屬于太子李隆基一派,因?yàn)榻ㄗh鞏固李隆基的權(quán)力,抑制太平公主的勢(shì)力,最讓太平公主受不了。711年二月,他遭遇貶官,外放為申州刺史,他的搭檔宋璟貶為楚州刺史。此后,朝廷的斗爭(zhēng)持續(xù)向高潮發(fā)展。從現(xiàn)在看到的史書,主要是太平公主從事?lián)v亂,要調(diào)換太子李隆基,其實(shí)質(zhì)應(yīng)該是睿宗提防太子,雙方屬于最高端的政治斗爭(zhēng)。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睿宗傳帝位給太子,自稱太上皇,太子李隆基即位成為皇帝。但是,重大的權(quán)力還在太上皇手上,雙方的斗爭(zhēng)并沒(méi)有到達(dá)終點(diǎn)。713年七月,朝廷的矛盾公開化,玄宗作為皇帝,親自發(fā)動(dòng)政變,殺太平公主等黨徒,睿宗放棄所有權(quán)力,玄宗完全執(zhí)政。
此時(shí)姚崇是同州刺史。開元元年(713年)冬十月,玄宗在新豐縣的謂川行獵,忽然召見姚崇,當(dāng)場(chǎng)任命姚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即宰相。關(guān)于這次見面,史書記載頗有戲劇性,如姚崇如何再三突破阻力等等。不過(guò),《開元升平源》所記,確有一定道理。就在這次會(huì)面中,姚崇向玄宗提出振興“十策”,史稱“十事要說(shuō)”,可以認(rèn)為完全把脈清晰,對(duì)癥下藥。十事,可以歸納為三個(gè)方面,一是穩(wěn)定政局,結(jié)束此前的亂政,如不許皇親國(guó)戚干預(yù)朝政,推行仁政,緩和社會(huì)矛盾。二是整頓吏治,取消一切斜封官,國(guó)親不得擔(dān)任御史臺(tái)、三省的重要官員,賞罰分明,同時(shí)鼓勵(lì)進(jìn)諫,禮敬大臣,養(yǎng)成良好的政治風(fēng)氣。三是改善財(cái)政狀況,穩(wěn)定邊疆,不求邊功,防止浪費(fèi),禁止建設(shè)佛廟、道觀等。玄宗聽到姚崇的十項(xiàng)建議,非常認(rèn)同。君臣對(duì)于時(shí)政認(rèn)識(shí)的高度契合,是密切合作的基礎(chǔ)。開元之治的曙光,就這樣出現(xiàn)在一次行獵的路上。
姚崇執(zhí)政后,基本上實(shí)現(xiàn)了他的十項(xiàng)政策。開元四年,姚崇辭相位,五年之后去世,年七十二。
(摘自《國(guó)家人文歷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