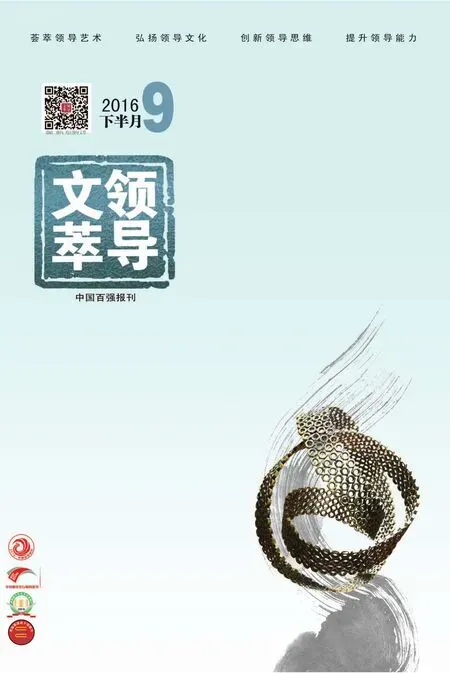大國(guó)反腐:“蘇聯(lián)方案”為何敗于“美國(guó)方案”
高波
1959年夏天,美國(guó)副總統(tǒng)理查德·尼克松造訪莫斯科,主持美國(guó)展覽會(huì)開(kāi)幕式。在名為“典型美國(guó)住宅”的展品前,他與蘇聯(lián)領(lǐng)導(dǎo)人赫魯曉夫之間爆發(fā)了轟動(dòng)一時(shí)的“廚房辯論”。兩人在剛剛興起的電子攝像機(jī)的鏡頭前展開(kāi)舌戰(zhàn),竭力讓對(duì)方相信本國(guó)制度更加優(yōu)越、自己的世界觀更加正確。
在當(dāng)時(shí)的冷戰(zhàn)背景下,“美版廚房、美式用品、美國(guó)制造”作為“美國(guó)方案”的現(xiàn)實(shí)載體,承載了意識(shí)形態(tài)的斗爭(zhēng)色彩,帶有挑戰(zhàn)蘇維埃生活方式及“蘇聯(lián)方案”合法性的濃烈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廚房辯論”當(dāng)事人的尼克松,在有生之年見(jiàn)證了蘇聯(lián)的解體。他在接受CNN(美國(guó)有線電視新聞網(wǎng))采訪時(shí)指出:當(dāng)時(shí)我知道赫魯曉夫肯定是錯(cuò)的,但是其實(shí)我不知道我是對(duì)的。
是什么壓垮了“蘇聯(lián)熊”
美國(guó)和蘇聯(lián),都是前所未有的超級(jí)大國(guó),也是冷戰(zhàn)時(shí)期的世界兩極。兩強(qiáng)對(duì)峙,美國(guó)人何以笑到最后,分析林林總總。其中一個(gè)較為公認(rèn)的原因是,蘇聯(lián)人是“自己打敗了自己”。特別是蘇共黨內(nèi)的特權(quán)和腐敗等問(wèn)題,成了壓垮“蘇聯(lián)熊”的最后幾根稻草之一。很多研究者指出,蘇聯(lián)政權(quán)的崩塌是從信仰的瓦解開(kāi)始的,其根源是國(guó)家治理體系以及信仰體系與本國(guó)現(xiàn)實(shí)脫節(jié)、與人民需求相悖。
到了1985年,在戈?duì)柊蛦谭驎r(shí)期任總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說(shuō):“我們監(jiān)守自盜,行賄受賄,無(wú)論是在報(bào)告中、報(bào)紙上還是在高高的講臺(tái)上都謊話連篇,我們沉溺在自己的謊言之中,為彼此頒發(fā)獎(jiǎng)?wù)隆K腥硕歼@么做,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回顧蘇共執(zhí)政74年、蘇聯(lián)立國(guó)69年的歷史,從蘇共轟轟烈烈登上歷史舞臺(tái),到帶領(lǐng)蘇聯(lián)建成全球第二、歐洲第一的經(jīng)濟(jì)強(qiáng)國(guó),再到一朝傾覆,黯然出局。正是由于停滯、僵化的“蘇聯(lián)病”弊端,不但導(dǎo)致蘇聯(lián)政治笑話的蔓延,更導(dǎo)致蘇聯(lián)崩潰情緒的傳染。
“美國(guó)方案”與“蘇聯(lián)方案”都不是標(biāo)準(zhǔn)答案
古往今來(lái),腐敗現(xiàn)象和腐敗治理如影隨形。人們?cè)诓煌臅r(shí)代和國(guó)家,不斷提出并實(shí)施各種方案,試圖將腐敗現(xiàn)象背后的公權(quán)馴服,將隱藏于腐敗問(wèn)題深處的私欲改良。然而,就蘇美這樣的大國(guó)來(lái)說(shuō),成效確實(shí)不如想象的大。曾有西方專家指出:“蘇聯(lián)的錯(cuò)誤在于將利益這一因素從經(jīng)濟(jì)因素中移除,認(rèn)為割裂利益同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聯(lián)系可以為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專政提供足夠的條件。”但從腐敗和治理腐敗的角度看,蘇聯(lián)失敗的根源并不是“去利益化”,而恰恰是“利益集團(tuán)化”,或者說(shuō)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和相關(guān)利益落入了“少數(shù)特權(quán)派”的私囊。美國(guó)的“體制性腐敗”問(wèn)題實(shí)質(zhì)上頗為類似,美國(guó)因財(cái)富分化等因素導(dǎo)致的貧困水平甚至比俄羅斯、波蘭和韓國(guó)都要高。因此,美國(guó)總統(tǒng)羅納德·里根曾經(jīng)評(píng)論說(shuō):“我們和貧困奮力一戰(zhàn),結(jié)果,貧困贏了。”
歸根結(jié)底,腐敗治理是國(guó)家治理體系的特殊視窗,檢驗(yàn)的是國(guó)家治理能力。
就“美國(guó)方案”來(lái)說(shuō),主要是以利益沖突防控為核心理念,建立政商兩界“區(qū)隔前臺(tái)、打通后臺(tái)、相互站臺(tái)”的“旋轉(zhuǎn)門(mén)”機(jī)制,輔之以競(jìng)選類政務(wù)官(政治家)和考績(jī)制事務(wù)官(公務(wù)員)分途共治的公職譜系,以及市場(chǎng)化的薪酬體系和開(kāi)放參與機(jī)制,從而分散腐敗風(fēng)險(xiǎn),改善政治“觀感”。
相比之下,“蘇聯(lián)方案”則主要是以政治治理統(tǒng)攝乃至“覆蓋”國(guó)家治理體系為核心特征,建立以干部委任制、終身制為基軸的公職配置機(jī)制,以及以供給制為基礎(chǔ),并由特殊津貼、特供商品、特享別墅等共同構(gòu)成的干部福利保障體系,從而在對(duì)干部利益和欲望進(jìn)行“結(jié)構(gòu)化滿足”的基礎(chǔ)上,弱化執(zhí)政黨核心成員和團(tuán)隊(duì)成員的貪腐動(dòng)機(jī)。
其實(shí),這兩種“大國(guó)方案”都不是腐敗治理可以照抄照搬的標(biāo)準(zhǔn)答案。正如事實(shí)一再揭示的那樣:“美國(guó)方案”究其根本是一條競(jìng)逐經(jīng)濟(jì)特權(quán)之路,而“蘇聯(lián)方案”察其始終是一條追慕政治特權(quán)之路。衡量社會(huì)成員成功與否的最大標(biāo)志,是能否成為各自“特權(quán)俱樂(lè)部”的一員——區(qū)別無(wú)非是兌現(xiàn)或變現(xiàn)特權(quán)的地方,究竟是在華爾街還是在克里姆林宮。
坦白說(shuō),這兩條路都不怎么樣,別的國(guó)家也走不通。它們不能提供可簡(jiǎn)單克隆的“大國(guó)基因”,也難以帶來(lái)可供通篇抄襲的“強(qiáng)國(guó)秘籍”。
就“美國(guó)方案”來(lái)說(shuō),其與之俱來(lái)的結(jié)構(gòu)性問(wèn)題早就被托克維爾點(diǎn)透:“如果我們追問(wèn)美國(guó)人的民族性,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美國(guó)人探尋這個(gè)世界上每個(gè)事物的價(jià)值,只為回答一個(gè)簡(jiǎn)單的問(wèn)題:能掙多少錢(qián)?”
就“蘇聯(lián)方案”而言,最大的問(wèn)題在于豢養(yǎng)了黨內(nèi)的特權(quán)階層。斯大林時(shí)期實(shí)行的個(gè)人集權(quán)制、職務(wù)終身制、指定接班制、等級(jí)授職制、官員特權(quán)制等,使得蘇聯(lián)社會(huì)缺乏社會(huì)主義民主、自由和法治,國(guó)家治理體系的結(jié)構(gòu)性弊病越來(lái)越嚴(yán)重。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shí)期,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huì)和黨委會(huì)每次改選必須更換四分之一成員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事實(shí)上的干部終身制。這種政治生態(tài)逐漸形成了一個(gè)穩(wěn)定的特權(quán)階層。這個(gè)特權(quán)階層為維護(hù)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種實(shí)質(zhì)性的改革,導(dǎo)致蘇聯(lián)深陷機(jī)構(gòu)臃腫和官僚主義的泥沼。
“美版腐敗”和“蘇式腐敗”結(jié)局迥異之謎
值得今天的人們思索的是,幾乎同樣處于動(dòng)蕩政局的“風(fēng)暴眼”時(shí),為什么“美版腐敗”沒(méi)有導(dǎo)致國(guó)家分裂,而“蘇式腐敗”卻造成了普京所說(shuō)的“20世紀(jì)最大的地緣政治災(zāi)難”?當(dāng)美國(guó)在“鍍金時(shí)代”遭遇誠(chéng)信缺失、貪腐橫行等重大考驗(yàn),面臨“國(guó)家重組”的重大挑戰(zhàn)時(shí),人們?yōu)槭裁礇](méi)有選擇“跳船”,也沒(méi)有選擇“棄船”?而當(dāng)蘇聯(lián)出了問(wèn)題的時(shí)候,人們棄之唯恐不及。特別是擁有1900萬(wàn)黨員、執(zhí)政74年之久的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甚至無(wú)力做出“應(yīng)激反應(yīng)”,在沒(méi)有任何痛苦和抗?fàn)幍那闆r下自行消亡和解散。
應(yīng)當(dāng)說(shuō),腐敗問(wèn)題并不是“蘇亡美興”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區(qū)別在于,當(dāng)整個(gè)國(guó)家直面“腐敗之痛、貪瀆之恥”時(shí),人民做出了怎樣的選擇?
美國(guó)人民在抱怨中選擇了和這個(gè)腐敗的國(guó)家一同改進(jìn)。正如美國(guó)史學(xué)家弗雷德里克·L.艾倫所總結(jié)的那樣:“當(dāng)國(guó)家這艘大船偏離航線的時(shí)候,也就是說(shuō)它沒(méi)有按照應(yīng)有的方式運(yùn)轉(zhuǎn)的時(shí)候,你完全沒(méi)有必要?dú)У羲缓罅碓煲凰掖蟠喾矗偃邕@艘大船上的全體船員始終都保持著警惕、時(shí)刻都仔細(xì)地檢查,并且及時(shí)修補(bǔ)的話,你完全可以通過(guò)一系列的調(diào)整和改進(jìn),一邊保證它繼續(xù)行駛,一邊進(jìn)行維修。”
蘇聯(lián)人民則喪失了希望。1990年10月24日—11月5日,蘇共中央社會(huì)科學(xué)院社會(huì)學(xué)研究中心的一項(xiàng)問(wèn)卷調(diào)查已現(xiàn)端倪:關(guān)于對(duì)社會(huì)主義的信仰,有30%的被調(diào)查者直接宣布對(duì)共產(chǎn)主義思想失望,每5人中就有一名黨員對(duì)黨的綱領(lǐng)目標(biāo)持否定態(tài)度;關(guān)于黨的威信和作用,有21%的被調(diào)查者認(rèn)為黨組織已不具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認(rèn)為其殘存的威信也在喪失,且每5人中就有一人指出自己已經(jīng)脫離了政治生活……
腐敗就是腐敗,既不應(yīng)當(dāng)在國(guó)家崩潰的歷史審判席上缺席,也不應(yīng)該大包大攬為那些國(guó)家治理體系的結(jié)構(gòu)性“硬傷”頂罪。當(dāng)蘇共自我凈化、自我糾錯(cuò)的功能被“閹割”之后,這個(gè)曾經(jīng)的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領(lǐng)頭羊的生機(jī)活力與日俱減。蘇聯(lián)解體的親歷者麥德維杰夫深刻反省說(shuō):“這樣一個(gè)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突然間由于并不猛烈的沖擊而開(kāi)始削弱和瓦解,這個(gè)強(qiáng)大國(guó)家的命運(yùn)只能說(shuō)明一個(gè)問(wèn)題,即蘇聯(lián)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jiān)固和不穩(wěn)定的基礎(chǔ)之上的,其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chǔ)被沖毀和削弱,如果承重結(jié)構(gòu)被侵蝕和破壞,那么無(wú)論看起來(lái)多么堅(jiān)實(shí)和宏偉的建筑都會(huì)倒塌。1991年正是發(fā)生了這樣的劇變。”而民心盡失,民意所向,或者說(shuō)人民對(duì)這一切的集體漠視和袖手旁觀,才是劇變背后真正的最大危機(jī)。
(摘自《廉潔拐點(diǎ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