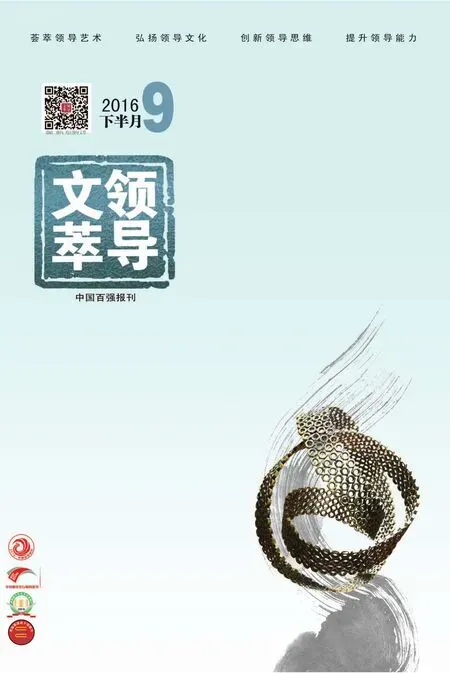中國智庫應多些“基辛格”
王文
今年五月,89歲高齡的美國前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去世,引起中國輿論的一陣學術懷念。多數(shù)紀念文章不是去評論他作為美國高官的政績,而是對他的戰(zhàn)略思想推崇備至,尤其驚嘆于他在退休后任智庫學者期間連續(xù)出版《大棋局》《大失控與大混亂》等著作。中國人崇敬的美國戰(zhàn)略思想家當然還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筆者常想,為什么中國智庫就出不了像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這樣能傳播本國思想、提升本國外交軟實力的人物?這些年,筆者走訪西方數(shù)十家智庫,發(fā)現(xiàn)歐美一流智庫的管理層大多有在政府擔任高層管理的履歷。尤其是在外交部、國防部等擔任過副職的西方前高官,最愿意利用智庫平臺,為本國利益與社會發(fā)展發(fā)揮個人余熱。這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長期以來,我們對歐美智庫的研究,多注重于智庫的性質、作用、規(guī)模等外部因素,對智庫微妙的內部運行機制與細致的官民交流方式的探索還遠遠不夠。筆者接觸的歐美前高官的優(yōu)勢是其他從業(yè)者很難獲得的:
一是政策敏感度。前高官都有規(guī)劃、制定、執(zhí)行相關政策的經(jīng)驗,也知道政策運行的困難和障礙,更能理解政策推進的路徑與最佳時間點。從事智庫工作后,以特有的政策敏感性和問題意識,準確選取研究課題,選擇推進的最佳時間點等。
二是高層關系網(wǎng)。智庫決策影響力的關鍵,在于能夠把高質量的政策研究報告送到最合適的決策者手里。這需要快捷、便利的內參報道渠道,還需要有熟絡、可信的政府人脈關系。這些對于曾在政府任職的前高官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
三是對外傳播力。在歐美發(fā)達國家政府中任職的官員,語言表達是一項基本素質。他們通常懂得在合適的場合、以合適的表達方式、講出最適合聽眾懂的話,這是一項對國家公共外交相當重要的能力。
四是籌款能力。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歐美發(fā)達國家智庫的經(jīng)費一般有20%~35%來源于政府項目撥款。前高官的加盟無疑能夠幫助智庫拿到政府的研究經(jīng)費。
近年來,中國有越來越多的退休高官開始加入智庫,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fā)展建策建言。但如何善用退休干部,仍是值得摸索的復雜課題。其本質不僅在于官員退休后的去向,更在于智庫本身需要有大量熟悉決策進程的研究者和運營者。更確切地說,目前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急需要人事拓展機制的改革。
從長遠看,新型智庫的建設需要打造中國式“旋轉門”。智庫可定期選派學者到各級政府掛職鍛煉,政府也可選拔官員重回各類智庫鍛造。長期下來,智庫與政府之間的相互溝通與理解將大大加強,學有所用的智庫學者與有思想底蘊的官員將大量應運而生。在此基礎上,智庫就能夠且善于運用退休但精力充沛的老干部,讓他們像基辛格那樣年逾90歲仍能為國家利益服務。
(摘自《環(huán)球時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