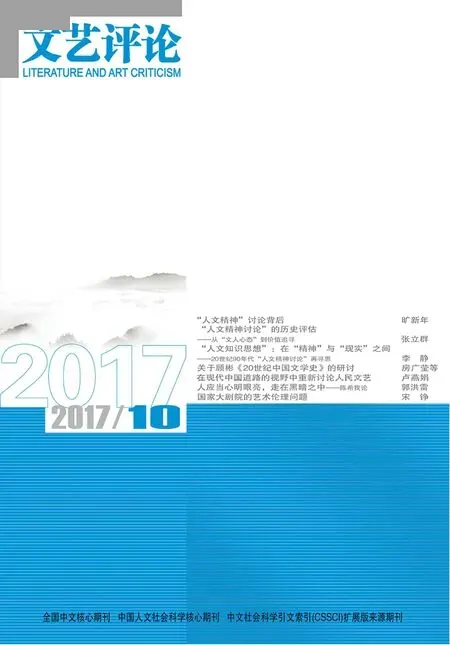想象中國方式一種
——評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
○房廣瑩
想象中國方式一種
——評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
○房廣瑩
顧彬因“垃圾論”事件成為漢學界“網紅”,他的驚人言論在國內讀者間的影響遠大于其書籍本身,這樣的效果恐怕與他本人的意愿相違背。為了洗刷“污名”,顧彬不止一次公開聲明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并且出于對中國的熱忱而撰寫、出版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一書。人們固然應該警惕“垃圾論”背后媒體炒作的嫌疑,但更應該意識到當前中國新文學史書寫所面臨的困境。顧彬作為浸染于德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恐怕無法真正實現與中國文化的完美對接,其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之間的裂痕和隔膜也就在所難免。因此,盡管顧彬處處表達著對“中國”的癡迷,翻譯出版了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為溝通中歐文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僅從《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一書看來,他的立場合理中包含謬誤,深刻中不乏偏激,可以說是一個矛盾重重的綜合體。
一、難言難說的“憂郁”
顧彬非常清楚文化之間的隔膜難以逾越,但在他的觀念中,充滿了與中國文化對話的渴望。因此,當面對“你不是中國人,你怎么能獲得中國人的知識”的責問時,顧彬急切地尋找一種詮釋的突破口。在中國作家筆下努力尋找“憂郁癥”的痕跡,是他進入《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通道之一。然而中國傳統文學史極少用“憂郁”來形容作家的創作風格或者抒情情調,造成顧彬對某些作家的評價往往呈現出與以往文學史不同的基調。例如他用了比較多的篇幅探討郁達夫的小說創作,認為“郁達夫可能是第一個能夠用本土語言去詮釋西方感傷病故事的核心概念、且予充分理解的中國作家”①。郁達夫固然深受西方影響,強調自我靈與肉、壓抑與反壓抑的沖突,但他是否試圖詮釋一種西方式的感傷病癥,還需要更加確鑿的論證。同樣,在丁玲那里,顧彬也看到了這憂郁的火苗,“丁玲用稍帶諷刺意味的口吻描寫了事實上的優裕處境與以貧乏自居的姿態間的矛盾,按照當時的時代精神,作家當然應該是苦悶而憂郁的。”②甚至在論述郭沫若詩歌中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個人的悲哀時,也采用了“熱情取代憂郁”的斷語。顧彬積極地肯定以上幾位作家的創作,認為他們無一不在展現時代的心靈危機和現代人的孤獨苦痛,并且將這些精神氣質籠統地歸結為——憂郁。
作者反復且含混地使用“憂郁”這一概念,卻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符合學理要求的內涵解釋,這就反而給讀者理解郁達夫、郭沫若、丁玲等作家設置了疏離的障礙。作為補充,他在《解讀古代中國的“憂郁感”》一文中較為透徹地為讀者解疑,“現在知道,accedia,一種西方中世紀基督教僧侶的苦修活動,是現代性憂郁的發端……現代性的憂郁,即開始于文藝復興以來的憂郁,不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態度,一種心靈狀態。它的出現伴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當面對著無限的時間和空間的時候,人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他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他竭盡全力擴展他的知識;但是,仍然不能認識一切事物。他不得不把自己局限在他的知覺限度內”③。可以說,顧彬之所以對憂郁情有獨鐘,是因為他對西方現代文化語境中自我有限性的深刻體認,這可能源于西方社會在受到現代性的沖擊后,與基督教剝離后精神無所依從的無家之感。更讓西方學者感到無力的是,即便現代人努力擴展知識的邊界與容量,也無法擺脫這種命定的“罪”——宿命般的孤獨與憂郁。
“憂郁”是顧彬為我們提供的一種帶有歷史視角的認知方式,在他看來,每個人都烙有文化傳統的印記,而每一位作家都應該放置于歷時和共時的坐標中進行解讀。這樣的方式本身并無問題,而且這與國內的中國文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只是顧彬沒有注意的是,在具體到“憂郁”這個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時,中國現代作家所處的傳統流脈和時代語境,似乎不能與西方吻合。其一,中國傳統文化里并沒有明確出現過“憂郁”這一詞語,倒是有一些字面相近的表達,比如“憂愁”“哀愁”等。這些心靈癥狀的產生主要來自于人與世界的碰撞,在傳統的“君臣、父子、夫婦”關系中逐漸生發并確定下來,它們并不表現西方現代層面上人與世界本質的不可縫合的裂隙,而是能夠通過具體困境的化解得到緩解。其二,受西方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現自我,創造自我”思潮的影響,五四時期的作家們將“自我”強調到空前的高度。盡管郁達夫等作家深深地感知到社會體制對個人的壓抑與戕害,在其前期創作中表面上是意圖消解梁啟超為代表的民族國家主義敘事,但這種以個人為本位的現代文化邏輯本質上是要求國家為個人的自由和幸福負責,更本源的是要求國家的強大和民族的自尊。也就是說,在救亡圖存這一層面,個人感傷與國家復興是一體兩面。從文化繼承與世代主題角度看,現代作家表現的憂郁與顧彬所謂的憂郁,在背景和內涵意義上并不相同,更談不上“詮釋西方感傷病故事”了。
二、彎彎繞繞的“現代性”
僅從顧彬不深入考察東西方歷史文化背景差異,簡單地認定郁達夫、丁玲等作家繼承西方“憂郁”心靈的思想理路即可窺見,顧彬對中國文學的批評邏輯是以現代性為中心的,并且以揭示所謂的中國人憂郁內心為最高準則。秉持這種批評原則,顧彬堅持認為小說這一文體最能體現現代性的特質,即使他對中國當代詩歌的評價更高,但是始終堅持小說體裁的流行才是中國現代文學進入世界文學軌跡的標志,因為“小說應成為一種出自政治意識和國家信念的新意識形態的載體”④。正因如此,許多批評家詬病顧彬對具體作家作品的不恰當評論,認為他片面抬高郁達夫、郭沫若等作家的文學地位,更無法理解他所謂“忽略情節正是現代小說的特征之一”的武斷評述。可見其評價作品的出發點并不在文本的文學性,而更關注作品是否體現了“優越的”現代性上。
正是在這一文化邏輯的支配下,顧彬對當代文學的成就評價很低。比如在他看來,莫言就是一位藝術上非常落后的作家,因為現代性的作家不會用傳統的章回體形式來寫作;先鋒小說是一種反動的現代主義;“尋根文學”更被單一地歸結為作家們夸張的反神話意圖。中國文化傳統被顧彬武斷地視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最大負面障礙,重回傳統即意味著當代作家主動拋棄現代性的文學創作原則。
基于崇尚現代性的文學觀和歷史觀,顧彬又設置出三個具體參照系,其一是世界性文學標準,可以窄化為歐洲文學標準;其二是本土作家的外語水平;其三是作家的語言駕馭能力。在他的批評實踐中,我們不難發現,后兩個參照標準統一在“世界文學”之中。眾所周知,20世紀中國文學具有豐富駁雜的歷史景觀,在連綿不息的論爭和思潮中努力拓寬自我格局,在反思和突破中闡釋文學發展的精神向度。顧彬用窄化的“世界性”眼光之履,讓中國文學來試足,自然引起廣大讀者和批評家情感及理智的反彈。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顧彬隨意的判斷和情緒化的取舍,總是能夠對讀者發出干擾電波。例如,“從西方人角度看,所謂的‘譴責小說’要優越于‘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和‘科幻小說’”⑤,在討論郁達夫小說《沉淪》結尾時,有如下論斷:“保守的詮釋者會對該結尾信以為真,可從西方視角讀來,如果不把它當做戲仿來理解和翻譯,這段文字會不由自主地顯得滑稽、媚俗……”⑥如以上這般缺乏內部邏輯、表意不詳之處不勝枚舉,使得顧彬在深入文學史實和文本內涵之處捉襟見肘,而這種表述中突兀的揚西抑中的傾向,難免落下西方中心主義的口實。
從整體結構上看,這部文學史明顯出現頭重腳輕的弊端。顧彬用大量篇幅描寫現代文學史,卻極力擠壓新時期文學的分量:張抗抗、王安憶、鐵凝、賈平凹、格非等作家如浮光掠影,只著片縷地一筆帶過,更遑論歷次文壇論爭和新詩流派的起落。可以說,新時期文壇在他筆下,呈現出支離破碎的片段式閃爍景象。黃修己認為:“最好不要用邏輯來代替歷史本身,不要用理論來剪裁歷史事實。”⑦顧彬恰反其道而行之,按照“顧彬式”的輪廓描摹20世紀中國文學史面貌,處處體現以論代史的寫作思路。然而流動多變、眾聲喧嘩的新時期文學早已不能用單一的“憂郁”現代性來框定。盡管顧彬一直聲稱對“中國的執迷”,并且反復提醒中國讀者警惕“自我東方化”的心態,可正是他自己用失衡的“世界性眼光”損害著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整體格局。
三、大有可為的“介入”
當然,顧彬的文學史寫作雖然有諸多矛盾與謬誤,但其努力和嘗試以及所得的成果同樣不容忽視。這不得不引出一個話題,那就是異文化的介入和闡發在何種程度上成為可能?語言的“巴別塔”在顧彬那里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步入崇高殿堂的阻礙,文化的“巴別塔”正是橫亙在這場“垃圾論”中的高墻。只有異質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才能在厚重的隔膜間打出一些孔洞,盡管時有誤讀和遮蔽,但是總還能起到煥發雙方文化生機的作用。
顯然,顧彬在與中國文學的對話中尋找緩釋“憂郁”的藥方,可以從他贊同樂黛云為《關于“異”的研究》所做的序中找到端倪。樂黛云認為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大抵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在‘異域’中尋找與自身相同的東西,將‘異域’的一切納入本地的意識形態,以證實自己所認同的事物,或原則的正確性或普遍性;一種是將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異域’,把‘異域’構造成自己的烏托邦”⑧。對于顧彬而言,與上帝的分離造成人無法理解他人和理解自我的雙重局限性,促使他在漢學領域的求索中制造新的信仰。
顧彬在進行自我認知體系的編織時,也確實提供了一部個性鮮明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在眾多肯定顧彬文學史寫作的批評家看來,他的作品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注腳。從當前情況來看,其一,盡管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數量龐大,但是為了克服視野狹窄和史料疏漏等問題,較多地采取集體撰寫的方式,其功能也主要用于高校文科教材。因此,文學史寫作更注重知識性和普遍性,更多作家作品的介紹和史料的累積,缺乏獨到的批評眼光和具有穿透力的理論建設。其二,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學史的編撰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即使王瑤、劉綬松等人奠定了個人寫新文學史的基礎,可是依然受到時代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缺乏學術個性和創新性。本土文學史編纂現狀可謂陳陳相因,重復“撞車”,顧彬的文學史寫作反而在這片相對沉寂的海域中攪起波浪,“在這種更需要‘他者’視角的介入和參照、以引起我們深度反思的情況下,顧彬文學史的問世就愈發可貴”⑨。因此,盡管顧彬的“世界性”評價標準自相矛盾、史料史實漏洞頻出,但是他能夠運用異質化的學術體系和比較的眼界,為新文學史書寫提供新理路。
顧彬是一位有雄心的理論家,他著力打造一部作為思想史的文學史。通常情況下,歷史學的重心在于考察史料的真實性,文學史除了標注材料的“真”以外,還要關照“善”和“美”的價值維度,著力于展現人類的時代心靈。文學史除了是歷史的,更應該具備文學的、藝術的特性。顧彬從來不避諱在書中表達個人的文學觀,因“感時憂國”的焦慮生發出中國式“現代性”,成為他的敘事中心,并且貫穿始終,“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大變革與民族國家相聯系,將20世紀文學的日益激進化和一體化與中國現代性的‘單邊性’特質相聯系,從而對這些重大的文學問題的歷史動因做出更為深層的、整體的把握”⑩盡管這種思路容易剪裁出一個充斥著曖昧現代性的理論模型,但是顧彬始終在追問20世紀中國文學的特質,使看似散亂的文學現象能夠統罩在一起,或許能夠從中窺見出整個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訴求和時代心靈。同時,顧彬還采用從“邊緣”和“中心”兩個方面看中國文學的思路,整合1949年后不同意識形態下兩岸四地的文學發展歷程,展現兩岸對文學現代性的追求。也許正是因為作者“異”文化的身份,使他脫離了意識形態的約束和歷史的局限性,能夠以一定的審美距離關照和考量20世紀中國文學。
毋庸置疑,文學史寫作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特別是面對流動的現當代文學現場時,如何處理文學與歷史、區域與整體等關系,更是難上加難。我們借助顧彬這位“他山之石”,以期形成良好的交流和爭鳴的文學生態環境,激活自身文學史書寫活力,才更有價值。
①②④⑤⑥[德]顧彬《20世紀中國文學史》,范勁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頁,第132頁,第16頁,第12頁,第53頁。
③[德]顧彬《解讀古代中國的“憂郁感”》[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第19卷
⑦黃修已《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頁
⑧樂黛云《關于“異”的研究·序》[A],[德]顧彬《關于“異”的研究》[M],曹衛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
⑨羅振亞《“世界性”眼光與中國現當代文學評價問題——評顧彬〈20世紀中國文學史〉》[J],《中國文學批評》,2017年1期
⑩張霖《作為思想史的文學史——評顧彬〈20世紀中國文學史〉》[J],《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 2期。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