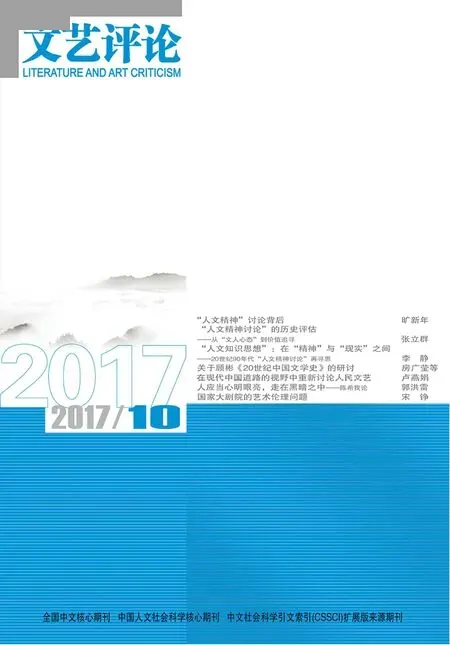媒體與文學批評新秩序
——以“顧彬事件”為例
○趙 潔
媒體與文學批評新秩序
——以“顧彬事件”為例
○趙 潔
2006年底,《重慶晨報》上一篇名為《德國漢學教授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新聞稿在中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這篇新聞稿中的“德國漢學家”就是“對中國文學情有獨鐘”的顧彬。此稿件雖然被證實為夸大其詞,然而顧彬之后又在媒體上接二連三地對中國當代文學發表尖銳批判,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激烈討論,并掀起了文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重估”熱潮,形成了所謂的“顧彬事件”。
十余年過去了,對顧彬的文學觀和文學著作的研究一直持續不斷,而對這一文化事件的挖掘卻極少。一個言過其實的“標題黨”竟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討論,梳理事件會發現,它其實清晰呈現出了新世紀民族的矛盾心理和全球化浪潮下的身份焦慮,以及為緩解焦慮對重建文學秩序的渴求。在文學價值標準混亂之時,媒體作為不速之客,介入并重建了文學批評秩序,并同時建構批評主體和受眾,新秩序的文化霸權成為媒體和批評主體的合謀。
一、“顧彬事件”的社會文化語境
將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分別比喻為五糧液和二鍋頭,或“中國作家是包子”,這些都是顧彬在中國媒體上的發言。然而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外國人的否定能引起中國文學、文化界如此激烈的反應,有些讓人出乎意料。一時間市面上的大部分期刊報紙紛紛刊載相關討論。支持者們同意顧彬“垃圾論”,“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分析顧彬這些批評意見,難道不會認為他是切中了當代文學的要害問題嗎”①?韓浩月認同顧彬的批評方式同時,還要附和幾聲:“國內的文學批評不像胳肢就像撓癢,通常看著像文學批評,看完之后發現原來是文學按摩。”②而反對者們對顧彬的論斷與“垃圾論”的風格是一以貫之的,殘雪認為顧彬“蠢里蠢氣,根本就不懂文學”③,虹影對顧彬的評價是:“我見過顧彬一面,我沒怎么理他。我覺得他這個人傲慢無禮。”④張光芒在接受采訪時稱顧彬“是標準的傲慢和偏見在作祟”,“只有垃圾才武斷地說人家是垃圾,而且振振有詞”⑤。無論支持與否,這些回應都過于情緒化,更像是本能的反擊。
為何會出現如此火爆場景,則不得不回到當時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去。
上個世紀80年代,文化界因極力擺脫“文革”的影響,重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大量翻譯、引進西方的科學與社會科學著作,引起了一股“西方熱”。在主流話語重構中,“是參照西方中心重構中國在現代世界上的邊緣位置,并有力呼喚著一場朝向中心的偉大進軍”⑥。很多在這樣的熱潮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內心深處有著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西方標準”成了重要的價值衡量準則。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社會浮現意識形態危機與消費社會的拜金浪潮,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開始出現,并進而重新喚回了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1996年圖書《中國可以說不》⑦的熱銷正是最好的例證。這本書具有強烈的反美情緒,雖遭到部分學者的批判,但在青年人中極受歡迎,甚至形成了一股“說不”圖書熱潮。新世紀以后,西方中心主義所帶來的邊緣位置焦慮,和渴望身份認同的民族主義夾雜在一起,構成中國人矛盾復雜的文化心理。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底色的民族主義,意味著對他者的批評異常敏感,聞風而動奮起反擊,然而這種反擊是以他者的文化邏輯為依據的,注定是徒勞的。這種矛盾的文化心理在國人對顧彬言論的反應中清晰地體現了出來。
在這樣的焦慮下,文學秩序的重建成為亟待解決的命題。事實上,年輕的批評家們已經在嘗試。
世紀之交的文壇上,“酷評”一詞甚是流行,它是指不求學理、直率犀利、短小精悍的文藝批評,基本上均為否定性批判,犀利、刻薄,甚至謾罵是其主要的特點。1999年葛紅兵發表《為20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全面否定“五四”之后的作家、作品,王朔發表《我看金庸》一文,對金庸作品進行了嚴厲批判。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同年出版了一本“對當下中國文學的一次暴動和顛覆,把獲取了不正當名聲的經典作家拉下神壇”的《十作家批判書》,對錢鐘書、余秋雨、北島等名作家進行了顛覆性討伐。其后,《十詩人批判書》《五作家批判書》《十美女作家批判書》等相應出版,一時間文學界刀光劍影、硝煙彌漫。
這種以反叛姿態出現的文學批評新形式,其背后是深層的身份焦慮與對新的價值標準的渴求。他們希望通過“大破大立”的方式重新探尋世界與中國文學新秩序的可能,表面是否定的中國文學,實際是否定的長久盤踞文學批評界的西方評價標準。同時我們也可看出,早在顧彬發出驚世之言之前,文學界內部已然已經開始自省,因此對顧彬的不容忍,大有一種“兄弟鬩于墻,外御其辱”的陣勢。
緩解民族身份焦慮的有效辦法是寄希望于新的文學價值標準和文學批評秩序,這個秩序不是依照十七年的政治標準,也不是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標準,而是能肯定民族文學價值的全新的標準。而就在作為文學批評主體的批評家們試圖重構文學秩序時,不速之客到來,媒體揭開了新秩序的序幕。
二、媒體與文學批評秩序重構
新世紀的社會文化環境較之之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來自于媒體的影響。現在回望新世紀初,甚至可以斷言,21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文化是媒體主導的文化。傳統媒體告別了“傳聲筒”的單一定位,與官方的距離逐漸拉遠;互聯網帶來新媒體的發展,更快捷的信息和互動性更強的傳播機制,使得媒體使用已成為很多人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體驗。媒體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向廣大受眾施展著它的無限影響,媒體被稱作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媒體的影響自然也伸到了文學領域,尤其是文學批評。在某種程度上,前文提到的新世紀的身份焦慮恰為媒體建構文學新秩序、搶占話語權提供了好的契機。“顧彬事件”中媒體的參與即是最好的例證。
2006年11月27日,“德國之聲”中文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德國漢學權威另一只眼看現當代中國文學》的采訪稿。在這篇文章中,記者問顧彬對中國最近出版的“美女作家”的作品如何看待,顧彬的回答是:“開玩笑。這不是文學,是垃圾。”從采訪稿看,顧彬的“垃圾”話語只是針對20世紀90年代的身體寫作,并未指向中國當代文學的全部。這篇文章最開始發表后,只有少數媒體轉載,無甚影響。真正引起強烈關注的,是2006年12月11日《重慶晨報》記者摘錄了這篇采訪稿,并將其命名為《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篇文章是這樣開頭的:“日前,在國際漢學界有著一定知名度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接受訪問時,突然以‘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等驚人之語,炮轟中國文學。”看似言之鑿鑿的話語,卻在原采訪稿中找不到依據,《重慶晨報》的這篇文章無論是題目還是內容,都在斷章取義、甚至是歪曲顧彬的原意。
《重慶晨報》的文章見報后不久,新華網、人民網、中國日報、新浪、網易等中國國內重要媒體未經核實就原文轉載。之后又衍生出多個文不對題的“震驚”標題:“我和中國作家無話可說”“德國漢學家:中國作家被稱嫖客”“顧彬:中國作家應該沉默20年”等等。一時間,對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討論甚囂塵上,成為文學界的熱點。
這是一場精心準備的媒體策劃,也是媒體建構文學批評秩序的有效嘗試。
一方面,媒體消解了傳統的文學批評,使得單一的精英批判轉化為眾聲喧嘩。傳統的文學批評發聲自權威專家學者之口,見諸專業文學刊物,是嚴肅的、權威的、斷定性的。而大眾媒體的出現,為更多的普通人提供了文學批評的平臺,批評主體由單一走向多元,批評場域由高雅的象牙塔走入大眾廣場,批評空間不斷擴展,批評角度新奇多變,讀者數量和需求也向多元化發展。傳統的精英批判不再,而解構的、娛樂的、符合大眾文化口味的批評風生水起。也就是說,大眾媒體對文學批評的影響不是平面、簡單的,而是立體的、全方位的顛覆與消解。因此在大眾傳媒時代,媒體反客為主,成為文學批評的主導性的力量,常常是媒體開啟某個話題的討論,專業批評家才緊隨其后,依據媒體設置的腳本展開或學理性或大眾化的文學批評。“媒體的編輯記者不時地客串批評的主角,左右著批評的輿論導向,媒體命題由批評家作文的情況比比皆是。”⑧在“顧彬事件”中,整個事件最初不過是來自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記者的違規操作——一個夸大其詞的標題,卻為傳統文學批評主體提供了言語的契機和理由,最終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文學標準論爭。
另一方面,在消解的同時媒體也在建構新的文學批評秩序。除上述所說的多元化的批評格局外,媒體也在用一些“專屬力量”制衡文學批評角力場,如文學“議程設置”“震驚效果”等。美國傳播學家麥克姆斯提出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即媒體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哪些事實和意見及他們談論的先后順序。在文學批評領域,媒體也在進行著“文學的議程設置”,正如前文所說,“媒體命題,批評家作文”,進而引發大眾的關注。
很明顯,“顧彬事件”即是媒體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所做的議程設置。《重慶晨報》的標題是有意為之,網絡媒體盛行的當下,這樣的新聞處理方式并不罕見,甚至已成為公認的爭奪注意力的有效范式。媒體出于自身的利益,為吸引眼球而故意使用似是而非的、驚異式的標題,將公眾視線引入事先設計好了的路線,這樣的方式被戲稱為“標題黨”,它并不符合新聞寫作規范,卻是無論傳播者還是受眾都心照不宣默認的“公理”。而在此范式中,“震驚效果”是終極要義。一條新聞只有提出不同常人的、驚世駭俗的言論,才能在茫茫的信息大海中脫穎而出,成為被關注的重點。“顧彬事件”也恰恰證實了這一點,同樣的訪談文本,平淡的標題下無人問津,歪曲原意的標題卻引起眾聲喧嘩。“震驚效果”可以吸引短時的社會關注,而其他媒體跟風的話題討論則能夠延長事件的熱度,形成歷時性的關注和討論,至此,媒體才算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文學議程設置。它從一個有“震驚效果”的標題開始,通過多次重復、補充、對話等信息一步步引導受眾的關注視線,最終構造出一個受人關注的事件,為受眾的議程表添加了極為重要的一項。
經過不斷的消解和重構,在新的文學批評秩序中,媒體處于領導統帥地位,擁有至高的話語霸權。
三、新秩序的話語霸權合謀
在福柯的話語理論中,話語的實踐是用符號界定事物、建構現實和創造世界的社會實踐活動,而其無所不在的建構力量即話語的權利所在。
新世紀以來,媒介就是通過文學議程設置、“震驚效果”、命名暴力等種種方法構建著由自己主導的文學批評霸權,它通過集中陳述設置社會的關注議程,引導批評主體和受眾的注意力,并通過命名、曲解等方式用符號建構“真實”,進而影響人們的認知。“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即是一種話語權力的施展:憑借大眾媒介的傳播優勢,定義、導演一個“事實”。這句話背后隱藏的是一個掌握世界唯一標準的西方對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否定,而這個否定借顧彬之口說出,這時顧彬怎么想已經不重要,他成為代表西方評價標準的符號,承載著國民的“西方想象”。
然而,如果認為媒介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僅在于話題選擇和輿論導向,那實在是太天真了。事實上媒介也在無時無刻不建構和異化批評主體的話語模式、批評策略,甚至是思維方式。媒體時代,批評主體對媒體話語霸權的應對本身陷入邏輯悖論——他們如果希望糾正話語霸權命名的錯誤標簽,就不得不通過媒體發聲,而話語一旦進入媒體傳播過程中,就再一次被符號化、標簽化。顧彬大概體驗過這種無奈,新聞出來沒幾天,顧彬再次接受采訪時就澄清過,說自己從未說過此話。而幾天后新聞出來,標題成為:“顧彬否認說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句話依然存在,加上“否認”二字彷佛又多了欲蓋彌彰之感,所以這條新聞雖然是在糾正之前的誤解,卻又在制造新的、更加曖昧的能指。
在這個沖不破的“網”中,批評主體如要對抗則無路可走,而合作則路路暢通,于是,文學批評的媒體化成為媒體與傳統批評主體的合謀。2006年顧彬被曲解后,或許是發現否認無效,在后來的媒體發聲中,他并沒有用詞更加謹慎,反而一再重申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否定,并用各種多意性的比喻,而絲毫不擔心媒體的曲解和讀者的誤解。他似乎是發現自己碰到了中國文化界的癢處,于是一撓再撓。批評主體在發表言論時,為媒體提供可抓住的“把柄”,從而在媒體制造轟動效果的過程中成為事件的主角,以求與媒體共分話語霸權,這是批評主體在媒體時代學到的新的批評策略,也是從被媒體建構到主動建構的過程。
不僅是顧彬,中國的批評家們對這種批評策略并不陌生。上文中提到的“酷評”即是此類,正如前文提到的批評主體反抗媒體話語霸權的悖論,“酷評”有著天生的矛盾之處,它一方面帶有打破“歌功頌德”式批評的獨立、自由之決心,另一方面又陷入嘩眾取寵、尖酸刻薄的窠臼,正如李建軍所說,“真正意義的批評意味著尖銳的話語沖突,意味著激烈的思想交鋒。這就決定了批評是一種必須承受敵意甚至傷害的沉重而艱難的事業”⑨。然而,聰明的學者發現了共謀的可能,如果“嘩眾取寵”是叛逆言論的必然附屬品,不如利用“嘩眾取寵”,使叛逆成為可能。劉心武在接受訪問時曾提到,“如今的酷評,百分之百來自民間,無論它怎么個酷,不影響我每月領工資,也不影響我投稿掙稿費(甚至因為有那酷評,本已邊緣化的我,還會被傳媒短暫地喚回到中心,甚至約稿反多起來),當然更引不出什么運動,什么斗爭”⑩。
正是如此,當顧彬的原意和“垃圾論”的真實內涵明確之后,學者依然自說自話,不愿糾正這種誤讀,依舊針對“中國當代文學到底是不是垃圾”進行爭論,這可以說是爭奪“顧彬事件”中媒體和顧彬分成的話語權。
于是在新的文學批評秩序中,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引導文學批評的走向,而文學家和批評家沿著媒體規定好的路線,被媒體利用的同時利用媒體,文學批評的話語霸權成為媒體和批評主體的合謀。
似乎媒體和批評主體處在合作共贏的狀態,然而事實是,大眾傳播中處在弱勢地位的受眾也在被影響著。媒體的話語重塑受眾的審美傾向和思維方式,充滿“震驚”的媒體話語一方面使得受眾思維走向極端化、簡單化,另一方面又使得媒體和權威批評主體喪失公信力,受眾的“看客心理”膨脹到極致——不管中國當代文學是不是垃圾,只要有熱鬧看就好——而這或許并不是新的批評秩序所希望看到的。
①肖鷹《顧彬不值得認真對待嗎?》[N],《文匯讀書周報》,2007年4月13日。
②韓浩月《當代文學缺乏自我批評精神》[N],《中國圖書商報》,2006年12月19日,A01版。
③④⑤彭曉蕓《漢學家集體批判中國作家》[J],《南都周刊》,2006年版,第 82頁。
⑥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⑦宋強《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后的時政與情感抉擇》[M],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
⑧陳俊濤《略論90年代文學批評的變化》[A],《世紀末的中國文壇》[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頁。
⑨李建軍《關于“酷評”》[J],《文學自由談》,2001 年,第4期。
⑩劉心武《酷評與暗算》[J],《文學自由談》,2004年第1期,第31-34頁。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