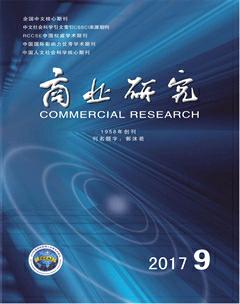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ISSP測度指標體系研究
王曙光 梁偉杰
內容提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國重要的發展戰略,但理論和實踐上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尚無統一的認識和標準。本文通過構建4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和46個三級指標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ISSP測度指標體系,以評價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水平及其發展差距,并對東北和中西部地區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
關鍵詞:區域經濟;區域差異;協調發展;測度指標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9-0103-07
收稿日期:2017-04-20
作者簡介:王曙光(1963-),男,山東青島人,哈爾濱商業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財稅理論與公共政策;梁偉杰(1991-),男,山西陽泉人,哈爾濱商業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事務與政策。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財稅政策創新與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4BJY003。
區域經濟最早源于1826年德國經濟學家杜能(Johonn Heinrick Von Thunen)在《孤立國對農業和國民經濟之關系》著作中提出了“區位”的概念后逐步形成[1]。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國外主要包括以拉格納·格納斯、羅森斯坦·羅丹等人為代表的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理論和以岡納·繆爾達爾、佛朗索瓦·佩魯、艾波特·赫希等人為代表的非均衡增長理論。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一詞由我國學界首創,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漸成研究熱點。其研究源于人們對區域間經濟發展差異的認識,差異源于區域間經濟發展速度的不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3》數據,按照可比價格計算,1991-2001年中部與東部的經濟差異與1980-1990年相比擴大了245個百分點,西部與東部的經濟差異擴大了101個百分點。
鄧小平同志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思路,確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兩個大局”,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區域經濟發展道路。目前,東部利用政策優勢與區位條件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東北等地區相比發展緩慢。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則成為我國決策層與理論界共同面對的問題。
一、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實踐與相關研究
自1995年起,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成為黨和國家重要的戰略任務之一,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1995年黨的十四大五中全會通過的《九五規劃》,把“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差異”作為之后十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針之一,并實施有利于緩解差距擴大趨勢的政策;1996年3月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九五綱要》專設“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一章,標志著區域發展戰略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階段的轉變。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2003年1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區域發展”的重要戰略,同年9月四中全會和2004年3月五中全會分別提出了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此后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進行了重要的闡述,體現了黨對我國經濟區域間協調發展的決心。2016年3月《國家十三五規劃》又明確提出: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為基礎,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創新區域發展政策,完善區域發展機制,促進區域協調、協同、共同發展,努力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從萬方數據庫統計看,1996年以區域經濟發展為關鍵詞或標題的論文為76篇,超過1985-1995年10年的總和,這是由于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導向的變化。1994年出版的《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被認為是我國較早提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研究成果[2]。此后,諸多專家學者們相繼研究了有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概念和對策等問題,但其界定和認識不盡相同。蔣清海(1995)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在各區域開放的條件下,各區域間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狀態和過程,且形成內在穩定的運行機制[3];胡延照(1996)認為,應著重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體系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4];馮玉廣和王華東(1996)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指區域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系統(即 PRED 系統)中諸要素和諧、合理、效益最優的發展[5];曲振濤等(2006)認為區域即地區,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按標準劃分的有限空間范圍[6];覃成林等(2011)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含義:描述區域間經濟關系的狀態或過程,區域間開放與相互聯系、發展上形成關聯互動,相關區域經濟都能持續或共同發展、經濟差異趨于縮小[7];劉志彪(2013)認為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突出表現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傾向[8];崔木花(2015)認為城鎮化與區域經濟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彼此制約[9];丁任重和陳姝興(2015)認為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存在政策理念碎片化、政策思路趨同化、政策執行孤立化等問題[10];田開友(2017)認為區域性限制競爭、公共產品有效供給不足及宏觀調控性缺失等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范[11]。
上述研究沒有界定“發展”等概念,似乎是心知肚明或不用釋義,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概念必須明確。本文在進一步辨析發展與增長、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等概念的基礎上,構建相關的測度指標體系,并對我國四大區域的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分析。
二、構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ISSP測度指標體系
(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概念的界定
一般而言,發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其內涵包括增長、可持續發展,而增長只是事物由少變多的過程;經濟一般是指社會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經濟發展是指除經濟增長造成的區域、時間內產品與服務的增加外,還包括了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收入分配的變化等,經濟發展的變化指優化;可持續發展與傳統發展不同,它是在滿足當代人發展需要的同時不損害后代人的發展條件,既包括數量的增長和結構的優化,又包括了發展的持續性。協調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是配合得當之意,配合作動詞指合作,合作的前提是兩個及兩個以上部分的參與,在本文中所指我國東中西北四大區域;得當指適宜的狀態,而適宜是指區域各自經濟較快發展的同時彼此間差距的縮小,故此協調是指我國四大區域的經濟發展通過區域間合作而達到相互適宜的狀態。endprint
綜上,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界定為:“區域間的經濟交往日趨密切、生產要素有序流動、收入分配科學合理、相互聯系良性互動、發展差距逐步縮小,以達到各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過程”[12]。這種發展包含一定時期內區域各自產品與服務數量的增加,以及各自區域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分配結構的優化,且不以犧牲后代人發展為代價,主要維度包括區域經濟穩定增長、區域經濟結構優化、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潛力四個方面。
(二)ISSP測度指標體系的設計
1.ISSP測度指標設計的總體框架。關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測度指標,我國沒有確定的標準,學界也沒有統一的認識,至今仍尚未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客觀的、普遍認同的測度指標體系。諸多專家學者傾向于評價原則的研究,缺少量化的測度指標體系或可操作的標準;或限于數據搜集的難度,所提出的評價指標通行度偏低;或提出的指標很難度量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更深刻的內涵。
故此,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本文界定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內涵,提出可量化的測度指標體系,包括經濟增長(Increase)、經濟結構(Structure)、公共服務(Service)和發展潛力(Potential)4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和46個三級指標。我們將其4個一級指標關鍵詞英文的第一個字母綜合稱為ISSP指標,并將三級指標確定為“以人均指標為主體、總量指標為輔助”,以保證測度的準確性與可比性。
2.ISSP構建測度指標體系的思路。在ISSP一級指標下,具體構建14個二級指標和46個三級指標,其基本思路為:
(1)經濟增長一級指標。根據宏觀經濟學的觀點,經濟協調發展應是又快又好,其中的“快”主要體現為經濟增長。而區域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消費和外貿“三駕馬車”拉動,故在經濟增長一級指標下設立相應的政府投資規模(包括人均財政支出數量、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等)、居民消費水平(包括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等)和外貿收支狀況(包括人均進出口額、人均順差額等)3個二級和6個三級指標。
(2)經濟結構指標。經濟協調發展中的“好”主要體現為經濟結構,而優化的經濟結構包括區域行業發展均衡、基礎設施良好及居民經濟情況富裕,故此作為經濟結構的3個二級指標,并設立10個三級指標。行業發展水平指標下,三大產業的GDP占比可反映一個區域產業發展的均衡程度,行業發展有無偏廢,通過GDP占比一目了然;在基礎設施建設指標下,主要選取反映一個地區的交通、郵政、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情況的指標;人均GDP、人均工資和私人汽車擁有量,則可直觀地反映居民的經濟狀況。
(3)公共服務指標。經濟協調發展除又快又好之意外,還包括區域公共服務水平,進而帶動文化、科技、教育、衛生、社保和就業等事業發展,因而將其設立為6項二級指標和18項三級指標。其中,在文化建設水平下選擇報刊、廣電、文藝和圖書館等指標進行測度,科技發展程度下則通過技術市場的成交額和有效專利數量兩個側面予以反映,教育發展情況下通過教育經費和高校數量來反映,基礎衛生水平下的3個指標則側重于居民醫療待遇,社會福利保險下選取最基礎的醫療、失業和工傷等數據,社會就業狀況下主要選取公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中就業水平及社會總體就業水平。
(4)發展潛力指標。一個區域自然資源儲量和環境保護情況決定其經濟發展潛力,故而將其設立為2項二級指標和12項三級指標。在自然資源儲量下確立為最主要的自然保護區、煤炭、石油、天然氣、鐵礦、森林、水和耕地等自然資源的儲量情況;在環境保護情況下主要選取廢氣、廢水、固體廢料等垃圾產量的負向指標和垃圾清運量的正向指標。
需要強調說明的是:在設計ISSP指標體系時,一些重要的指標如土地承載力等,由于數據搜集和處理的難度,或未能納入該體系中,或是三級指標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二級指標(如外貿指標、行業發展和文化建設指標等)的內涵,其主旨是構建一個相對完善、合理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也期待學界更深入的研究與指正。具體的ISSP指標體系見表1。
(三)ISSP測度指標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為衡量區域間發展的協調程度、消除數據間單位差異,本文標準化處理是以一個區域年數據為基準。其模型為:
Cij=qijMj
其中Cij為第i年j指標的標準化分值,qij為其他地區第i年j指標的原始數據,Mj基準地區的數據值。
本文采用多因素評價法構建綜合評價模型,其公式為:
Ui=∑CijAj
Ui為第i年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指標,Cij為第i年j指標的標準化分值,Aj為j指標的權數。Ui是區域數值的比較值,可較好地衡量所比較的區域之間的協調程度。
(四)ISSP測度指標體系的權重設計
為使指標權重更加客觀,本文通過因子分析法提取各項指標的主要成分,并根據各成分的累計方差貢獻度和指標在成分中的得分來確定權重。在運用因子分析時,運用最大方差法旋轉數據。設置最大迭代收斂的25次,在5次迭代后達到收斂。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三個主要成分,其方差占比見表2。
在成分提取的基礎之上,根據每個變量的在提取因子中的成分值的絕度值占該因子比重,得到了每個變量的權重。經計算,一級指標經濟增長權重為1234%、經濟結構為2257%、公共服務為3913%、發展潛力為2596%。需要說明:環保指標中設置污染指標在理論上應為負值,但為了保證權重之和為1及計算的客觀性,本文設為正值,即在加權計算之后、求和之前將人均廢氣、廢水、工業廢料指標作負化處理。ISSP測度指標體系各級指標的權重,詳見表1。
三、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測度與分析
(一)四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測度
按照上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ISSP測度指標體系,本文選取我國四大區域“十二五”的相關數據,在標準化和加權后進行評分加總,測度其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結果見表3;總體評分結果的折線統計圖如圖1。endprint
(二)四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測度結論
第一,四大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依次為東部、東北、西部和中部。從表2中可知,東部地區在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和公共服務方面均高于其他地區,但發展潛力最低。隨著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潛力,四大區域間的經濟差距將會逐步縮小。
第二,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下降趨勢。從表2看,東北地區的4個一級指標數據逐年下降,特別是經濟增長評分走低,即從2011年的326降為2015年的270。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和外貿雖沒有大的變動,但政府投資出現明顯的降幅,因而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需要尋找新的突破點。
第三,中部地區經濟不具備明顯的發展優勢。從圖1可以看出,中部地區的發展潛力最低,且沒有任何一項一級指標高于其他3個區域。這也表明中部地區缺乏經濟增長的核心競爭力,但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總體呈上升趨勢,與東部區域經濟差距也在逐步縮小。
第四,巨大的發展潛力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優勢。西部地區有豐富的資源,主要能源儲量是其他區域數倍,甚至水、煤炭資源的儲量是東部地區的數十倍。其經濟發展潛力從圖1看排名第二,從表2看其發展潛力是其他區域的數倍。因此,西部地區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環境構成了其獨特的發展優勢與潛力。
(三)我國西部地區11省區的測度分析
在四大區域評分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西部12省區經濟協調發展情況進行測度。由于西藏自治區的數據錯誤和空項較多,因此暫不包括對西藏的測度。其評分結果見表4;總體評分結果的折線統計圖如圖2。
對西部11省區經濟協調發展測度后,我們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同區域各省區經濟協調發展情況不盡相同。從圖2看,貴州、云南和廣西3省區發展趨勢平緩,但總體水平較差;陜西和青海2省區發展波動較大,但總體水平較高;而重慶市發展趨勢呈下降狀態,與其他10個省區的趨勢相逆。可見,即使同區域內不同省區的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甚至是不同的發展趨勢,也說明一個區域總體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和區域內所有省區的經濟協調發展水平之間存在差異性,不能以區域的總體繁榮代表內部所有地區的繁榮。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非均衡性特點,國家及其政府部門在制定政策時不能忽視地區間的差異,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應滿足差異化的要求。
圖2 西部11省區綜合評分的折線統計圖
第二,同區域不同省區可擔負不同的經濟發展任務。在西部發展較好的省區中,各自具有其獨特的優勢,如重慶市經濟發達、公共服務完善,青海省資源豐富、環境優美。在西部諸多省區中,不同區域發展稟賦及自身優勢條件可擔負該區域不同的發展任務。在不同的發展條件下,區域內分工和協同發展可有效地促進一個區域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因此,區域整體的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提高,要求區域內各省區應發揮自身的優勢條件,而非機械地制定同樣的發展目標與政策。
四、加快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策略
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應以區域間的協調發展為基礎,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兼顧經濟總量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過程。只有加快我國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實現精準扶貧、縮小各省級區域間的差距,才有可能實現我國區域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13]。但東北地區與中西部情況有所不同,故此應制定符合其適宜的策略。東北地區策略的核心是扭轉目前“斷崖式”經濟衰退的態勢,中西部則在于保持和提升發展速度。
(一)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策略
1改變以政府直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東北地區的衰退由政策失效引起,特別是以政府直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缺乏持續的動力和穩定的質效。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應重視優化經濟結構,以供給側改革代替政府投資拉動,走一條充分利用區位優勢、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以質量代替規模的經濟發展道路[14]。
因此,東北地區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優化投資結構,以導向型政策配合直接投資,以市場選擇代替行政命令,逐漸放寬政府行政審批范圍,發揮市場機制效應;適時對國家某些壟斷行業嘗試引入民間資本,以激發該行業活力;積極實施PPP等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新模式,鼓勵大眾創業創新,促進中小企業快速發展[15],以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2著力解決人口老齡化等突出性的人口問題。目前東北地區面臨諸如人口老齡化問題、出生率過低、人口凈流出大于凈流入特別是高層次人才外溢等突出性問題,這是造成東北區域經濟下滑的重要原因。內部需求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突出性人口問題的發生導致東北地區的內需嚴重不足,必須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
改善東北地區生存發展環境,如提升城鄉低保標準,解決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提供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在東北地區可率先實施全面開放二胎生育試點,并適度擴大生育保險基金規模;加大高素質人才培養和引進激勵政策力度,創造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的優越環境[16];加大財政支出中關于民生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力度,努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策略
1.做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工作。在經濟新常態的政策要求下,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增速下降,但這又是改善經濟結構的重要時機,因而中西部地區應抓住改革契機,組建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聯盟,加強區域間的開放、互動與協調,并完善各省級區域經濟體制,煥發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新的活力,以保持其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17]。
我國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以區別于需求側的經濟增長政策。中西部地區供給側改革應著力于供給上提升經濟發展的質效,結構性改革可持續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包括經濟、消費、產業、企業和分配等結構的優化,將穩增長、去產能、補短板、惠民生作為工作重中之重,加快縮小與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18]。
2.創新區域經濟分工協作方式。處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區域的分工與協作關系。傳統的協作關系的實質是發達地區的高端產業需要較不發達地區的低端產業支持。這種協作方式只會擴大區域間的不協調與經濟的兩極分化,目前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剪刀差就是這種分工方式的體現。endprint
因此,縮小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差距就必須改變傳統的分工協作方式,通過各種途徑去發展中西部地區的高端產業,從根本上提升其創造財富的能力,改變東部地區壟斷產品大部分價值的現狀。目前中西部勞動密集型產業仍是主要產業,面臨著產業升級轉型,故此應降低其比重,并提升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以促進中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
3.加大財稅激勵政策支持力度。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主因是其優越的區位優勢和國家“一部分人發展起來”的區域戰略發展政策,而如今到了“先富帶動后富”的戰略節點,中央政府在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時要賦予適宜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條件與政策,并從東部地區的發展成果中抽出一部分使“先富”的東部帶動需要“后富”的中西部地區。
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需要給予其財稅激勵政策支持,包括直接的財政投資、財政補貼和財政貼息,以及規范的稅收優惠政策等,以激發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力和財力。此外,還應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東部地區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彌補中西部地區的區位不足,增強其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參考文獻:
[1] 約翰 馮· 杜能. 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J].1986(95).
[2] 張敦富,覃成林. 中國區域經濟差異與協調發展[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1.
[3] 蔣清海.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若干理論問題[J].財經問題研究,1995(6):49-54.
[4] 胡延照. 論上海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J].上海環境科學,1996(4):1-3.
[5] 馮玉廣,王華東. 區域PREE系統協調發展的定量描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6(2):42-46.
[6] 曲振濤,周旭亮,王慶江.區域經濟協的界定及其差異性分析[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3-6.
[7] 覃成林,張華,毛超.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概念辨析、判斷標準與評價方法[J].經濟體制改革,2011 (4):34-38.
[8] 劉志彪. 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路徑與長效機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4-10.
[9] 崔木花. 中部六省城鎮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動態演化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5(8):71-75.
[10]丁任重,陳姝興.大區域協調:新時期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趨向分析——兼論區域經濟政策“碎片化”現象[J].經濟學動態,2015(5):4-10.
[11]田開友.區域經濟發展失范的經濟法規制研究[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37-42.
[12]王曙光,樊迪.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財稅機制研究[J].會計之友,2016(13):114-118.
[13]溫雪,趙曦. 中國西部地區收入差距的實證研究與政策調整[J].社會科學家,2015(9)66-70.
[14]付德申,孔令乾. 貿易開放、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J].商業研究,2016(8):25-32.
[15]王曙光,李金耀. 小微企業稅源培育的政策研究——以哈爾濱市為例[J].學習與探索,2016(10):119-122.
[16]侯力,于瀟. 東北地區突出性人口問題及其經濟社會影響[J].東北亞論壇,2015(5):118-126.
[17]方來.產業結構與區域經濟增長互動關系研究——基于我國四大經濟區域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102-110.
[18]黃小勇,陳運平,肖征山.區域經濟共生發展理論及實證研究——以中西部地區為例[J].江西社會科學,2015(12):38-42.
ISSP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ANG Shu-guang, LIANG Wei-jie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China)
Abstract: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ur country, however, there is no universal cognition standard on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set in theory or practice. An ISSP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ith 4 first grade indexes, 14 second grade indexes and 46 third grade indexes is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gap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dominant strategies on acceler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regional distinc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pth index
(責任編輯:李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