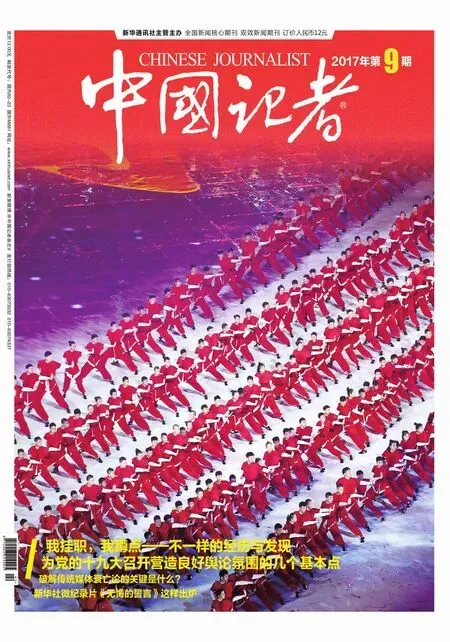“四個全面”和馬克思的“全面觀”
□ 文/徐人仲
“四個全面”和馬克思的“全面觀”
□ 文/徐人仲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戰略思想的重要內容,閃耀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光輝,飽含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的本質認識,堅不可摧,決不動搖。本文著力闡述“四個全面”與馬克思“全面觀”的關系。
四個全面 馬克思 全面觀
一、馬克思非常強調“全面”
馬克思曾說:“研究必須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表現出來。”[1]他說的“各種發展形式”,就是“全面”。包括“在顯微鏡下解剖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像對“勞動”這種“瑣事”,馬克思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分析。有縱向的,有橫向的,馬克思對“勞動”問題這樣“全面”的分析,就能深刻解剖“整個勞動”——這個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
對于“資本”,馬克思是非常“全面”解剖的。有總體的,有具體的,有肯定其歷史的巨大作用,有深入揭示它的各種特點……資本有:作為基本形式的產業資本,有特殊形式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有生產資本和流通資本——有流通形式的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有商品資本、貨幣資本、生息資本,以及貿易資本和商業資本,等等。另外,信用制度和虛擬資本——匯票,股票、債券、商業票據等形式也是資本的繁多形式的表現。當經濟危機到來時,虛擬資本就會大大減少,泡沫破滅了。
馬克思如此全面深刻分析了“資本”的各種表現,也就把它的“活的靈魂”如此準確生動地揭示出來。
馬克思說:“就像以掃(注:人名,即長子名)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一樣,工人也是出賣勞動的創造力,工人必然會變得貧窮,因為他的勞動創造力作為資本的力量,作為他人的權力而同他相對立,他把勞動作為生產財富的力量轉讓出去,而資本把勞動作為這種力量據為己有。”[2]這一論述是多么深刻啊!
對一件事或一個人,也應“全面”,只有“全面”,才能“準確”。
1853年12月馬克思寫了《帕麥斯頓勛爵》[3]一組八篇文章,揭露英國寡頭政治,深刻生動有趣,膾炙人口。馬克思除了曾到議會旁聽以外,還特別查閱了1808-1853年的帕麥斯頓《在下院講話》66冊,全面詳細了解那個人物的言行。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報》、英國《人民報》《格拉斯哥哨兵》《自由新聞》、紐約《改革報》等多家報刊登出,轟動了歐美。
“全面觀”,就是系統、完整。在“一切方面、各種形式”上求得“多樣性的統一”,在大局上講究“質和量”,從新高度上追求整體觀。它絕不是支離破碎、顧此失彼的。
二、用“全面觀”來加深認識“四個全面”
過去有段時間,我們不大強調“全面”,認為一談“全面”,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并以為這是不好的觀念。這樣,在認識上輕視“全面”,行動上缺少“全面”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在全國沒有形成“全面觀”的氛圍。
就拿改革來說,是取得了巨大成績,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由于沒有“全面”的要求,也造成諸多損失。比如,為了快富就到處簡易開發有色小礦,形成了土地嚴重染污,很不好治理,至今仍是一大問題。
剛改革時還可以說這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實踐,再不能以此來推脫責任,確實要以“四個全面”來嚴格要求。
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為我們在思想上、行動上更好地執行“全面觀”指出了方向。為堅持“全面”,反對“片面”,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全面深化改革”,內容非常廣泛。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法律、軍事以及外交等等。當然要由各個部門分頭實行,但是,各個部門也要協同起來。“全面”的內容要認真“細化”,并突出“創新”,在改革創新上取得新成果。要正確處理“全面”與“重點”的關系。
要加深認識“四個全面”,防止各種“變樣”的或“悄悄偷換”和“局部偷換”的做法。要用心去做,踏實地做,不能貪圖“省力”。
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項要求包含了許多內容,有貧困地區的自覺改變,有國家政策的落實,有原來比較富裕地區的幫助等等。這需要細分,怎樣做到“全面”扶貧?怎樣使貧困地區人民在改變生活貧困的同時,做到人口素質的大提高?現在有一種說法:只要黨提出了要求,沒有不能完成的。要警惕這種“放心”念頭背后的不努力、不盡心的情況。應該說,改革幾十年了,我國確實要“消滅”貧困了。
有人認為,“四個全面”是從“木桶理論”那里來的。這并不完全對。所謂一個木桶有一塊“短板”,那就不能“盛很多的水”,所以,要補短板。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我們提出的“四個全面”和“木桶理論”的“補短板”是不一樣的。
比如,“全面從嚴治黨”,這不是“短板理論”所能概括得了的。如果不從嚴治黨,就會使黨變質,而是和整個黨的生死存亡攸關的問題。所以,它不是一個“短板”,而是關系到“全局”。

新華社推出的“四個全面”說唱動漫MV。
其他三個“全面”,也有類似的情況。例如,如果我們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就永遠不能解決,那就不能再叫社會主義了。
“四個全面”實際上在“背后”有一個“全面教育”的問題,要加快、優質地全面發現和使用人才。
龔自珍曾寫過一首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詩是發表在1840年后,鴉片戰爭已經開始,戰爭如火如荼,到處是列強侵略的血腥,四野餓殍,煙館林立,中國人民處于深重災難之中。而全國卻“萬馬齊喑”,詩人悲痛地感到,“天公”,即“管控者”要根本改變“選人才”的策略。
這首詩的參考意義還在于,在新時期的人才戰略需要有更高的要求,要創造“全面”成長的勢態。宏觀、微觀、國內、國際的,而且一個人最能發揮作用的時間是很短的,大體是幾十年罷,而且一般先是要學習一段時間,然后可能“施展才華”,不久“趨于成熟”,到那時也就老了,要退出舞臺了。而共產黨人的要求是應該嚴格的、高標準的,一般的通常的作法已經不適合了,這要有“全面”的要求,即快、又扎實,有階梯地、有新思路地進行。要把“四個全面”化為對人才的要求,革新人才教育。
三、“四個全面”、馬克思的“全面觀”和新聞報道
用“四個全面”和馬克思的“全面觀”來要求我們的報道,這也有著豐富的內容。
僅以文風來說,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曾深刻地指出,新聞媒體改進文風依然任重道遠,不同程度上存在常說的老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好聽的虛話多,一些報道篇幅長,核心信息少,宏大敘事多,具體故事少,抽象表達多,形象表達少。奇葆同志講得很實在,很中肯。
為什么“常說的老話多”呢?這是對老話比較熟悉,不用費力,很容易落入這樣的老套。
為什么“嚴謹的套話多”呢?這是覺得引用一些報告、講話、法令的“用語”,來得“保險”,就盡是“嚴謹的套話”了。現在,“嚴謹的套話多”,是說有一批人在做講話、報告,發文件、指示以及寫重點文章時,確實是“嚴謹的”“認真的”,但同時要看到它的“反面”。
為什么“核心信息少,宏大敘事多”呢?這是對“核心信息”在頭腦中不是很清楚,也不知“核心信息”要到哪里去找,去采訪。而對怎么才算是“故事”,也并不清晰,虛有其表,只能用“宏大敘事”,來代替生動的故事了。
為什么“抽象表達多,形象表達少”呢?這主要是沒有深入到基層和群眾中去,沒有生動的故事,于是,只好“以次代好”地用“抽象”來表現實際生活中的動人事跡了。另外,在方法上也缺乏創新。
新聞媒體需要來自實際的事實、反映當代新的知識和與黨和人民的深厚感情,這三個方面的“結合”非常重要,沒有這種“結合”,并在采訪中很好地應用,那將寸步難行。
用“四個全面”的觀點來審視,選擇那些既符合“四個全面”,又“看得見,摸得著,動人心”并“看得準、拿得起”的具體事實,而不是所謂的“抽象表達”,然后加以有力的報道。這需要“強大的動力”,“四個全面”就是前進的“強大動力”。
“四個全面”、馬克思“全面觀”和新聞報道結合好,是媒體工作的“整體”,也是一項必備的“看家本領”。要思維敏捷,思考深刻,不怕艱苦,采訪深入,這就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怕挫折,努力去開辟新聞報道的新局面。
(作者曾任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
【注釋】
[1]馬克思.資本論[M]第一卷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第26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長子權”出典于圣經的故事:一天,雅各熬紅豆湯,其兄以掃打獵回來,累得昏了,求雅各給他湯喝.雅各說,須把你的長子名分讓給我.以掃就起了誓,出賣了自己的長子權.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2卷第397-478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帕麥斯頓子爵(1784-1865)英國國務活動家,初為托利黨人,1830年起為輝格黨領袖,曾任陸軍大臣/外交大臣、內務大臣和首相.
編 輯 文璐 wenlu@xinhu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