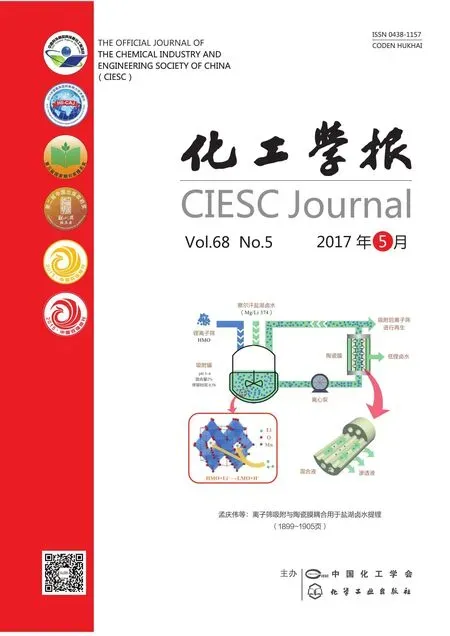雙層配碳燒結過程的傳熱傳質分析
張斌,周孑民,李茂
?
雙層配碳燒結過程的傳熱傳質分析
張斌,周孑民,李茂
(中南大學能源科學與工程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為了研究雙層配碳下的鐵礦石燒結過程及其節能效益,建立了鐵礦石燒結過程的二維非穩態數學模型。模型基于多孔介質理論,考慮了燒結過程中的主要物理變化和化學反應,以燒結杯為求解對象,利用FLUENT軟件及C語言自定義編程對燒結過程進行了數值模擬,并利用燒結杯實驗數據對模型進行了驗證。通過對常規均勻配碳和雙層非均勻配碳燒結的傳熱傳質過程進行仿真計算,分析了兩種燒結方式下床層溫度和物料熔化分數分布,并通過熔化分數對燒結礦成品率進行判定。研究結果表明:在不改變整個床層配碳量的條件下,相對于單層均勻配碳,雙層配碳條件下熱效率更高,床層溫度和物料熔化分數沿料層高度分布更加均勻;上下層物料配碳分別為5%和3.4%且料層厚度相同時,燒結成品率提高10%;降低上層高配碳區料層厚度,即當上下層厚度比為5:9,配碳為5%和3.756%時,成品率能夠進一步提高。
燒結;數值模擬;傳熱傳質;分層配碳;熔化分數;成品率
引 言
鐵礦石燒結是將粉狀鐵礦石、焦粉、熔劑和水分制粒并進行高溫加熱,在不完全熔化的條件下燒結成塊狀燒結礦的過程。隨著燒結技術的發展,利用料層自動蓄熱作用的低碳厚料層燒結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然而隨著料層厚度不斷增大,自動蓄熱作用更加明顯,導致沿著料層高度方向燒結溫度分布不均勻,上層燒結溫度偏低而下層偏高,最終導致燒結礦質量沿料層高度分布不均勻,產量降低,能耗增大[1]。為了克服熱量分配不合理問題,降低燒結過程能耗,提高燃料利用率,提出了雙層燒結法。雙層燒結法采用配碳不同的兩套布料系統,含碳量低的物料布在下部,含碳量高的物料布在上部[2-3]。一些學者對分層燒結工藝進行了研究:白晨光等[4]建立了一個燒結料層的蓄熱模型, 計算了高度為300 mm的料層均勻分為3層時各層蓄熱量比;黃柱成等[5]用實驗分析了3層配碳燒結,得出在不降低燒結礦產量的同時降低了固體燃耗;張小輝等[6]將600 mm料層分為3層并進行數值模擬研究,基于料層最高溫度控制對各層燃料使用量進行了優化;Nath等[7]應用遺傳算法分析了雙層配碳條件下燃料燃燒效率和燒結礦質量。然而對于多層配碳下燒結過程的傳熱傳質過程的研究仍較為缺乏。某些多層燒結過程的數學模型簡化較多,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化學過程。采用3套以上的原料制備和布料系統其工藝過于復雜,投資較高,不適用于實際生產。此外,對雙層配碳燒結工藝的理論研究仍然較缺乏,尤其是對雙層燒結的配碳量、料層高度等燒結工藝參數與熱質傳遞的耦合機制研究較少。
利用數值模擬方法有助于研究鐵礦石燒結過程中物理變化和化學反應的機理,控制燒結反應速率,開發燒結新工藝和技術[8]。一些學者建立了燒結過程的數學模型[9-13],并應用數值模擬方法對燒結過程進行研究,如Yang等[14]分析了燒結過程的燃燒特性;劉斌等[15]計算了燃料配比、風量和給料溫度等操作參數對燒結過程的影響;周昊等[16-17]研究了多孔介質內的燃燒及火焰的傳播;Masoud等[18]分析了燒結參數變化對燒結礦質量的影響;Ramos等[19]模擬了燒結過程中的結塊現象和燒結床層的結構變化;Castroa等[20]預測了燒結過程中PCDD和PCDF的排放。本文應用數值模擬方法對雙層配碳燒結過程進行分析。根據多孔介質理論,對燒結過程中的守恒方程和主要的物理變化和化學反應進行分析,針對燒結杯建立非穩態二維數學模型;對常規均勻配碳燒結和雙層非均勻配碳燒結過程的熱質傳遞進行仿真計算;研究床層溫度場與物料的熔化分數的耦合關系;對雙層配碳條件下不同的配碳料層厚度進行研究,以提高燒結礦的產量。
1 數學模型
1.1 模型假設
為了建立燒結過程的數學模型,需要做出合理的假設與簡化:(1)燒結床層被作為多孔介質處理,氣體和固體為兩種不同的連續介質;(2)模型中考慮的固相組分有焦粉C、石灰石CaCO3、赤鐵礦Fe2O3、磁鐵礦Fe3O4,氣相組分包括H2O、O2、CO、CO2;(3)所有物料顆粒均作為球體處理,且每種物料顆粒都有各自的初始直徑;(4)忽略床層的收縮對燒結過程的影響。
1.2 守恒方程
1.2.1 質量守恒方程 氣體和固體的質量變化主要是由化學反應中產生碳氧化物和水分蒸發冷凝導致。氣相質量守恒方程為

固相質量守恒方程為
(2)
式中,為孔隙率;g為氣體密度,kg·m-3;為時間,s;為氣體表觀速度,m·s-1;b為床層密度,kg·m-3;R為化學反應速率,kg·m-3·s-1。下角標從1到7分別代表水分遷移、焦粉燃燒、石灰石熱解、磁鐵礦氧化、赤鐵礦還原、CO與O2反應和CO與水蒸氣反應。一些數學模型通過簡化忽略了固相質量的變化,認為固相反應所產生的碳氧化物和水蒸氣對固相質量影響很小。而實際生產中,水分一般占物料總質量的6%~12%[21]。水分的蒸發冷凝導致床層密度變化較大,因此固相質量守恒方程不能被忽略。
1.2.2 能量守恒方程 燒結床層為顆粒填充床,基于多孔介質理論,床層內主要的換熱反應為氣相和固相間的對流換熱[22-23],因此需要對氣相和固相分別建立能量方程。氣相能量方程為

固相能量守恒方程為
(4)
式中,cg、s分別為氣相和固相比熱容,J·kg-1·K-1;g、s分別為氣、固相溫度,K;g、s分別為氣相和有效固相熱導率,J·m-1·K-1·s-1;v為體積對流傳熱系數,J·K-1·s-1·m-3;ΔH為化學反應熱,J·kg-1;m為熔化(凝固)熱量,J·s-1。能量方程等式左邊分別為非穩態項和對流項,固相能量守恒方程沒有對流項。等式右邊第1項為擴散項,第2項為對流換熱項,第3項為水分蒸發(冷凝)熱量,固相能量守恒方程第4項為熔化(凝固)熱量,最后1項為化學反應熱量。
氣體在床層孔隙中相對運動的速度差和溫度差導致氣固相間的對流換熱,氣相中損失(得到)的熱量等于固相中得到(損失)的熱量;固相中水分蒸發導致蒸發熱量由固相遷移到氣相中,水蒸氣冷凝則導致熱量從氣相遷移到固相中。因此,氣、固相能量方程中對流換熱熱量和水分蒸發熱量數值相等,符號相反。熔化(凝固)僅發生在固相中,熔化(凝固)熱只作用在固相反應源項中。能量方程中最后一項為化學反應熱量。將氣、固相中的化學反應熱分別歸類到氣、固相能量方程源項中,表明反應熱完全釋放到氣、固相中,而氣、固相間主要通過對流實現熱量交換。
一些文獻中省略了氣相或固相能量方程中的水分蒸發熱量,而蒸發水分所需要的熱量占到燒結總熱量的25%左右[21],省略該項會導致計算出現偏差。一些模型中認為所有化學反應熱量一部分釋放在固相中,另外一部分釋放在氣相中,不同的化學反應其熱量分配系數需要根據經驗來人為調整,以確定模擬結果與實驗數據匹配,該方法物理意義不夠明確。
1.2.3 動量守恒方程 燒結床層內的流動需要求解不可壓縮Navier-Stokes方程

其中f為作用于單位體積流體的反方向阻力,根據Ergun方程
(6)
式(6)右邊第1項表示黏性阻力損失,第2項表示慣性阻力損失。為壓力,Pa;p為顆粒直徑,m;為床層深度,m。
1.3 子模型
子模型是為了求解守恒方程中源項的反應熱及化學反應速率,分別包括對流換熱模型、水分遷移模型、熔化和凝固模型、固相和氣相中化學反應模型。
1.3.1 傳熱系數 燒結床層中的主要換熱方式為對流換熱,體積對流傳熱系數關系式可由Achenbach 準則關系式確定[24-25]
v=6(1-)/p(7)
式中,為面對流傳熱系數,J·K-1·s-1·m-2。

式中,為Nusselt數;為Prandtl數;為Reynolds數;g為氣體黏性系數,kg·m-1·s-1。
(9)

同時,考慮到導熱及輻射換熱,引入有效固體熱導率[26]
s,e=(1-)s+ 4p3s(11)
式中,s為固體熱導率,J·m-1·K-1·s-1;為Boltzmann常數,W·m-2·K-4;為發射率。
1.3.2 水分遷移 水分的蒸發和冷凝是在燒結初始階段進行,當水分被完全蒸干時,固相溫度開始升高,其他化學反應才開始進行。綜合其他文獻研究結果,本文采用兩階段水分干燥模型[27]。
1.3.3 熔化及凝固過程 燒結過程中顆粒溫度升高到熔點后發生不完全熔化,形成液相包裹住周圍顆粒,當溫度低于凝固溫度時形成燒結礦。熔化和凝固熱為

熔化分數為[19]
m=(s-m)/(max-m) (13)
熔化溫度m隨著原料成分而變化[7]
m=1380 + 21.22Al2O3+ 3.35SiO2-1.8flux(14)
式中,max為最高固相溫度,K;Al2O3、SiO2、flux分別為物料中氧化鋁、二氧化硅和熔劑的質量分數。
1.3.4 氣、固相中化學反應 燒結床層固相中化學反應包括焦粉燃燒、石灰石熱解、赤鐵礦的還原和磁鐵礦的氧化,反應所放出(吸收)的熱量全部作用在固相能量守恒方程源項中。氣相方程包括CO的氧化、CO和水蒸氣反應,反應熱量作用于氣相能量守恒方程源項中。化學反應速率如表1所示。

表1 氣固相化學反應速率
1.4 物性參數
燒結物料和空氣的比熱容、熱導率、黏性系數等物性參數隨著溫度而改變,在本文的模擬過程中考慮了物性參數隨溫度的變化,如表2所示。

表2 固相和氣相物性參數
此外,床層孔隙率隨粒徑的變化采用Castroa經驗公式[29]
= 0.403×(100p)0.14(15)
2 模型的求解
2.1 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
2.1.1 初始條件 燒結數學模型中參數的初始條件如表3所示。

表3 數值模擬及燒結杯實驗初始值
2.1.2 邊界條件 燒結杯入口為速度入口邊界條件。燒結杯出口為壓力出口邊界條件;點火階段,出口壓力為-6.3 kPa,點火完成后,出口壓力在-12 kPa;燒結杯側壁選用絕熱邊界條件。
2.2 數值求解方法
選取燒結杯截面并網格化,網格平均間距為2.5 mm,共生成18250個矩形網格。基于FLUENT軟件,采用有限體積法對質量、動量、能量守恒方程進行求解。氣、固相質量變化、化學反應引起的能量變化、流動過程的阻力項等均作為守恒方程的源項。使用C語言編程自行定義了質量、動量、能量守恒方程中非穩態項、對流項、擴散項和源項。模型方程中需要求解的參數如溫度g、s,濃度O2、CO2、H2O,密度H2O等定義為標量,建立并求解其輸運方程。方程的離散選擇二階隱式差分,速度壓力耦合選用SIMPLE算法,標量方程的收斂標準均設置為10-6,時間步長取0.5 s,以準確跟蹤物料溫度變化,同時保證較合理的計算經濟性。為促進收斂,連續性方程松弛因子取0.8,動量方程松弛因子取0.5。
3 實驗及驗證
3.1 燒結杯實驗
相對于燒結臺車,燒結杯的漏風率更小,測量的數據相對較為準確,且測量更加方便。本文利用燒結杯實驗來測量物料的溫度及出口煙氣溫度,以驗證所建立數學模型的正確性。圖1為燒結杯實驗及溫度測量裝置。
燒結杯高度為700 mm,直徑300 mm。兩個R型熱電偶橫向插入物料中,高度分別為=300 mm和=500 mm。同時,在燒結杯底部還設有煙氣溫度測量熱電偶。點火、保溫時間及溫度與數值模擬邊界條件一致,如表3所示。
3.2 模型驗證
圖2顯示了在=300 mm和=500 mm處燒結杯熱電偶測試溫度與數值模擬計算所得出的氣相、固相溫度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300 mm處測試溫度曲線位于計算固相溫度與氣相溫度曲線之間。由于燒結床層由顆粒堆積構成,熱電偶測溫點并非與固體物料緊密接觸。隨著固相顆粒部分熔化,局部形成液相,床層結構發生變化,熱電偶測點較容易暴露在床層空隙中。因此,熱電偶所測量的溫度并非固相溫度,而是介于固相與氣相之間的溫度[30]。在升溫階段,由于床層結構和物料顆粒變形較小,實驗曲線與計算固相溫度曲線較為接近。而在降溫階段,由于燒結礦冷凝收縮導致孔隙率變化較大,此時實驗曲線介于計算固相和氣相溫度之間。
在=500 mm高度氣固相溫度計算值相對實測溫度較為提前。實測溫度曲線的延遲主要是由于燒結物料發生收縮,且越靠近燒結終點,物料的收縮幅度越大。燒結杯測試曲線在燒結過程后期相對計算曲線延遲這一現象也出現在其他的文獻中,通過平移計算曲線,計算值與實驗值較吻合。
圖3為出口煙氣溫度的實測值與計算值的比較。從圖中可以看出,計算值與實測值接近,變化趨勢相同。初始階段煙氣溫度沒有變化,實測溫度略高于計算值,當煙氣溫度到達最高點開始下降時,實測煙氣溫度略低于計算值。計算值與實測值不同的原因是在數值模擬中沒有考慮燒結杯邊緣效應和物料的收縮,由此導致空氣不經過物料直接進入燒結杯底部;在燒結接近終點時床層收縮較大,漏風量增大,由此導致實測溫度與真實煙氣溫度出現偏差。
對燒結杯截面進行網格化,并對不同網格數下的計算區域進行模擬計算。圖4顯示了當網格數為9125、18250和27375個時在燒結杯高度為300 mm時的固相溫度。從圖中可以看出,當網格數量為9125個時,對應的計算固相溫度與網格數為18250個時的不同。而網格數量為18250和27375個時,得到的計算結果差別很小。因此可以得出,將計算區域網格劃分為18250個時,網格獨立。
對不同時刻的測試出口煙氣溫度與計算值進行對比分析,如表4所示。從表4中可以看出,在計算仿真結果與實驗值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誤差,但相對誤差在5%以內。當燒結時間為20.5 min時,實測煙氣溫度為724 K,計算值為749 K,此時兩者之間的誤差最大,達到25 K,但相對誤差僅為3.5%。對比燒結杯實驗數據與計算數據,可以看出數值模擬結果與實測值變化趨勢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認為本文所建立的燒結數學模型是可靠的。

表4 測試出口煙氣溫度與計算值對比
4 分析和討論
4.1 模擬結果分析
很多研究表明,床層溫度曲線對燒結礦質量有很大的影響[31]。使用實驗方法測量床層溫度曲線不僅成本較高而且操作復雜,而應用所建立的數學模型對燒結過程進行模擬,可以得到與測量數據基本一致的不同時刻和不同位置的氣、固相溫度分布。對溫度曲線進行進一步分析,有利于預測燒結效率和燒結礦質量。
圖5顯示了計算固相溫度曲線和出口煙氣溫度曲線。根據出口煙氣溫度曲線可以預測燒結終點,即出口煙氣溫度最高點,從而得到燒結時間為20.85 min。固相溫度曲線的峰值即為最高燒結溫度(peak temperature),計算得到在=300 mm和=500 mm料層的最高燒結溫度分別為1491 K和1562 K。根據物料組成的質量分數按照式(14)可以計算出物料的熔化溫度,即m=1411 K的水平虛線。當固相溫度高于熔化溫度時,顆粒開始熔化并生成熔體,對應的時間段即為熔化停留時間(residence time),計算得出在=300 mm和=500 mm料層的熔化停留時間分別為2.84 min和4.22 min。此外,某一時刻固相溫度曲線和熔化溫度m的差值與物料比熱容的乘積為單位時間內所傳遞給燒結混合料的熱量(J·kg-1·s-1),即
mgh=(s-m)c,s(16)
而在整個熔化停留時間段內固相溫度曲線和熔化溫度線所構成區域的面積(如圖5中陰影區域)與物料比熱容的乘積即在熔體生成階段所得到的熱量,簡稱熔體生成熱(melt formation heat)

溫度曲線和燒結停留時間決定了熔體生成熱的大小。熔體生成熱越大,表明傳遞給混合料并用于生成熔體的有效熱量越多。根據溫度曲線可以計算得出在=300 mm和=500 mm高度下物料的熔體生成熱分別為10439和27794 kJ·kg-1。
常規均勻燒結下燃料在物料中均勻分布,冷空氣經過燃燒帶后被加熱進入下層物料,相對于上層物料,下層物料通過對流換熱得到的熱量更多,導致焦粉燃燒更加充分,溫度水平更高;此外,下層較高的氣固相溫度也不利于物料的冷卻,導致了燃燒帶變寬。因此隨著燃燒帶從上向下移動,溫度水平逐漸升高,熔化停留時間更長,熔體生成熱更多。固相溫度水平決定了物料的熔化程度,通過模擬計算得到了燒結杯中物料的熔化分數分布,如圖6所示。
圖6顯示了在燒結終點時燒結杯內的熔化分數分布以及平均熔化分數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熔化分數沿著床層高度方向逐漸增加,最大熔化分數出現在靠近燒結杯底部區域,此時熔化分數達到0.44。由于下部床層熔體生成熱更大,物料得到的用于生成熔體的熱量更多,因此熔化更加充分,熔化分數更大。熔化分數曲線從床層頂部開始逐漸升高,然后突然降低,在燒結杯上部=80 mm處熔化分數達到極小值0.185,隨后又逐漸升高。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點火結束后冷空氣突然進入床層,造成床層溫度急劇降低,導致上層物料熔化分數降低,此后隨著燒結過程的進行,物料溫度提高,熔化分數逐漸增大。在床層底部為鋪底料層,物料沒有發生熔化。
熔化分數反映了燒結過程生成的液相熔體份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燒結礦的強度(TI)、還原性(RI)、還原粉化率(RDI)等質量指標。上層物料由于獲得的熱量不足,溫度水平低,混合料中部分礦物在熔融物中的熔解過程沒有充分發生,導致在這個區域中生成的結塊物少,成品燒結礦中返礦率升高。而下層物料熔化熱量多,熔化分數大,但熱量過剩會導致燒結礦過熔,成品還原性下降,使燒結礦質量指標下降。
很多學者提出了關于燒結礦質量指標的評判標準。Zhou等[13]、Loo等[31]提出包裹面積(enclosed area)的概念,即熔化停留時間內固相溫度曲線所包裹區域的面積,并分析了與燒結礦強度與產量的關系。Cheng等[32]將此參數定義為熔體量指數(MQI),通過燒結杯實驗分析得出MQI越大產量越高。然而實驗使用的燒結杯高度為400 mm,而大多數燒結機的高度都超過600 mm,甚至達到1000 mm。床層高度越高,底部物料的過熔現象越明顯,雖然生成的熔體量更多,但燒結礦質量下降。
燒結是顆粒在床層實現部分熔化最終形成具有一定強度和冶金性能的燒結礦的過程,熔化分數在很大程度了決定了燒結礦質量,對于評價燒結礦質量是一個重要參數[18]。Nath等[7]提出,當物料的熔化分數在0.3左右時,燒結礦質量達到最好。本文假設當熔化分數低于0.2時生成的燒結礦返礦率過高;而當熔化分數高于0.4時生成的燒結礦還原性過低,均為質量不合格燒結礦;當熔化分數介于0.2~0.4之間時為質量合格的燒結礦。
圖7為熔化分數m<0.2,介于0.2~0.4之間和>0.4時物料在床層中的分布。熔化分數小于0.2的物料主要分布在燒結杯頂部和底部鋪底料層;熔化分數大于0.4的物料分布在床層底部;質量合格的燒結礦(熔化分數在0.2~0.4之間)位于床層中部。通過所提出的判斷標準,質量合格的燒結礦在床層中所占份額即為成品率,因此可以計算得出成品率為61.96%。根據燒結杯實驗,得出所生產的燒結礦成品率為63.51%。按照所提出的假設對床層成品率進行預測判斷,所得結果與實際吻合,證明了假設的合理性。
4.2 雙層配碳條件下的燒結分析
雙層配碳燒結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手段,本文以高度700 mm燒結杯為計算區域,上層配碳為5%,下層配碳3.4%,上下層高度均為350 mm,保持物料中總焦粉含量為4.2%,即與均勻配碳燒結時含量保持一致。以均勻配碳為算例0,雙層配碳為算例1,分別計算研究相應工況下的燒結傳熱傳質過程及其特征,兩種燒結方式的配碳量及料層高度如表5所示。

表5 數值模擬計算算例0、1
圖8顯示了均勻配碳和雙層配碳條件下的氣固相溫度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雙層配碳時在=300 mm處,固相溫度高于均勻配碳時的燒結溫度;在床層下部=500 mm處,兩種燒結方式的固相溫度較為接近。雙層配碳燒結時上層配碳量高,焦粉燃燒釋放熱量較多,因此上部床層的溫度水平高于均勻配碳時的固相溫度;盡管下部床層含碳量較低,冷空氣經過床層上層后被預熱到更高溫度,進入下層的高溫空氣提高了焦粉燃燒效率,導致下層物料溫度的提高。兩種配碳方式下燒結時間分別為20.85 min和21.92 min。由于床層溫度水平提高,物料的冷卻變慢,由此導致了燒結時間的延長。對兩種燒結方式的最高燒結溫度曲線、熔化停留時間和熔體生成熱如表6所示。

表6 兩種燒結方式溫度參數
從表6中看出均勻配碳時,上下層物料的最高燒結溫度溫差為71 K;雙層配碳下溫差為35 K,由此可見雙層配碳時床層內的溫度更加均勻。均勻配碳時上下層物料的熔化停留時間差為1.38 min,雙層配碳時為0.29 min,上下層物料的熔化時間接近。均勻配碳時上下層物料的熔體生成熱差值為17355 kJ·kg-1;雙層配碳時為4311 kJ·kg-1,上下層物料的熔體生成熱差距更小,表明上部床層得到的用于生成熔體的有效熱量增加,整個床層內物料的熔化程度相對更均勻,熱效率更高。
圖9顯示了雙層配碳時(工況1)床層內熔化分數的分布及熔化分數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雙層配碳時上層高配碳區物料的熔化分數沿著料層高度逐漸增加,在高配碳區底部熔化分數達到最大;下層低配碳區的熔化分數分布相對均勻。從單層配碳(圖6)和雙層配碳(圖9)的熔化分數曲線可見,兩種燒結方式下床層內熔化分數分布差別較大。兩種燒結方式下熔化分數的分析如表7所示。

表7 單層燒結和雙層燒結熔化分數分析
從表7中可以看出相對于均勻配碳燒結,雙層配碳時最大熔化分數提高了4.9%,床層內平均熔化分數比均勻配碳時提高了3.5%。由于雙層配碳條件下上下層物料的溫差更小,溫度分布更加均勻,熔體生成熱差距更小,床層內的熔化分數分布更加均勻。由于上層配碳量的增加提高了上層的熔體生成熱,未熔化物料比例從14.1%降低到7%;下層配碳量降低使得過熔物料比例從23.94%降低至21.44%;未熔化物料和過熔物料比例降低導致成品率提高了接近10%。盡管在上層高配碳區底部區域熔化分數大于0.4,物料出現了過熔,但在下層低配碳區域熔化分數介于0.2~0.4之間,整個床層內質量合格的燒結礦所占比例提高,未熔化物料和過熔物料相對減少,燒結成品率提高。由此可推斷出雙層配碳燒結時,當上下層不同配碳物料高度為1:1時,在不改變料層中總配碳量條件下可以提高燒結礦成品率。
4.3 不同配碳料層的高度分析
在雙層配碳燒結過程中,床層內仍然會出現物料燒不透和過熔區域,導致成品燒結礦中存在返礦以及部分燒結礦還原性下降,降低了成品率。由于上部床層配碳量較高,相對于均勻配碳燒結,隨著燃燒帶下移物料熔化分數急劇增大,在上層高配碳區底部熔化分數達到最大。因此,改變高配碳區的料層高度和含碳量可能減少物料的過熔程度,進一步提高成品率。
本文中對不同高度的高配碳區和配碳量進行了模擬計算,計算的工況中保持床層總配碳量4.2%不變。當高配碳區料層高度為250 mm,配碳量5%,低碳區料層高度為450 mm,配碳量3.756%,設為算例2;當高碳區料層高度為450 mm,配碳量5%,低碳區料層高度為250 mm,配碳量2.76%,設為算例3,如表8所示。

表8 數值模擬計算工況2、3
圖10顯示了工況2和工況3床層中熔化分數的分布。從圖中可以看出,最大熔化分數出現在上層高配碳區,即對于工況2最大熔化分數位于=250 mm處,對于工況3位于=450 mm處。圖11顯示了3種雙層配碳方式在床層內的熔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上層高碳區高度的增加,最大熔化分數逐漸增加,床層內平均熔化分數有增大的趨勢。由于上層物料配碳量高,單位面積內釋放熱量多,熔化分數沿著床層深度方向逐漸增大。而下層床層配碳量低,下層熔化分數分布較均勻。對3種配碳方式的分析如表9所示。

表9 雙層配碳燒結方式熔化分數分析
3種配碳方式下熔化分數低于0.2所占比例都為7%,且位于床層底部鋪底料層。相對于單層配碳,雙層配碳條件下上層物料的配碳量更高,焦粉燃燒產生熱量更多,因此在床層上部沒有熔化分數小于0.2的區域,從而避免了上層物料熔化不完全,減少了燒結礦中的返礦量。而隨著高配碳區厚度的增加,熔化分數超過0.4的物料所占比例劇烈增加,導致合格燒結礦所占比例逐漸減小。當高配碳區厚度為450 mm時(工況3),燒結礦成品率甚至低于單層配碳條件下的成品率。3種配碳方式下的燒結時間變化較小,料層高度的變化對燒結時間的影響較小。
通過對3種雙層配碳燒結方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在保持床層內總配碳量不變的條件下,當高配碳區與低配碳區料層高度比例為1:1時,相對于單層配碳條件下的成品率可以提高了10%;降低高配碳區的厚度,高配碳區與低配碳區料層高度比例為5:9時,相對于單層配碳其成品率可以提高22.5%;而提高高配碳區的厚度,高碳區與低碳區料層高度比例為9:5時,燒結成品率低于單層配碳條件下的成品率。因此,在實際生產條件下,使用雙層配碳燒結工藝時應控制上層高配碳區的厚度小于下層低配碳區床層厚度,以達到大幅提高燒結礦成品率的目的。如果上層物料厚度大于下層厚度,則可能造成床層中過熔物料比例增大,成品率大幅下降,甚至低于均勻配碳燒結。雙層配碳燒結相對于傳統燒結過程更加復雜,在今后的工作中將對不同料層的配碳比等參數對燒結效率、成品率等影響進行研究。
5 結 論
(1)通過研究鐵礦石燒結過程中傳熱傳質現象及化學反應,結合多孔介質理論,建立了燒結過程的二維數學模型。模型中考慮了主要的物理變化和化學反應,并使用燒結杯實測結果進行了驗證。
(2)通過分析均勻配碳燒結床層內溫度曲線,得到最高燒結溫度、熔化停留時間和熔體生成熱。燒結溫度決定了物料的熔化分數,而物料的熔化分數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燒結礦質量。基于熔化分數指標,可對燒結礦的成品率進行有效預測和評價。在均勻配碳條件下,上層熔化分數小導致返礦量升高;而下層熔化分數大,物料過熔,燒結礦還原性下降;熔化分數沿床層分布不均勻降低了成品率。
(3)在含碳量相同的條件下,采用雙層配碳方式時,燒結時間僅延長1 min左右;上下層物料燒結溫差減小,溫度更加均勻;物料熔化停留時間差距縮短,熔體生成熱差距同步減小,上部床層得到的用于生成熔體的有效熱量增加,熱效率提高,床層內熔化程度更均勻,成品率提高。
(4)雙層配碳條件下最大熔化分數位于上層高配碳區的底部,高配碳區的厚度對燒結礦質量影響較大。在整個床層配碳量與均勻配碳一致時,當上下層物料配碳分別為5%和3.4%且料層厚度相同,燒結成品率相對于均勻配碳提高了10%;降低上層高配碳區料層厚度,即當上下層物料配碳為5%和3.756%,厚度比為5:9時,成品率能夠進一步提高;而上下層物料配碳為5%和2.76%,厚度比為9:5時,成品率大幅下降,甚至低于均勻配碳燒結。
References
[1] 郜學. 中國燒結行業的發展現狀和趨勢分析[J]. 鋼鐵, 2008, 43(1): 88-91. GAO X.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rend analysis of sintering industry in China[J]. Iron and Steel, 2008, 43(1): 88-91.
[2] MASAAKI N, KANJI T, YOSHIYUKI M. Ironmaking technology for the last 100 years: deployment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from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how, and evolution to next-generation process[J]. ISIJ International, 2015, 55 (1): 7-35.
[3] 付菊英, 姜濤, 朱德慶. 燒結球團學[M]. 長沙: 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 1996. FU J Y, JIANG T, ZHU D Q. Sintering and Pelletizing[M].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1996.
[4] 白晨光, 謝皓, 邱貴寶, 等. 燒結料層中的蓄熱模型[J]. 重慶大學學報, 2008, 31(9): 1002-1007. BAI C G, XIE H, QIU G B,An accumulation hea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ron ore sintering[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2008, 31(9): 1002-1007.
[5] 黃柱成, 江源, 毛曉明, 等. 鐵礦燒結中燃料合理分布研究[J]. 中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6, 37(5): 884-890. HUANG Z C, JIANG Y, MAO X M,Fuel 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in iron ore sintering[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37(5): 884-890.
[6] 李法社, 張小輝, 張家元, 等. 基于料層最高溫度控制的鐵礦燒結燃料合理分布[J]. 中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5, 46(2): 386-393. LI F S, ZHANG X H, ZHANG J Y,Fuel 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control in iron ore sintering[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46(2): 386-393.
[7] NATH N K, MITRA K.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of two-layer sintering process for quality and fuel efficiency using genetic algorithm[J].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2005, 20(3): 335-349.
[8] 陳林根, 夏少軍, 謝志輝, 等. 鋼鐵冶金過程動態數學模型的研究進展[J]. 熱科學與技術, 2014, 13(2): 95-125. CHEN L G, XIA S J, XIE Z H,Progress in study on dynamic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iron and steel metallurgy processes[J].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13(2): 95-125.
[9] YOUNG R W. Dynamic mathematical model of sintering process[J]. Ironmaking and Steelmaking, 1977, 4(6): 321-324.
[10] CUMMING M J, THURLBY J A. Developments in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iron ore sintering[J]. Ironmaking and Steelmaking, 1990, 17(4): 245-248.
[11] YANG W, RYU C, CHOI S. Unsteady one-dimensional model for a bed combustion of solid fuels[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2004, 218(A8): 589-598.
[12] ZHOU H, ZHAO J P, LOO C E,Numerical modeling of the iron ore sintering process[J]. ISIJ International, 2012, 52(9): 1550-1558.
[13] ZHOU H, ZHAO J P, LOO C E,Model prediction of important bed and gas properties during iron ore sintering[J]. ISIJ International, 2012, 52(12): 2168-2176.
[14] YANG W, RYU C, CHOI S.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in an iron ore sintering bed-evaluation of fuel substitution[J]. Combustion and Flame, 2006, 145(3): 447-463.
[15] 劉斌, 馮妍卉, 姜澤毅, 等. 燒結床層的熱質分析[J]. 化工學報, 2012, 63(5): 1344-1353. LIU B, FENG Y H, JIANG Z Y,Heat and mass transfer in sintering process[J]. CIESC Journal, 2012, 63(5): 1344-1353.
[16] 凌忠錢, 周昊, 錢欣平, 等. 自由堆積多孔介質內預混燃燒火焰傳播[J]. 化工學報, 2008, 59(2): 456-460. LING Z Q, ZHOU H, QIAN X P,Propagation of premixed combustion wave of methane/air in packed bed[J].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China), 2008, 59(2): 456-460.
[17] ZHOU H, LIU Z H, CHENG M,Effect of flame-front speed on the pisolite-ore sintering process[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5, 75(22): 307-314.
[18] MASOUD P, MOHSEN D E, MASOUD P. The effects of kinetic parameters on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in a sintering bed[J]. Energy, 2014, 73 (6): 160-176.
[19] RAMOS M V, KASAI E, KANO J,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iron ore sintering directly describing the agglomeration phenomenon of granules in the packed bed[J]. ISIJ International, 2000, 40(5): 448-484.
[20] CASTROA J A, PEREIRAA J L, GUILHERMEA V S,Model predictions of PCDD and PCDF emissions on the iron ore sintering process based on alternative gaseous fuels[J].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2013, 2(4): 323-331.
[21] PATISSON F, BELLOT J P, ABLIZER D. Study of moisture transfer during the strand sintering process[J]. Metallurgical Transactions, 1990, 21B: 37-47.
[22] 李菊香, 涂善東. 考慮局部非熱平衡的流體層流橫掠多孔介質中恒熱流平板的傳熱分析[J]. 化工學報, 2010, 61(1): 448-451. LI J X, TU S D. Heat transfer of laminar flow over a plate embedded in porous medium with a constant heat flux under local non-equilibrium condition[J]. CIESC Journal, 2010, 61(1): 448-454.
[23] ALAZMI B, VAFAI K. Analysis of fluid flow and heat transfer interfacial conditions between a porous medium and a fluid lay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01, 44(9): 1735-1749.
[24] KIM S J, JANG S P. Effects of the Darcy number, the Prandtl number, and the Reynolds number on local thermal non-equilibriu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02, 45(19): 3885-3896.
[25] 李茂, 母玉同, 張家元, 等. 燒結環冷機分層布料的數值模擬與優化[J]. 中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3, 44(3): 1228-1234. LI M, MU Y T, ZHANG J Y,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inter cooler in multilayered burden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44(3): 1228-1234.
[26] THUNMAN H, LECKNER B. Ignition and propagation of a reaction front in cross-current bed combustion of wet biofuels[J]. Fuel, 2001, 80(4): 473-481
[27] PATISSON F, BELLOT J P, ABLIZER D,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iron ore sintering process[J]. Ironmaking and Steelmaking, 1991, 18(2): 89-95.
[28] 俞昌銘. 多孔材料傳熱傳質及其數值分析[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1: 16-31. YU C M. Numerical Analysis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for Porous Materials[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31.
[29] CASTRO J A, SASAKI Y, YAGI J. Three dimensional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iron ore sintering process based on multiphase theory[J]. Materials Research, 2012, 15(2): 848-858.
[30] ZHAO J P, LOO C E, DUKINO R D. Modeling fuel combustion in iron ore sintering[J]. Combustion and Flame, 2015, 162(4): 1019-1034.
[31] LOO C E, TAME N, PENNY G C. Effect of iron ore and sintering conditions on flame front properties[J]. ISIJ International, 2012, 52(6): 967-976.
[32] CHENG Z L, YANG J, ZHOU L,Sinter strength evaluation using process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iron ore sintering process[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6, 105(1): 894-904.
Analysis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in two-layer sintering process
ZHANG Bin, ZHOU Jiemin, LI Mao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Hunan, China)
In order to analyze two-layer sintering process and its energy-saving benefit, a two-dimensional unsteady mathematical model of iron ore sintering process, which considered major physical changes and chemical reactions was developed based on porous media theory. Employed with FLUENT software and C language programmingcustom code, the sintering process was simulated and a sinter pot test was used to validate the model. Both conventional sintering process and two-layer sintering process were simulated. Distribu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melt fraction in sintering bed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heat efficiency became higher, temperature and melt fraction distributed more evenly in two-layer sintering when coke rate was kept the same as in one-layer sintering. Besides, the yield increased 10% when coke rates were 5% in the upper layer and 3.4% in the lower layer while two layers had the same heights. Reducing the height of the upper layer the yield of the sintering could be further increased when the height ratio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ayer was 5:9 and coke rates were 5% and 3.756% respectively.
sinter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heat and mass transfer; multi-load coke in charge; melting fraction; yield
10.11949/j.issn.0438-1157.20161334
TF 046
A
0438—1157(2017)05—1811—12
李茂。
張斌(1983—),男,博士研究生。
湖南省科技創新項目(CX2013B065)。
2016-09-22收到初稿,2017-02-13收到修改稿。
2016-09-22.
LI Mao, limao89@163.com
supported bythe Hunan Provincial Innovation Foundation of China (CX2013B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