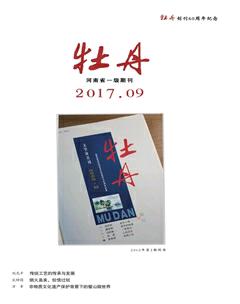北魏時期的士族階層及其寫經風格特征
劉淮
“寫經,是我國一種民間風俗……以佛教信仰崇拜為心理基礎,以寺院為集散中心的一種全社會的活動……表達自己對佛祖的虔誠和奉獻,對社會所盡的功德。”寫經,是一種社會文化活動,上自王公下至百姓都可以接受來自經文的加持與洗禮。1900年,敦煌道士王圓菉在帶人清理莫高窟積沙時,偶然發現了現在編號為388號窟中的藏經洞。1909年起,我國開展了敦煌藏經的研究,筆者就北魏士族寫經部分做簡要分析。自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鮮卑族逐漸漢化,門閥制度被沿用,加速了階級的分化。然而,在這個動亂的年代,書法蔚然成風。其中,離亂與苦難使人們對人生產生了出離心,強烈的求生凈土的愿念,使寫經活動空前繁榮起來,逐漸形成官方與民間兩個不同階層的寫經群體。本文就寫經這一宗教藝術產物,分析北魏時期士族階層寫經的風格特征。
一、北魏士族階層的寫經團隊組成部分
北魏由鮮卑族統治,宣武帝元恪篤信佛教。據《魏書·釋老志》載:“世宗(宣武帝)篤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在宣武帝的倡導下,佛教大為興盛:“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眾。”寫經團隊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寫經是中國書法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活動,目前重大數量的經卷集中出現于敦煌地區,其中北魏部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北魏控制敦煌地區有一個世紀之久(442-534),在這近百年時間中,產生并保存至今、有明確紀年的敦煌寫卷共有五十件左右。通過對這些重要文獻的研究分析,筆者發現北魏時期已經出現專門的寫經團隊:一是由王室貴族、文人士族、豪強、僧侶、官經生這些地主階層領導的官方寫經集團;二是來自民間的寒門經生、普通僧侶、傭書等貧民階層自發組成的比較零散的寫經群體。但無論身處何階層,信眾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積累功德——他們相信通過抄寫經論可以擺脫現世的困頓不安,從而往生極樂世界。
士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中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家族所構成的一個特殊階層。文人士大夫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引領時代的審美傾向。魏晉時期的士族階層書風更為盛行,如王羲之等社會名流、書法大家就寫過《妙法蓮花經》《佛遺教經》等不少經文。因此,由貴族、士人領導,組成一個龐大的官經生集團,如東陽王元榮就大力倡導、支持寫經活動;此外,也有被聘請專任寫經的“博士”“寫經師”“寫經生”等,如“典經師令狐崇哲”“官經生曹法壽”“經生張顯昌”等專門從事抄經的官方抄手,以及劉廣周、令狐禮太、張阿勝等人也常出現于相關文獻中。其中,作為寫經大戶的令狐氏在敦煌一帶本身就是士族大族。據敦煌考古文獻資料,人們可見令狐家族最早接觸佛教的記載:“北涼馬德惠石塔題記:令狐颯書。承陽二年歲在丙寅(426)次于鶉火十月五日,馬德惠于酒泉西城立,為父母報恩。”敦煌寫經活動中,官方都有一定分工:(官)經生、典經帥、校經道人等人各負責,而令狐禮太、令狐藝康、令狐永太等令狐家族成員占有據了絕對優勢。
二、北魏士族階層的寫經風格特征
北魏時期富有家學文化的士人書風,影響了整個時代的審美風尚。敦煌寫經則以令狐氏、張氏、曹氏等大族為首的寫經團隊占主流書風,體現了官方寫經的書法風格特征。
(一)妍逸工整,賞心悅目
翻譯、抄寫佛經,對于抄寫者來說,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經生在抄寫之前凈身凈心,沐手焚香,懷揣虔誠之心,秉持敬畏之心進行書寫,這是寫經活動與其他書法書寫活動不一致的地方。書寫,是心手合一的過程,張懷瓘在《書論》中云:“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也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盡于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因為對佛經的虔誠恭敬、因為對佛國的向往崇敬,北魏寫經要求很高,要求寫經者經不僅熟知一些佛學常識和佛教修養,還要接受嚴格訓練,格式統一規范、要求書寫既快又準,這就需要寫經者全神貫注、一絲不茍,從而達到精準無誤、毫無錯漏、工整細密的效果。士人寫經風格妍逸近媚,清代人王樹楠曾在寫經跋中指出:“北魏延昌二年寫經殘卷,出敦煌千佛洞,結體取姿有一種妍逸之致。”士族寫經字體工整,字的大小相差無幾,排列規整、行文流暢、點校精細、令人讀來賞心悅目。
(二)隸楷相間,平正寬博
北魏時期寫經活動盛行,形成了處于隸楷之間的正書體:波磔、重按之處較為明顯,使卷面顯得莊重,同時盡量保持寫經的虔誠、不摻入己意。可分為隸楷型和魏楷型兩種,行書、草書并不多見。這種書體是介于隸書和楷書之間的過渡形態,尚存隸書遺意,又見楷書筆法。它更符合寫經活動對實用性的要求,易于識讀,便于傳抄。縱觀北魏時期士族領導的書寫官方寫經經卷,隸書向楷書過渡形態比較突出,其特點是:隸楷型的寫經體結體平正寬博,取橫勢,氣象宏大;魏楷型的寫經體則抑左揚右、斜畫緊結,橫畫則左低右高,橫距比較緊密,中宮收緊,呈放射性結構,突出主筆,取疾勁之勢。寫經用筆比較迅疾,因此尖峰入紙,不再如隸書逆鋒起筆,而收筆處則重按,轉折處又頓駐后調鋒,取疾勁之勢,用筆極富變化。正如華人德先生評價北魏寫經書法:“寫橫劃都是尖鋒起筆,不用逆鋒,收筆處重按,轉折處多不是提筆轉換筆鋒,而是略作頓駐后再調鋒,以取勁疾。”例如令狐崇哲所寫《誠實論卷第八》,其整篇布局平整有序,疏朗有致,嫻熟老練,帶有較濃厚的隸書意味;結體呈縱勢,左低右高,筆跡流麗、灑脫,整體氣勢一貫,行文既嚴謹工細,又不乏生動活潑的韻律。而筆畫粗細分明,結體則為魏碑典型的“斜畫緊結”的特征。
(三)綿密穩健,行列整齊
北魏寫經從整體上來看,規范整齊,穩健沉著、行列整齊,而由于書寫速度迅疾,往往給人干凈利落、不拖泥帶水的審美體驗。因為寫生經與僧人、士大夫有著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在書寫佛經的過程中,不但形成了較為統一的寫經規范,同時也促進了寮用書法的發展,從隸至楷,間有行意,是北魏寫經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整個書體演變中,在平緩中力求變化發展,由原來隸味濃厚轉而向楷書靠近。寫經形式有著嚴格的規范,很多經卷上帶有界格,每列一般為17字,也有20字、甚至更多的,但較為少見。寫經卷中也可見“行意”,北魏東陽王元榮供養的經卷就表現出了行書意味,或筆筆相連,或筆斷意連,也加強了隸書的綿密感。北魏寫經間距疏朗、工整統一,利于識讀和傳抄,雖有界欄,不失行氣,通篇貫氣流暢。孫過庭《書譜》云“隸欲精而密”,綿密而整齊,正是北魏士族階層寫經的特點之一。
三、北魏寫經書法的后世影響
北魏時期的“隸楷型”和“魏楷型”的寫經書法對于東、西魏及唐代寫經都有一定的影響。東、西魏楷書在北魏寫經書法的基礎上逐漸成熟,體勢向縱長發展,筆法也增加了提按變化,楷書特征更為突出;至隋唐,楷書已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官方抄寫團隊也非常龐大,訓練有素,宋代朱長文在《墨池編》中說:“唐世寫經類可嘉,紹宗者猶屈為僧書,則寫經者亦多士人筆爾。”這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直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學界書法家再次掀起敦煌寫經熱,敦煌寫經成為書法學習的重要范本。始于宗教、終于審美,是敦煌寫經書法對后世發展的最大啟示。
(江蘇師范大學美術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