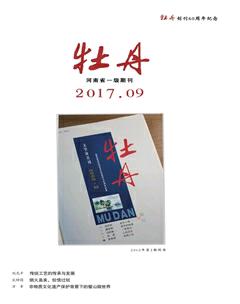杜夫海納論感性
項瀅
感性作為重要的美學范疇之一,在西方美學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被理解和闡釋,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種認識:一是認識論意義上與理性認識相對的感性認識。自古希臘哲學至近代英國經驗主義以來,有關感性的認識看似大相徑庭,實則異曲同工,即認為感性是人類認知的手段之一。二是生存論意義上的感性生存活動。黑格爾和馬克思通過引入“實踐”的概念,使得對感性問題的闡釋從感性認識轉向感性生存,這種以人的生存活動為基礎的理解賦予了感性更為豐富的社會實踐內涵。三是指感性對象,即訴諸人的感官的事物特征,如聲音高低或者色彩明暗等。
與上述三種認識不同,法國美學家杜夫海納以審美對象為載體重新定義了感性。在他看來,感性就是經由現象學還原之后,“在呈現中被給予和被感知的審美對象”。在杜夫海納的美學思想中,“感性”一詞有著極高的地位,這體現在他對感性的創造性闡釋中,而且這種闡釋貫穿了杜氏審美經驗理論的始終。為此,本文將從感性是什么、感性如何呈現等方面對杜夫海納筆下的這一概念進行論述。
一、什么是“感性”
審美對象就是感性。在杜夫海納看來,藝術作品只有自身被審美關照時才充分存在并成為審美對象,而感性就是人們面對作品時立刻感受到的呈現于眼前的那種東西,如果沒有感性或者感性退居次席,審美對象就不復存在。審美對象“既非實在又非非實在”,而是二者的結合。以歌劇為例,“實在”是演員載歌載舞的表演,是精心設置的舞臺布景,更是觀眾聚精會神形成的欣賞氛圍。這些都是演出的一部分,但它們不是審美對象,“不能把一切可以伴隨歌劇并為知覺歌劇創造良好氣氛的東西同歌劇本身混為一談”,一切被感知到的人或物的材料都在經過“中性化”之后才融入審美對象。“非實在”更是如此。劇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盡管使人感到緊張,但人們不會為此采取行動;綠色紙板制成的“森林”不足以帶給人身臨其境之感,卻因其鮮艷的顏色引起人的興趣。可以說,非實在的主題仍然是為作品服務的一種手段。實在與非實在都不是由于其自身而被把握,它們的共同點在于都為審美對象的出現服務,前者顯示作品,后者引出作品。由此可見,杜夫海納所說的感性是藝術作品呈現給人們的“完滿”。正如學者葉秀山曾經說過的:在杜夫海納美學思想中,審美對象的感性因素具有一種存在性的意義,“任何對象都有顏色,一般對象‘有顏色,而審美對象則就‘是顏色,譬如,變了顏色的衣服仍是衣服,但畫上的衣服卻與它的顏色不可分,所以在杜弗朗看來,藝術作品中的感性已不再是‘標記,而就是存在。長笛的聲音不是那種樂器的‘屬性,而就是那種聲音的‘存在,所以我們不說‘那個樂器在演奏,而是說‘長笛在演奏,也不說‘一個活人在跳舞,而是說‘生命在舞蹈。”
另外,感性之所以能完美地呈現于人們,是因為“在一切藝術中,感性都必須被整理和組合成使人們能毫不含糊地感知到它的程度”。首先,感性材料的呈現確定了藝術作品獨特的審美語言。如音樂是聲音的和諧、繪畫是色彩的搭配、詩歌是詞語的組合等。然而,材料又同產生材料的物質手段密不可分,畫布和顏料是產生色彩的物質手段,樂器是產生聲音的物質手段,能寫會讀的人是產生詞語的物質手段。對此,杜夫海納明確指出:在審美活動中,物質手段不再作為工具被感知,而是通過顯示自己豐富的感性來吸引人的注意。例如,石頭之于雕像是物質手段,但石頭的嚴峻、光滑、灰暗等特質使其作為構成審美對象的真正材料而存在。其次,內在于感性的意義賦予審美對象統一性。這里的意義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再現性意義。仍然以歌劇藝術為例,支撐全劇的臺詞、展開情節的舞臺動作和表示環境的場景布置互相配合向人們傳達“再現物”,即說明這是一部歌劇演出。其二是表現的意義。藝術作品具有更深一層的意義,臺詞的選擇、音樂的穿插和造型的設置都必須集合起來為這種表現的意義服務。因此,審美對象的感性絕非一種無組織、無意義的感性,而是按照嚴格的邏輯展開并述說自己的感性。它還同時通過它再現的東西和它述說自己時表示的東西向人說出其他東西。
二、“感性”如何呈現
杜夫海納曾說:“感性是感知者與感知物的共同行為”。根據這個論述,審美對象的出現需要具備兩個條件。
(一)作品要充分呈現,即作品需要得到表演
這里要區分兩種不同情況的表演:表演者不是作者的表演和表演者就是作者的表演。前者以戲劇、舞蹈等藝術為代表,作者創作出作品,而演員通過表演使作品中的思想得以傳達。后者以繪畫、雕塑等藝術為例,創作就是表演。對藝術家而言,作品存在于創作之前,也就是說,在藝術家動手創作以前,他已經感覺到一種“召喚”,即某種東西要求存在。杜夫海納把藝術家在創作前的沉思默想比作產婦的分娩,“力求固定和釋放的東西”就是要求存在的作品。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是使作品從非現實到現實過渡的工具。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不斷否定,不斷修改,直至聽到某種“呼喚”發出“就是這個”的聲音,他的作品才算完成。
無論是有專門表演者的表演,還是作者即表演者的表演,都是為了使作品從“要求”過渡為“要求的實現”,從抽象存在過渡到感性顯現,從而有助于審美對象的完滿呈現。
(二)欣賞者要積極參與,即作品要付諸審美知覺
有無審美知覺的參與是杜夫海納區分藝術作品和審美對象的唯一標準,他認為,“藝術作品的本質在于呈現,這種呈現是為了使我向它呈現,因此,知覺的地位不可替代”。表演在欣賞者面前進行,反之,欣賞者同表演者一起促成審美對象的“顯現”。
1.欣賞者協助表演
杜夫海納以戲劇和舞蹈為例指出,一方面,觀眾以聚精會神的目光回應著演員的表演,他們是審美對象得以展現的豐富的“生物學背景”;另一方面,欣賞者以“良好的精神狀態”領略作品。受審美對象的影響,欣賞者既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又要遏制激情。例如,人們在觀看電影時,看到劇中角色開車在狹窄的馬路上橫沖直撞時會感到緊張或者害怕,但絕對不會下意識躲避或者撥打120。審美對象的顯現參照這種主觀性并就主觀性而言才有意義。
2.欣賞者充當作品的“見證人”
作品期待通過欣賞者的“見證”來闡明自己,可以這樣說,公眾對一部作品的不同解釋并不是由主觀的差異性造成,而是作品的意義和密度在各個欣賞者那里出現的情況不同。“作品的同一性并沒有因此受到改變,因為它的內容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和折射到各個不同的意識中。更確切地說,所有這些看法僅僅展現或揭露了作品的可能性,把它內藏的資本兌成現金。”因此,欣賞者帶給作品的除了“見證”之外,別無他物。
三、結語
總之,在杜夫海納看來,感性不僅是審美對象的第一構成要素,還以豐富的內涵代表著整個審美對象。這里,受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思想影響,杜夫海納賦予了感性濃厚的生存意義。
(西北大學文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