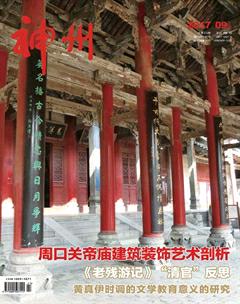隋唐時期敦煌壁畫舞蹈的形態(tài)特征與審美闡釋
王藝蓉
摘要:敦煌石窟藝術博大精深,氣魄宏偉。是集建筑、雕塑、壁畫三位一體的立體藝術寶窟,內容極為豐富。石窟壁畫藝術涵蓋了大量古代樂舞的內容,壁畫舞姿形象優(yōu)美,傳神。本文從敦煌石窟壁畫中,以隋唐時期的壁畫舞蹈為主,從人物線條、服飾、內容的變化反映出當時我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
關鍵詞:敦煌壁畫;形態(tài)特征;審美闡釋
古老的文化長河在中國的土地上蔓延了幾千年,當中經過了人們的不斷研究,發(fā)現(xiàn)了許多令人驚嘆的歷史文化,敦煌石窟壁畫藝術就是我國歷史遺跡中的瑰寶。
隋代建立時,由于統(tǒng)治階級推崇佛教,敦煌也是盛極一時,壁畫題材范圍變得更加廣泛。人物造型開始擺脫北朝清瘦的形象而顯得圓潤方正,端莊而風姿綽約。隋代時期的壁畫中以說法圖和本生故事圖為主,畫風從北朝時期的粗獷而日趨華麗,在壁畫的創(chuàng)作中大量出現(xiàn)凈土經變畫,結構宏偉,富麗非凡,如西方凈土變、東方藥師變、法華經變等。再者進入隋代后,飛天的形態(tài)主要為女性的造型,特點為眉清目秀身體修長,動態(tài)舒展輕柔,服飾、發(fā)髻明顯為宮娥仕女,飄帶流暢,多呈牙形旗狀。飛天數(shù)量也日增,除環(huán)窟四周繪制外,在窟頂藻井四周,及佛龕、背光左右也是飛天云集。畫面講究色塊的搭配,用色多為土紅、白色、藍色相間,形成了這一時期格外華麗生動的風格。隋代常見的佛傳故事畫“夜半逾城”,“乘象入胎”中的馬和象之四蹄卻是飛天托舉,在天空飛行,極富浪漫色彩,從整體藝術風格上來說從前期的畫面柔美向后期氣勢磅礴的轉變。
到了唐朝時期,中國古典舞蹈走向了發(fā)展高峰,這個高峰的形成首先是因為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域內外貿易發(fā)達,文化交流頻繁,為文學藝術的繁盛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南北朝各族舞蹈文化大交流,為唐代舞蹈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滋養(yǎng)。唐代恢宏博大的時代精神,海納百川的兼容氣度,急速旋轉的胡旋舞,筋骨柔軟騰躍輕捷的胡騰舞,反身下腰貼地的花舞,翔鸞飛鶴的霓裳羽衣舞在敦煌壁畫中都有生動的描繪。
莫高窟唐代初期的舞蹈人物形態(tài),克服了隋代比例不對稱的毛病,人物的造型比例更加的協(xié)調,更接近于現(xiàn)實,也特別注意刻劃舞者人物性格心理,自然佛和菩薩都不存在于現(xiàn)實生活中,但是古代匠師們在塑造佛和菩薩的形象時,線條流暢,菩薩的體態(tài)為一波三折的“S”形。畫師們在人物性格捏塑上,給予它們以人的思想感情,使觀者精神與之相通,激起其虔敬與親切之感。
中唐時期壁畫中的飛天十分盛行,這題材正好表現(xiàn)了當時繁榮昌盛,歌舞升平的景象。同時飛天創(chuàng)作也提倡發(fā)揮藝術家的想象力,施展才華。所以從初唐之后,飛天進入高潮。在藻井四周、龕楣背光處,說法圖上端,都會畫飛天,并成為固定程式。此時飛天已全部女性化,成為翩翩起舞的仙女形象。因此而成為宮廷貴族仕女寫照,臉型豐滿,姿態(tài)嫵媚,明目皓齒。衣飾、發(fā)髻雍容華貴,人體比例適當。上身均裸露,下為長裙,飄帶旋迥,衣紋流暢。這個時期的飛天樂伎聚增,所持樂器的品種亦多樣,而且極具演奏情態(tài)。
從晚唐進入五代,飛天創(chuàng)作意識日漸淡薄,多為因襲前朝之作。繪制水平下降,但仍然不乏富麗堂皇的場面。從動態(tài)和裝飾上看,已趨于平庸和衰落,人物造型已不是那么豐滿婀娜,轉為清瘦素雅,已無盛唐那種昂揚、激蕩之勢,略有呆板、沉重之感,程式化傾向已開始顯露.。
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看到,人物形體藝術已經完完全全的中國化,人物造型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審美標準,就是我們所謂的以胖為美,這其實在隋代的壁畫中已經初路端倪,所以我們也不能斷定是在唐代開始流行這種審美觀。
敦煌壁畫樂舞動作幾乎都有以一種共性特點,勾腳,出胯,扭腰。別致到頭頸多變的姿勢而形成韻味無窮的曲線美,每一個舞姿一般都是由一條或數(shù)條近似S形曲線所組成,例如在北涼第272窟頂四坡、北魏第257、254、431、435窟、西魏第249、288窟等,窟中都在四壁的上部畫出一排天宮伎樂,當中樂舞姿態(tài)都有很明顯的三道彎身形和異域樂舞的特點。從北涼到北魏、西魏至北周,一直延續(xù)至隋代。從隋唐到宋元飛天的各種飛天舞姿都能真切感受到三道彎“S”形美感效果。成為一種舞蹈的固定形態(tài),不斷延續(xù)和發(fā)展著以它特有的人體藝術形式。除了石窟壁畫上舞者本身的S型舞姿形態(tài)之外,在華麗而豪放的壁畫舞蹈場景中,還有舞者身上一種不可忽視的飾品——飄帶。①舞伎們的“S”形舞姿體態(tài)與翩翩飛舞的“S”形飄帶相互交叉,強調了整個“S”形曲線的功能。它挽在舞者的手中,雖然局限了舞者們的手型,卻放開了整個手臂,形成上肢動作的一種延伸。
莫高窟壁畫是世界各國博物館藏品所未見的。熾熱的色彩,飛動的線條,在這些西北的畫師對理想天國熱烈和動情的描繪里,我們似乎感受到了他們在大漠荒原上縱騎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許正是這種激情,才孕育出洞窟中那樣張揚的想象力量。
注釋:
①曹佳塢:《敦煌壁畫舞蹈“S”形肢體符號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第2頁
參考文獻:
[1]曹佳塢.敦煌壁畫舞蹈“S”形肢體符號研究[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
[2]段文杰.中國壁畫全集(敦煌 隋)[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1991.
[3]郭元平.壁畫藝術欣賞[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4]高金榮.敦煌舞蹈[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3.
[5]高金榮.敦煌石窟舞樂藝[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6]穆紀光.敦煌藝術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7]史葦湘.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8]易存國.敦煌藝術美學;已壁畫藝術為中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