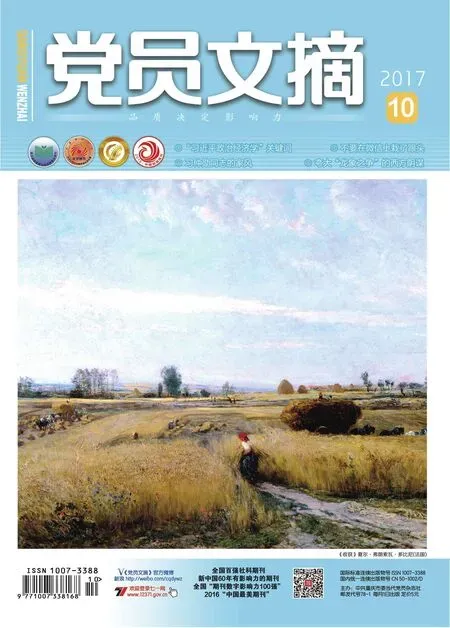“變壞”的老人與我們的時代癥候
□李少威
“變壞”的老人與我們的時代癥候
□李少威

大移民社會
被“街上有個人”看到和被“村里王大嬸”看到完全不是一回事。
對“問題老人”現象,有各種解釋,其中最為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話:“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
這句斷語的流傳,并非因為其內含的真理性,而是因為其形式上的簡單粗暴符合了群體思維特點。它一棍子掃倒一代人,邏輯上非常過癮。
當我們說“這一代老人”的時候,對象事實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現在公共場合的老人,他們已經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齡,而且體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國成立前后10年。
如果他們可以被統稱為“一代人”,那么這一代人人生歷程的最大特點是跨越了農業中國和工業中國兩個大時代。此外,由于中國的城市化率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從1977年不到20%到2016年的57.35%),所以其中大部分人還跨越了農村中國和城市中國兩個空間。
這意味著,如今的中國城市社會,是一個大移民社會。
從來路上看,城市里生活著四種人:第一種是世居的本地人,第二種是城市之間交換的人口,第三種是完成了農民進城這一過程的人,第四種是正在經歷這一過程的人。
后三種,毫無疑義屬于移民,而第一種(世居的本地人)由于城市急劇發展導致生活環境面目全非,以及后三種人的介入帶來的文化糅合,在與城市的關系上與移民已經差別不大。
道德是依靠輿論對越軌行為進行制約的,而在一個陌生人社會,輿論的力量大打折扣。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更是早已表明,一個人如果處在“匿名”狀態,自我約束意識就會削弱——這也是《禮記·中庸》提出“慎獨”的原因。
一個家庭里的正經人,在外面偶爾做一回混蛋,誰知道呢?這便是這個大移民社會里一個隱形的心理過程。在這一環境下人其實是抽象的,被“街上有個人”看到和被“村里王大嬸”看到完全不是一回事。
時代跨越和社會變遷
對于能夠適應技術變化的年輕人群而言,生活變得越來越簡單,而對于很多老人而言,則越來越艱難,環境正變得越來越不友好。
我們再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廣場舞在中國如此風靡?
那些大媽大爺們,原本大多是連站出來說幾句話都忸忸怩怩的傳統內斂的人,而現在他們早已不憚于乃至熱衷于在大庭廣眾之下展示“各美其美”的舞姿,他們真的是出于鍛煉的目的嗎?
深層的動機其實是,他們熟悉的社會瓦解了,瓦解發生之時他們已經過了富于可塑性的年齡,難以和新的現實建立情感聯系,而廣場舞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熟人社會的共同體體驗。
威爾斯在《新馬基雅維利》中描述鄉村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說:“這是一種猝然發生的進步,一種難以控制的變動,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
這在中國,也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這一代老人,就是跨越了“猝然發生”的變化,來到了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
不過,為什么“上一代”的老人就沒有出現“問題扎堆”的現象呢?比如,2006年“彭宇案”出現之前的老人,社會形象上還是切合傳統的,而他們同樣經歷了時代跨越和社會變遷。
答案在于,一方面他們更少地出現在公共場合(比如那時還沒有廣場舞),另一方面當時技術進步的速度遠遠不如今天快。
少參與,就少是非,這一點不用解釋。
技術進步不僅僅指“壞形象”的傳播效率,還對人的生活能力提出了全方位的新挑戰。比如支付寶、網購、網約車、共享單車,對于能夠適應技術變化的年輕人群而言,生活變得越來越簡單,而對于很多老人而言,則越來越艱難,環境正變得越來越不友好。
“老人小惡”并不值得寬容,但值得理解。他們在努力擺脫了生存問題之后,卻迎頭趕上了一個四下惶惑的世界。
有人對現代工業社會里人的“孤獨和不愉快”提供了一個分析角度:現代工業社會處理人事的能力跟不上處理技術的能力。人們對技術的操控得心應手,但對如何與他人進行情感交流越來越生疏。
今天的現實是,相當一部分人非但無法處理人事,而且也無法處理技術——這便是今天的老人。
他們中的大部分,都符合下面幾個要素中的某幾個: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齡未能受教育,在青春尚在的時候經歷下崗;在年輕時經受長輩的權威卻在年老時無法繼承這一權威;在青春消逝后被動急劇城市化,在惶惑的技術環境下,成為騙子與謠言的捕獵目標。
在現實面前,這一切都會轉換為一種非常可怕的心理體驗——強烈的被剝奪感,它會轉化為人格上的攻擊性。
“技術性孤立”
即便全世界都不理你,你也不會瘋狂。因為不是個人被動孤立,而是人主動把環境孤立了。
關于“問題老人”現象,有一種觀點聽起來非常“進步主義”,它說:自己出問題,不能賴時代。
如果它所指的是“不能用問題來否定時代進步”,那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其意思是說“社會問題跟社會沒有關系”,那說話者的面容就變得很抽象了。
這不叫“賴”,而是解析,下面進一步解析。
人的孤獨存在,是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間的顯著區別,客觀地看它是中性的,既不積極也不消極,但人是有情感的,從情感出發,孤獨存在就是一種病態。而今天,強大的技術讓它不再是一種病,而是人的正常又甘愿的存在方式了。
這個強大的技術,是智能手機終端及其后面的一整個支持性技術系統。一開始,是年輕人坐著、躺著、走著、開車、騎自行車都在玩手機,而這幾年,老人也被傳染,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又顛覆了傳統的社會學、心理學認知,“孤獨而不愉快”轉變為“孤獨且愉快”。這一存在方式帶來的新局面是,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發生了主次易位。也就是說,通過移動互聯網所進入的那個空間,變得比現實生活空間更加重要了。
過去我們認為,一個人如果被周圍環境所孤立,時間長了是會出問題的。但現在,事實出現了反轉:即便全世界都不理你,你也不會瘋狂。因為不是個人被動孤立,而是人主動把環境孤立了。
這是一種技術導致的自我孤立,但技術讓孤立本身變成了一件深具樂趣的事情。同時人們發現,電子化的人際關系比現實的人際關系更容易處理,于是社交工具從現實的輔助變成了現實的替身。
結果是,人們在情感上和生活問題上彼此需要的程度下降了,因而人類的社會結合本能也在退化。不可避免地,人也會變得自私,變得對自身越來越愛惜,但對他者的戒備和敵意卻在不斷升級。
英國宗教倫理學家約瑟夫·巴勒特說:“一個人在世上可以有所有的自愛,而同時是悲慘的。”“悲慘”,是說缺失了直接的、真實的責任感,而被自身變異所俘虜。
沒有責任感的自愛,作用于他人便是敵意。
在某種程度上,一些“問題老人”也是這樣“中招”。
一個有社會大背景的問題,在整體層面上卻往往無計可施。對“問題老人”,空談社會教育或重復道德教條都沒有意義,而只能寄希望于個體的自我救贖和家庭成員的協助矯正。
(摘自《南風窗》2017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