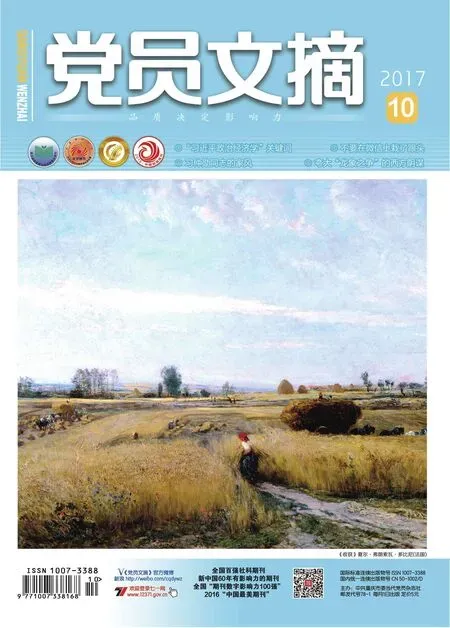從好萊塢到中國主旋律該如何唱?
□王煜
從好萊塢到中國主旋律該如何唱?
□王煜

“為啥美國的英雄主義就可以,中國的英雄主義就不可以?”前段時間,創造票房神話的“國民大片”《戰狼2》主角吳京怒懟一些網友。這說明一個問題:從美國到中國,電影中的英雄主義主旋律其實一直存在,而且很不少,關鍵在于怎么把它做好,讓觀眾買賬。
美國的主旋律
個人英雄主義是美國文化的主旋律。
西部片是舊時期好萊塢類型片中最能代表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片種,它所開拓的主旋律基調對后世的好萊塢電影影響深遠。20世紀30年代,美國進入大蕭條時期,民眾生活困苦、社會秩序混亂,此時電影《金剛》在一個破壞力極強的大猩猩身上突出表現了一個“暴力個人英雄主義”的典型。二戰之后,戰后的心理空虛在民眾中蔓延,于是宣揚美式民主和英雄主義的《超人》誕生,這個救世主的形象影響了幾代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強勢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地位讓美國人有自信將個人英雄主義理想在電影中變為現實,并在全球傳播,如《終結者》系列、《虎膽龍威》系列等等。
進入21世紀,美國的世界第一強國地位已經穩固,“拯救人類”“維護世界和平”這種主題又在《后天》《2012》《拯救大兵瑞恩》《狂怒》等一系列災難片、戰爭片中顯現。泛娛樂化蓬勃發展后,蜘蛛俠、鋼鐵俠、蝙蝠俠等美國漫畫中的超級英雄紛紛登上大銀幕,他們都擁有超強能力,一次次地重演“拯救”的橋段。
從始至終,幾乎所有的好萊塢電影類型中,包括西部片、黑幫片、戰爭片、動作片、科幻片、災難片,等等,都有很多是反映美國社會文化價值觀的主旋律影片。
“套路”也很重要
除了在內容上牢牢抓住當時社會民眾的心態外,好萊塢英雄主義電影在講故事時也特別遵從“規則”、講究“套路”。美國比較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一書中,就曾非常系統地分析出這一套編碼。無數好萊塢的主旋律大片都驗證了這個“套路”的可操作性和對觀眾的有效性。

坎貝爾是這樣描述“英雄程式”的:
首先是對英雄的“召喚”:英雄從來都是從普通人開始,慢慢走上英雄之路的,他可以是世界任何一角落的任何一個人。英雄的冒險,是從被召喚開始的。
一般來說,起初被召喚,主角都是拒絕的。只因敵人太強大,主角不認為自己能打敗對手。
直到“金手指”的出現,事情才會有改變。什么是“金手指”?就是超自然的助力。對,就是無論看起來是否合理,總之有那么一瞬間,天降祥瑞,主角瞬間開竅,明白自己要鼓足勇氣走上漫漫長路。
這條“試煉之路”是程式的第二個重點。通常,試煉之路,主角會遇到一個能夠激發潛能的強大對手,這個對手可能在整個故事里只是炮灰,是個小Boss,但是對于還是初出茅廬的主角來說,他已經足夠強大。為了解決對手,主角不可缺乏一些幫助他的人,比如精神導師,比如召喚集結到的一群小伙伴。利用這些幫助,主角順理成章地戰勝小Boss,獲得經驗、能力和團隊的提升。
經過試煉,主角終于直面大Boss了。如果因為有了“寶物”的加持就輕而易舉地贏了,那大Boss還是大Boss嗎?這就好像現在網友看社會熱點新聞,最喜歡看反轉一樣,任何英雄故事,都必須要有反轉。如果沒有反轉,沒迎合觀眾的心理期待,觀眾是不會答應的。反轉就是,眼看著要成功了,突然發生一些事情,主角失敗了。
當然,主角雖然暫時失敗了,但還是要堅強地支撐著,最終還是要能力爆發,戰勝大Boss。
大戰勝利之后,英雄回到起點,衣錦還鄉。留點余味,讓觀眾回味一下,思考人生。
這套程式放到好萊塢的主旋律英雄片中,幾乎是屢試不爽。
可以說,好萊塢的這些主旋律電影都是極其準確抓住了人性的特點,導演知道觀眾最喜歡看什么,就按這套規律去流水線式地執行。
中國的主旋律可以被唱好
回到中國的主旋律電影上來。以前的中國主旋律電影過于刻板強調個人的行為與國家、集體、組織、責任等聯系在一起,甚至被高度政治化、臉譜化,幾乎都是高大全的形象。
但同時伴隨著的問題就是觀眾的審美疲勞。好萊塢的導演明白這些,便塑造了去除光環的平民英雄、西部牛仔、強人硬漢。即使是有“主角光環”、超能力的英雄,也多了幾分人性的光輝,多了幾分真實,有血有肉,敢愛敢恨,有喜怒哀樂,也有五味人生,讓觀眾有代入感而不是產生距離感。
中國電影顯然也沒有理由拒絕英雄主義,只是需要借用好萊塢的方法來講好自己的故事。
比如《戰狼2》,不僅是這部影片需要一個主旋律的框架,反過來,主旋律電影也需要像《戰狼2》這樣來引入新的商業、娛樂元素。在《戰狼2》之前,一些中國的主旋律電影已經在嘗試改變,通過引入新的元素來吸引年輕觀眾。比如徐克導演的《智取威虎山》,監制黃建新透露,根據多輪試映的反饋,決定拿掉所有“講大道理”的臺詞。
如果要說“主角光環”“孤膽英雄”,中國的武俠奇幻文化中其實早就有了。反映到電影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武俠神怪片《火燒紅蓮寺》。也就是從上世紀的20年代開始,中國觀眾就開始接受直接發氣功波或者刀劍滿天飛的電影特效。從1928年到1931年,中國拍了227部武俠神怪片,幾乎部部都是主角開滿了“不死光環”。
武俠電影里的英雄一人單刀赴會打敗幾十上百人,我們看上去也不會覺得奇怪,因為這是中國自己的傳統。但是到了現代的戰爭片、動作片,還加上了主旋律,就需要心理的置換時間了。
排除那種“逢中國傳統必反”“逢主旋律必反”的觀眾群體,對大多數觀眾來說,審美從來都是建立在一定距離感之上。當中國觀眾看習慣了好萊塢主旋律的套路時,主人公突然變成中國人,這種審美距離突然被打碎,或許會產生下意識陌生的抵觸感覺。其實,重新建立國產的好萊塢氣質娛樂大片的審美感,需要一個過程。對于日益自信的中國文化,對于越來越會抓人心的中國主旋律電影,多看看,習慣了就好。
(摘自《新民周刊》2017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