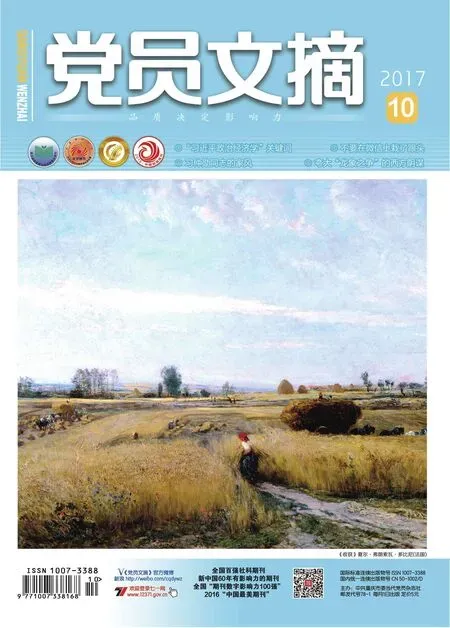時代在變,大師的定義也在變
□郭探微
時代在變,大師的定義也在變
□郭探微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百多年前英國作家狄更斯寫下的名言,放在“今天是否還有大師”這個話題中似乎挺恰當。
提到“大師”,很多人言必“民國”。確實,和民國時期相比,當下的“大師名錄”似乎黯淡了一些,我們很難立刻想到一個名字,在全民的認同中,把他奉為大師。其實,時代在變,大師的定義也在變。
只想到民國大師,是一種“回憶濾鏡”
辜鴻銘、章太炎、蔡元培、傅斯年、陳寅恪、劉文典、錢穆、顧頡剛、潘光旦、李濟、魯迅、胡適……這一大串閃閃發光的名字與那個烽煙四起、顛沛流離的時代緊緊聯系在一起,碰撞出獨特的魅力。
為什么我們覺得民國時期的大師那么多?
第一,當時大部分民眾處于蒙昧狀態,那個時期的大師們擔任了“啟蒙者”的角色,開啟了思想上的新時代。大多數情況下,“從無到有”都比“從有到多”有著更強的歷史意義,也更容易被人們記住。更何況這批大師生于憂患,重任在身,歷史形象如此鮮明,盡管現在的大部分人很難說清他們的學術成就,但那些民國大師留下的種種傳說足夠大家津津樂道了。
第二,亂世出英雄。民國時期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個杰出人才更容易受關注,也更容易被仰望。
第三,對很多人來說,遙望回不去的年代,時光總是最好的,我們用帶著濃厚主觀色彩的“回憶濾鏡”去追溯民國,那段風雨飄搖、國弱民貧的歲月也被鍍上了一層神秘的光彩。
感覺今天大師少了,是我們存在偏見
說完了民國的“回憶濾鏡”,我們再說說現今的偏見。為什么大家會覺得這個時代沒有大師了?
這是因為現在整個社會完成了從“精英社會”向“草根社會”的轉變。當夜空中月亮不再是唯一的光源,在漫天繁星鋪就的璀璨夜晚,你反而很難辨認出,哪顆星星是最亮的。
和民國時期相比,現今大眾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眼界更加開闊、見識更加豐富,對待大師的態度也變成了平視共處,并勇于發出質疑和反對的聲音。
這是一個消解權威的時代,任何一個權威式的人物出現,其學術觀點都有被質疑、被反對的可能。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更愿意用“專家”“學者”甚至不那么正式的“大咖”“大拿”去取代聽上去很神秘、神圣的“大師”稱謂。
比如登上《百家講壇》后被大眾熟知的閻崇年,他是清史研究專家,論述頗豐,和民國時期的清史大師孟森、肖一山相比,閻崇年的功底更為深厚,但上網搜索一下,隨處可見各種“反對者”的聲音。不要因此去感嘆什么人心不古,對比過去民眾較為單一的推崇心理,當代人敢于對大師提出質疑和思考,對大師進行“去神化”的解讀,更能體現出時代的進步。
因為社會分工不同,民國時期的大師們可以是一人橫跨多個領域的“百科全書式”人才,但現在的大師們多是集中精力在一個專業領域走得更遠更深,其取得的學術成就也許更高。但“隔行如隔山”,很多專業領域響當當的大師,如果沒有媒體的廣泛宣傳、民眾的特別關注,知名度其實是不高的。
隨便說幾個名字:戚發軔、談家楨、權希軍、陳能寬,大家能一一說出這些人的來歷,了解他們是干什么的嗎?戚發軔是我國空間技術專家、神舟飛船總設計師,談家楨是中國現代遺傳學奠基人之一、國際著名的遺傳科學家,權希軍是當代書法大家,陳能寬是金屬物理學專家、中國爆轟物理專業的開拓者。他們在各自領域取得的杰出成就足以被人們稱一聲“大師”,但因為“曝光率”不是很高,知道他們的人也遠沒有知道民國大師的人多。
今天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大師
和民國時期肩負著開啟民智重任的大師們不同,現今社會賦予了大師們不一樣的時代責任。今天的大師應具備的是工匠精神,具有專家治學能力,能夠用科研成果讓百姓的生活更好,讓社會更加進步。
在這個年代,其實不需要羨慕旁人,我們每個人都有成為專業領域大師的可能。
因為這是一個教育普及的年代。國家給了民眾平等受教育的機會,擁有知識不再是哪個階層、群體的特權,我們有機會學習各個行業最專業、最頂尖、最前沿的知識。
因為這是一個全球緊密相連、各種觀點思想都在碰撞、都被包容的年代。我們會接觸到來自全球的海量信息,積極創新也被時代允許和鼓勵,也許我們的每一次異想天開、每一次成功實驗,都將在下一秒改變世界。
因為這是一個站在大師肩膀上繼續前行的年代。前人留下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無比豐富,站在巨人的肩頭,我們有能力看得更遠,走得更遠。
可以說,今天這個時代,只要你認真努力,心懷目標,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擅長、專業領域的大師。你可能因為寫出了杰出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成為被民眾熟知的“國民大師”;也可能在某個冷門、小眾領域有了驚人發現或者新的理論,而成為被業內認可的“行業大師”;甚至你可能因為特別會收納、打理家務,經過你的妙手,能讓一個普通的家變成獨一無二的溫暖存在,而成為家人心中的“生活大師”……
夜幕下,一輪明月高照固然美麗,但總顯得有些清冷。只有群星的燦爛閃耀,才組成了最熱鬧、生機勃勃的夜空。今天的時代不是沒有大師,而是對大師的定義已經改變。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大師。
(吳寶河薦自《時代郵刊》2017年第8期圖:項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