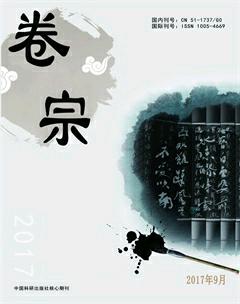不安靈魂的獨白
摘 要:提及驚世駭俗的寫作能力和離經叛道的寫作風格非卡夫卡莫屬。他的一生創造出《變形記》,《城堡》,《饑餓藝術家》等多篇長、中、短篇小說,給人類文明和爭芳斗艷的世界文學留下了豐碩的成果。而其孤獨的一生,為藝術和鐘愛的文學奉獻的一生更是令人嗟嘆和敬仰。本文以《饑餓藝術家》這篇短短幾頁的小說,窺探卡夫卡的生命軌跡和心靈世界。
關鍵詞:卡夫卡;《饑餓藝術家》;孤獨
提及卡夫卡,總會被他驚世駭俗的寫作能力和離經叛道的寫作風格所震撼。他“改變了二十世紀整個德語文學的面貌”。[1]而他曖昧的身份卻使得他的世俗身份很難界定——操一口德語卻在意大利上班,生于布拉格實際是奧匈帝國的臣民,供職于一家保險公司卻與寫作產生一生的情緣。這種曖昧的身份使得他長期幽閉在一個任其思維和靈魂游蕩的狹小空間。他的作品自傳性很強,連他自己都認為:“寫作意味著直至超越限度地敞開自己。”[2]作為最精湛的短篇小說《饑餓的藝術家》無疑是他一生最真實的寫照,它完美詮釋了卡夫卡的生命軌跡,清晰地折射了作家的心靈世界。當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校完此稿不禁淚流滿面。
1 寫作的苦行僧
卡夫卡一生的終極追求是:完全獻身于寫作。寫作幾乎占據了他的整個生命。“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寫作的,絲毫沒有多余的東西,即使就其褒義而言也沒有絲毫多余的東西。”[3]他忍受著孤獨,可能也享受這種孤獨,徜徉在文學的世界。他幾乎失掉常人一生中該有的生活,埋頭于自己熱愛的文字。
這位有些偏執的寫作者,為了鐘愛的文字,一再猶豫自己是否結婚。他一生放棄了幾次訂婚,斬斷了所有可能阻礙他進行文學創作的阻礙物。當婚姻與文學發生沖突,他痛苦、糾結的還是選擇了文學。
其中與費麗斯·鮑威爾5年的感情長跑使他最為糾結,兩度訂婚又依次解除婚約。我們從卡夫卡的日記里看到他的個人獨白;“我一直來多么熱烈地愛著費麗斯。主要是出于我的作家工作的考慮,是它擋住了我,因為我相信婚姻對這一工作是有危害的,我何嘗不想結婚,但單身生活已在我現在生活的內部把它毀滅了”。他沒能解決好婚姻和寫作之間的矛盾,他擔心婚姻會占據和耗費他過多的有限生命。所以,即便鐘愛費麗斯也不得不放棄結婚的念頭。
而在當時他的作品是不那么受追捧的,他的許多作品一直是書店的滯銷書。似乎很少有人理解和讀懂他,所以,他就像是一位獨行者。而他自己又是一個追求完美藝術的人,他經常對于自己的作品不滿意,經常對于自己的作品橫加挑剔。生前發表的幾部作品也是在好友勃羅德的苦苦懇求中見諸于世。甚至到生命的最后關頭,他留下遺囑讓好友勃羅德把他的作品付之一炬。
他孤獨的寫作,孤獨的摯愛著文學,孤獨的與文學對話,孤獨的喃喃自語。他是一位寫作上的苦行僧。
2 藝術的殉道者
作為最具卡夫卡真實寫照的《饑餓的藝術家》最能闡釋和表現出卡夫卡的藝術世界。讀完《饑餓藝術家》,幾乎可以悲憫的感受到來自他內心深處的無奈和哀嚎。“這是他為他自己和他的同類所寫的挽歌,而他自己則是挽歌中最令人心碎的注腳,并且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4]“凡是我寫過的事情將真的發生,通過寫作我沒能把自己贖回來。”[5]“作為作家的我當然馬上就要死去。因為這樣一種角色是沒有地盤、沒有生存權利的,連一粒塵埃都不配。”[6]這些觀點在《饑餓藝術家》中一一得以驗證。
(一)饑餓藝術家是一幅卡夫卡的自畫像
了解《饑餓藝術家》文本的讀者都知道藝術家臨終前的一段話:當管事詢問道到底什么時候才能停止不吃食物。饑餓藝術家當時的生怕對方漏聽一個字:“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驚動視聽并像你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依然堅定自己的信念:他要繼續餓下去。可以看出卡夫卡內心的痛苦和無奈甚至絕望。寫作是我幾乎全部的事情而我卻找不到一個令我滿意的作品,為了實現心中的信念,即便我生命即將終結,即便我不為別人所認同,我也不會放棄終生愿望—為寫作而生,因寫作而亡。我生命的全部只為寫作,寫出我認為有意義的,真誠的東西。
(二)饑餓藝術家的一生就是作者的一生
饑餓表演曾風靡全城,無人不曉。而現在世風日下。以前很多人為了看饑餓表演甚至長期觀賞,不曾離開。但這僅僅“取個樂,趕個時髦而已。”沒有人在意饑餓表演的真正意義是什么,更沒有人在意饑餓藝術家是如何看待他的表演。如何視表演超越生命存在。
別人甚至懷疑他的表演是不是弄虛作假。于是,看守人員每日看守,不給他任何偷食的機會。作為藝術家本身“他的藝術的榮譽感禁止他吃任何東西。”[7]而看守人有意給他留空隙讓他偷吃。藝術家“變得憂郁消沉”,“表演異常困難”。為了顯示他沒有偷吃東西,他“不斷的唱歌”。可別人因此倍加嘲諷,“他竟能一邊唱歌,一邊吃東西。”甚至后來藝術家請看守吃早餐,他們也把他看作是賄賂別人利于偷吃的手段。所有這些誤會和侮辱他都可以忍受,為了摯愛的饑餓表演,他繼續著他的表演。
最不能忍受的是幾乎每次還沒有表演盡興,還沒有到達他最出色的表演時刻。滿40天的表演即將結束,他覺得自己的表演是沒有止境的。如果堅持下去,他的表演將達到常人所沒有的高峰。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饑餓能力是沒有止境的。”別人都以為表演結束了,“只有饑餓藝術家不滿意,總是他一個人不滿意。”
沒有一個人能夠認真體察他的心情。即便別人的憐憫也是因為可憐他挨餓的瘦樣子,沒有人理解他,沒有人明白他很渴慕這種表演。所以,他感到更加可恨。
他們甚至不懂得饑餓是什么。他們只是看熱鬧而已。
即便后來饑餓表演變得不再流行,“到處可以發現人們像根據一項默契似的形成一種厭棄饑餓表演的傾向。”他依然堅信“饑餓表演重新風行的時代肯定還會到來”,“他對于饑餓表演這一行愛的發狂,其肯放棄。”人們把他安排在一個馬戲團偏角。他依然進行著自己表演并且堅信他可以讓世界為之震撼。但是“在行的人聽了只好一笑置之。”endprint
“假如有一天,來了一個游手好閑的家伙,他把布告牌上那個舊數字奚落一番,說這是騙人的玩意,那么,他這番話在這個意義上就是人們冷漠和天生的惡意所能虛構的最愚蠢不過的謊言,因為饑餓藝術家誠懇地工作,不是他誆騙別人,倒是這世人騙取了他的工錢。”對于藝術的追求與摯愛卻換取別人的鄙夷和詆毀這是卡夫卡所不能忍受的。他堅硬而又憤恨的回絕—是世人騙了他的工錢。內心的折磨和沉重令人唏噓不已。
3 總結
川端康成說過:“藝術家是行將滅絕的種族。”[8]盡管“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藝術的追求也將永不停息,更不會因為生命的消逝而終止。饑餓藝術家的一生就是卡夫卡真實生活和內心情感的真實寫照。但又遠不是卡夫卡一生的總結。他蘊含著所有執著于文學藝術,探尋生存意義的精神游蕩者和孤獨者。具有普適性和共通性。那種筆尖下流露出的堅定不移的信念、不被理解的孤獨感滲入到每個讀懂卡夫卡的人的心靈。
注釋
[1]葉廷芳:《通向卡夫卡世界的旅程》.文學評論(京).1994(3)80頁.
[2]卡夫卡.致菲利斯:論卡夫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72頁.
[3]卡夫卡:《卡夫卡書信日記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189頁.
[4]張天佑:《藝術·藝術家·觀眾—論卡夫卡的藝術館》.蘭州大學學報.2000,28.154頁.
[5]卡夫卡:《卡夫卡書信日記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167頁.
[6]同上,172頁.
[7]本文均引用卡夫卡:《卡夫卡集》.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年.不一一標注.
[8]川端康成:《我在美麗的日本—臨終的眼》葉渭渠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197頁.
參考文獻
[1]葉廷芳:《通向卡夫卡世界的旅程》[J].文學評論(京).1994(3).
[2]卡夫卡.致菲利斯[A].論卡夫卡[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8.
[3]卡夫卡:《卡夫卡書信日記選》[M].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
[4]張天佑:《藝術·藝術家·觀眾—論卡夫卡的藝術館》[J].蘭州大學學報.2000,28.
[5]卡夫卡:《卡夫卡集》[M].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
[6]川端康成:《我在美麗的日本—臨終的眼》[M].葉渭渠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
[7]李忠敏:《宗教文化視域中的卡夫卡詩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5.
作者簡介
韓營(1992-),女,文學碩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