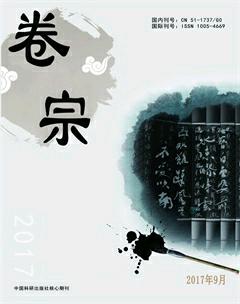宋代密疏進呈渠道略論
張華立
摘 要:宋代正處中國古代密疏制度的重要發展變革期。為保證密疏的保密及順利進呈,獲取相對真實的第一手的治國理政信息,宋政府在構建密疏進呈渠道上不遺余力,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嘗試,構建出常規渠道與特殊渠道相配合,中央與地方相區別的獨具宋代特色的密疏進呈體系,為中國古代密疏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貢獻。
關鍵詞:宋代;密疏;進呈渠道
宋代是中國古代密疏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但學術界在對唐、明密疏制度給予關注的同時,對宋代密疏制度的論述卻較少,只在少數其他著作中略有述及,且流于寬泛。本文擬通過對宋代密疏通進渠道的略述,以期對密疏進呈渠道在宋代的變化有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并希望能對唐明之間密疏演變過程的相關研究有所增益。
1 宋代密疏進呈的常規渠道
密疏通進的常規渠道,指朝廷官員根據官位品級及距京遠近,即可享有的通過某種渠道通進密疏的權利,主要表現為授予群體的眾泛性和通進渠道的多元性。綜合現有史料,并依照官員所屬區域距京師路程以及遞送方式的差異又可細分為在京官員密疏進呈渠道和地方官員密疏進呈渠道。
(一)在京官員的密疏進呈渠道
1、通進司
通進司設置之前,閤門負責在京百司奏疏及密疏的通進。太宗淳化四年,始置通進司“掌受銀臺司所領天下章奏案牘及閤門〔在〕京百司奏牘”(p3003)閤門所領內外奏牘俱歸通進司。但密疏仍可由閤門通進,真宗咸平二年,仍有“文武群臣封事,閤門畫時進入,勿使稽留”的詔令出現,閤門依然是密疏進入的主要渠道。直至真宗咸平四年,始有朝臣通過通進司進呈密疏的記載。真宗咸平四年,知泰州田錫應詔還朝,受命整理太宗時所進封章,并進呈《進撰述文字草本狀》稱“今詣通進司進上件草本四卷,隨實封狀聞奏”,是關于通進司承接密疏的最早官方記載。表明至遲在真宗咸平四年,通進司已具有具有明確意義上的密疏通進職能。
此后隨著閤門文書通進職能被統治者有意弱化及通進司體系的逐漸完善,通進司承接密疏數量的日漸增多,承擔了大部分在京官員的密疏通進,通過英宗時大臣李柬之所上奏章我們可以略窺當時的情景。治平元年十一月,知通進銀臺司事李柬之上書英宗:“應內外臣僚所進文字,不限機密及常程,但系實封者,并須依常下粘實封訖,別用紙折角重封。有印者內外印,無印者于外封皮上臣名花押字,仍須一手書寫。所有內外諸司及諸道州府軍監并依此例。”[1](p3004)對通進銀臺司在處理繁多的密疏時遇到的封面書寫混亂,體制不一等問題提出建議,不僅明確了通進司收掌密疏的職能,且“內外諸司及諸道州府軍監并依此例”,可見通進司已成為宋代官員密疏遞呈的主要渠道。
密疏想要通過通進司進呈,首先應取得通進司的文字通進權,但綜合現有史料來看,并非易事,只有在京高級官員方可通過通進司直接通進,普通及致仕官員則需事先奏請,有兩例可證。一例為慶歷五年,右屯衛上將軍致仕高化言,苦于“每有所進文字,須詣登聞鼓院,并與農民等”,而上書仁宗“乞詣通進司投下”,仁宗專門下詔:“今后文武臣僚內曾任兩地及節度使并丞郎已上,不曾貶黜,后來除致仕官者,如奏章文字,并許于通進司投下”[1](p3004)則慶歷五年之前情況更可想而知。一例為熙寧二年中書省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李承之”昨奏對言舉官事,令具文字進呈。”卻因”緣系選人,無處投下,乞許于通進司投進。”[1](p3005),李承之雖任要職,卻因“緣系選人”,而沒有資格詣通進司進呈奏疏,惟有通過中書省向皇帝提出申請,最終得到神宗“詔許于通進司投進”的答復后,才獲得此項權利。由此可見,除臺諫官外,只有較高級官員可通過通進司遞呈奏疏,有差遣而無官職及其他“無例通進文字”者,要得到皇帝首肯,才能通過通進司進奏。
2、登聞鼓、檢院
宋代的登聞鼓、檢院是宋代在京低級官員及下層庶民密疏進呈的重要渠道。
登聞院作為密疏進呈渠道在其職能中已有所體現。清人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中對宋代登聞院職能有精煉概括,稱其“掌諸上封,受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狀。”[1](p3092)表現在歷代宋帝所頒布詔令中更為明顯。如元豐八年六月,神宗崩,哲宗繼位,詔:“應中外臣僚士庶,并許實封直言朝政......在京于登聞院投進,在外于所屬州軍驛置以聞。”[2](p1966-1967)哲宗元符二年三月,詔臣僚士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于所屬州軍赴遞以聞”[3](p2006)。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詔:“中外臣僚士庶,并許實封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3](p2006)。紹興三十二年六月,詔“自今時政闕失,并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鼓院投進,在外于所在州軍實封赴遞以聞”[4](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申)四則詔令雖時間不一,但可證登聞鼓、檢院最遲至哲宗以后已成為在京宋代官僚特別是庶民階層呈遞密疏的重要渠道。
此外,多種史料表明,即使有專門負責審閱封事的封事看詳官的存在,登聞鼓、檢院的密疏仍然有機會得到皇帝的親自審閱處理。如天圣七年六月,鑒于檢院所上封事過多,仁宗以近臣晏殊等“看詳轉對章疏及檢院所上封事”,就引起了朝臣的強烈反對,右司諫范諷甚至以“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為陛下極言者”[5](天圣七年六月辛卯)為由進行勸阻,仁宗幡然醒悟。此后的宋代皇帝在位初期大多遵守著親閱登聞院所上密疏的傳統,并將其公開化,作為聚斂人心的一項重要措施。如元豐八年,初繼大統的哲宗所發布的第一封求疏詔中即有“并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在京于登聞院投進......,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2](p1966-1967)的語句。徽宗宣和七年所發布的詔書中更加明顯“中外臣僚士庶,并許實封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雖有失當,亦不加罪”[3](p2006)。
3、閤門司
通過諸閤門通進密疏也是北宋前期在京官員密疏通進的重要渠道之一。據清人紀昀所編《歷代職官表》載:“謹案唐代四方館及閤門俱得受四方章表而不詳其異同之制。考唐自中世以后,京僚上奏大抵在閤門投進”[6](p401-402),唐中后期諸閤門文書通進職能已較為完善。
北宋初期,承唐舊制,閤門仍為在京官僚奏疏通進的主要渠道,密疏也多由此通進。如端拱元年三月,太宗“患群下莫敢自盡以奉其上”,下詔申警群臣,“其后,上封者頗眾,有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5](端拱元年三月己酉)。咸平二年,真宗詔“文武群臣封事,閤門畫時進入,勿使稽留”[5](咸平二年夏四月丙辰)。景德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真宗下詔:“應在朝文武百官等,侯得替,先具民間利害,條例實封,于閤門通進”[1](p215)等。
但隨著多元化的密疏通進渠道的逐漸開通,登聞鼓、檢院、通進司甚至御藥院等都成為密疏通進的渠道之一,閤門司的密疏通進職能被大大削弱,只能畏縮到慶禮、慰禮等特殊場合,真宗以后閤門接受密疏的詔令及事例已鮮少出現。
(二)地方官員的密疏進呈渠道
宋代對地方官員管理嚴格,無皇帝特許或重大事件,一般不許擅離所轄區域。因此地方官員的常規密疏通進渠道與在京官員相比數量上要少得多。除可遣人直接赴前所述登聞鼓、檢院進呈外,只有進奏院和走馬承受兩種。
1、進奏院進呈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以后,詔改進奏院為“鈐轄諸道進奏院”,掌“受天下章奏、案牘、狀牒以奏御,分授諸司”[1](p3011),地方所上奏章于進奏院匯集,隨后分類報送樞密院、中書門下或通進銀臺司等機構處理。
進奏院所受密疏多來自地方,可分為地方官員所進密疏及地方吏民所進密疏。進奏院日常只接受地方官員密疏,但若遇非常時期,如前所述宋代皇帝面向“中外臣僚士庶”頒布求實封詔時,接受地方吏民所上密疏也成為其份內之責。如《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四五載:“諸州實封奏狀委監進奏院官看詳,驗無損動者,題『封記全』三字,即時進內。有損動者,重封進入”[1](p3013)。諸州實封奏狀都要經進監奏院官驗證無損動后,方可入內。
進奏院對所進密疏的處理也與普通奏疏不同。如前所述,對于地方送呈的普通奏疏進奏院不能擅自呈遞入內,需報送通進司,由通進司通進,要嚴格遵循進奏院-通進司-皇帝的順序進行。而對于密疏的處理則似更加直接,可越過通進司直達皇帝。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九月,詔“諸州實封奏狀委監進奏院官看詳,驗無損動者,題『封記全』三字,即時進內。”要求進奏院對諸州所上實封奏狀,驗訖無損動者應立即呈送。四年二月又下詔:云“應外州官吏奏民間利病,實封者即時進入,不得拆封。”對地方官吏所上密疏,要求進奏院做到即收即入,不可拖延。
2、走馬承受進呈
走馬承受是宋代設于地方專門用于傳遞地方軍情、監督地方軍政官員的特殊機構,也是地方高級官員密疏通進一條更為高效的渠道。
走馬承受職位雖低,卻身兼圣寵,不僅可隨時動用馬遞傳遞文書且享有不時入京覲見皇帝的權利。英宗以前,走馬承受“無事則歲一入奏”,至神宗時可“春秋赴闕”[1],此后次數被固定為一年兩次,且“邊防有警,不以時馳驛上聞”這些都為密疏的進呈提供了方便。
與地方官員一般性的遞鋪-進奏院-皇帝相比,走馬承受獨立的密疏通進體系無疑更為保密和高效,亦更為皇帝看重。因此地方官員多有利用職權便利,通過走馬承受上呈密疏者,最知名的,當為真宗時大臣李應機。李應機赴任益州通判前曾得真宗私囑:“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李應機到任不久,即有走馬承受依例入京覲見,于是遣人對走馬承受說:“應機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應曰:“諾”,甚至這位官員在覲見皇帝時還得到了皇帝的特別詢問,“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7](p128)。材料中走馬承受在“不知上旨”的情況下,雖不高興但卻不得不接受李應機委托,而不擔心事后遭到責問,且覲見時得到了皇帝的親自詢問,說明至少在真宗時期,地方高級官員通過走馬承受呈遞密疏的方式應是被默認的。但這種默認并非無所限制,只有地方較高級官員或沿邊將帥才能享有。
2 宋代密疏進呈的特殊性渠道
特殊性通進渠道是指非常規的,有時需經皇帝特別授權方可使用的密疏通進渠道,主要包括:御藥院通進、內東門司通進、個人利用覲見皇帝之機直接面呈及通過他人轉呈四種形式。
(一)御藥院通進
御藥院為具有皇帝特殊授權的在京官員使用的密疏呈遞渠道。御藥院設于太宗至道三年,本為皇帝服務的御用醫藥機構,深受皇帝寵信。宋仁宗時期開始,御藥院的職能日益增加,開始承擔呈遞外朝奏章的職責。其后多有乞請于御藥院呈進密疏者。如慶歷三年,宰相呂夷簡致仕,諫官歐陽修上書“風聞呂夷簡今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于御藥院暗入文字”[8](p606)。御藥院所接收“暗入文字”,即秘密奏疏。
(二)內東門司進呈
內東門司與御藥院同屬入內內侍省,是皇帝的內侍機構,主要“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訶之。承接機密實封奏牘,內外功德疏,回賜僧尼道士恩澤”[1](p3903),是承接外臣機密章奏,通進入內的重要機構。另據《宋會要》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載“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宮禁出入之事......若承詔有所須索、錫予,則謄報所隸而留其底。貢奉之物則受注籍以進,奏封干機速亦如之”[1](p3903),可見內東門司不僅可收掌密疏且所處理的章奏多是“干機速”的重要密疏,理應是密疏進呈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史料中關于內東門司對其這一職能的使用卻鮮少提及,除真宗景德四年年,曾下詔:“詔皇城司,雄州遞直赴內東門投下,每旬據數報樞密院”[1](p3859) 。及大中祥符六年詔:“教坊入內祗應,委副候提轄,不得妄有陳乞。例進兒男,許于使副處陳狀,具所習曲調按試。精通及好人材,即開析體例實封,于內東門以通”[1](p3629)外,其他史料鮮少記載。
(三)個人通過覲見皇帝之機直接面呈
除通過御藥院、內東門司及入內內侍省通進密疏外,也有通過個人覲見皇帝之際,直接面呈者。較有代表性者為太宗時期的田錫。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寅,田錫受命赴任河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5](p495)。
(四)通過他人轉呈
當密疏上呈者身處外地或不便出面時,可通過他人轉呈。這種方式除要求上呈者與轉呈者之間良好私人關系外,還要求轉呈者具有隨時面見皇帝的權力,當朝宰執成為第一選擇。如宋理宗紹定四年,史彌遠當國,都城臨安大火,尚右郎官吳潛上書無門,轉投史彌遠,羅列節俸級等六項建議,“欲丞相試入鈞慮,密啟主上,作一指揮”[9]。紹興十三年,汪藻受言官彈劾貶居永州,五年后欲乞致仕還鄉,上書時相云“適當引年之期,許為歸老之計。附之密啟,賜以生還”[10]。但若遇特殊情形,如皇帝疾病或其他個人原因,不見群臣時,宗室便可代為中轉。如光宗紹熙年間,孝宗禪位,退居重華,有疾,光宗不問,亦稱疾不理朝事,致使“中外憂懼,計無所出”,大臣陳傅良等即利用與嘉王趙擴良好的私人關系,向宮內呈遞密疏,最終迫使寧宗讓步。事后,陳傅良為表感謝,寄書嘉王“嘗賴大王密啟中宮,從容調護”并再次請求“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此固非大王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宮”,嘉王應允,回復“可改一本,不須作文字,便封來”[11]。
3 結語
宋代的密疏通進方式在繼承唐末五代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革創新,創立了常規渠道與特殊渠道相結合的嚴密完整的密疏通進體系,特別是特殊性的密疏通進渠道,因事而設,特權特授,是對密疏通進方式分層次,特權化的一次有益嘗試,對后世密疏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清)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 畢沅撰:《續資治通鑒》卷78《宋紀》,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版。
[3](宋)楊仲良撰,李之亮校:《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宋)李心傳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
[5](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
[6](清)紀昀等:《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7](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8](宋)歐陽修撰;張春林編:《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9](宋)吳潛撰:《履齋遺稿》,四庫全書本。
[10](宋)汪藻撰:《浮溪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11](宋)陳傅良撰:《止齋先生文集》,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