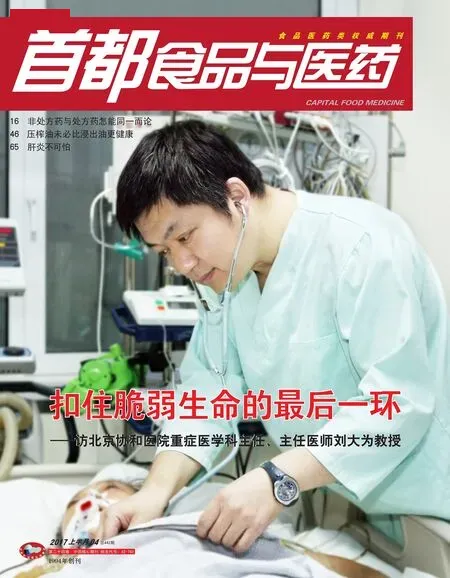風雨過后才見彩虹
● 本刊實習記者/

本刊記者 高軍/攝
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已經邁入第八個年頭,新一輪的醫改政策也在制定中,對于應該怎么看待醫改以及三醫聯動等熱點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從三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健康產業的大潛力
2016年8月,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的召開吹響了中國建設健康中國的偉大號角。張伯禮院士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會,一方面它響應了世界衛生組織建設健康國家的號召,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提出了三個重要論斷。一是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二是要把健康納入到各項政策之中,三是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這三點都是對全民有用的論斷。
除了這三個論斷,會上還強調醫學界要以預防為主,從治病轉向維護健康。同時對醫療、衛生事業從整體上進行規劃,不僅僅是去醫院看病,還要做到預防保健,并且跟養老結合起來。“我建議大家要認真地學習總書記、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講話和這個會議的文件,為什么?因為這里面就是商機。”
張伯禮院士談到,會上講到的健康服務業在國務院的規劃中曾專門提到,到2020年規模要達到8萬億元,而現在我國健康服務業的整體規模近5萬億元,不到4年的時間要增長3萬億元,可見這其中的商機非常大。“我國健康服務業的市場還遠未成熟,現在醫療移民、醫療旅游、國外購藥的人越來越多,就是因為國內的市場無法滿足他們,如何把這部分人留在國內,這其中就充滿了商機。我覺得醫藥企業除了做好藥外,還應該關注健康服務業這個龐大的市場,就目前來看,到2030年,健康服務業的規模將達到16萬億元。”
怎么看醫改
張伯禮院士從宏觀、微觀兩個方面表達了自己對醫改的看法。“從宏觀上看,中國的醫改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國政府用5%的投入使國人的預期壽命達到76歲,美國政府用GDP——18%的投入,使其國民的預期壽命達到79歲,每個美國人的平均醫藥費是9400美金,而我們中國人的平均醫藥費只是他的零頭400美金。醫改推行至今,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國的兒童死亡率、醫改覆蓋率都達到了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所以,從大方面來看,我國醫改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全國人大代表張伯禮
張伯禮院士說,從微觀上看,中國的醫改還存在著很多問題。“醫療環境的惡劣就是其中一個問題。我國現在的基層醫療整體呈虛化狀態,就是房子都蓋好了,但是里面沒有人。為什么?因為沒有能力,醫生進不去,這與醫學教育問題、職業環境問題都有關系。當然這些問題并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一直存在,國家也一直在解決,但是也一直出現新問題,我們的改革就是在這樣的磕磕碰碰中前進的。十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事沒有辦不好的,但是需要大家有點耐心。對待醫改,也應該這么看。”
張伯禮院士強調,有關醫改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在談到政府該不該管的問題上,張伯禮院士表示,政府不能不管,并且必須要管。他說:“政府要管什么?政府要出錢,政府不出錢不行。現在是政府和市場合作在解決醫療問題,醫療是一個國民的事,是一個國家的事,所以政府必須要管,但管的比例要研究。”
美國的醫療改革在推行8年之后以失敗告終,這就說明醫改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張伯禮院士認為,有的人把醫改的問題想得過于簡單了,認為醫改很快就會成功,但實際上,醫改的復雜性與長期性都不應忽視,“中國的醫改正在路上,我們以較少的投入辦成了較大的事。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醫改一定會成功,加之我們現階段的共同努力,中國的醫療狀況正在逐步好轉。”
在談到看病難、看病貴這個問題的時候,張伯禮院士表示,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已經初步解決了。在中國,有了病只要去醫院掛個號和排個隊還是都能看上的,特別是在基層一些二級醫院,并不存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目前的看病難、看病貴主要是指上大醫院看病難,上大醫院看病貴;找好醫生看病難,找好醫生看病貴。“我自己也是醫生,所以我想很多病人是真的必須要到大醫院來看病?頭疼腦熱的為什么非要到大醫院來看病?其實基層醫療完全能夠解決。”
對比國外的醫療模式,張伯禮院士以英國為例,指出英國雖然是政府全部承擔醫療費,但在英國看病需要排隊。等幾個月,等半年都是常有的事,其實“他們看病比我們看病要困難多了。再拿醫生開出的處方藥來說,無論是在英國還是中國,都是只開出幾天到一周的藥量,在哪里也不會開出半個月以上的藥量。所以說,在很多國家看病都需要預約,并非人們所想象的到那就看。當然想要享受到貴賓一樣的看病待遇也是可能的,那就是屬于貴族醫院、私立醫院以及個人商業保險的就醫情況了。”
張伯禮院士接著說,在醫改問題上,現在是看好病還有難度,找好醫生還有難度。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把“保基本”這條底線守住了,同時也要放開一部分高端市場。不論是專醫專護還是高級病房,要讓愿意花錢的人享受到他想要的服務,要把這部分人留在國內。現在,中國的一些民營高檔醫院已經有了這方面的投入,一天的服務費上千元,有的人自費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保基本”與高端服務可以并行不悖,既然有市場機制就應該弄活市場機制。
對于醫保個人賬戶的支付比例問題,張伯禮院士也表態,“一方面,在我國現行的醫保制度下,個人賬戶只需要負擔工資的2%。在國際上來看,單位賬戶與個人賬戶的比例通常為1∶1。我國現階段基本是4∶1,個人承擔2%,單位承擔8%~12%。所以我認為,適度地提高一些個人賬戶的支付比例是可以的,提高到4%應該是社會普遍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要適度調高封頂線,針對一些重大疾病,達到封頂線之后應該全額報銷,防止因病致貧。沒有病的時候,1個月多掏100多塊錢并不會影響你的生活,但是一旦得了大病,要花費幾十萬元,就可能會使你傾家蕩產,這兩種情況要調和好,充分發揮醫保的公益性、福利性。”
三醫聯動問題多
張伯禮院士表示,三醫聯動的問題應該說是最多的,特別是針對醫藥產業來講,新的舉措層出不窮。對西藥企業來講,有藥品注冊、醫保目錄支付方式、分類改革、一致性評價等問題;對中藥企業來講,有審評制度的改革、經典名方問題、注射劑問題等。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一定要看到三醫聯動依然在路上。
張伯禮院士說:“三醫聯動問題雖然很多,但是解決起來也很快。有關怎么調整的問題總的來說還是向國際靠攏,藥品是特殊的商品,藥品注重的是它的質量,所以建立一致性評價也好,去除臨床評價的水分也好,都是為了提高藥品的質量。這在戰略層面沒有問題,現在的重點是在技術層面上把它解決好。我特別希望能聽到基層的聲音,特別愿意聽到大家的意見,好為下一步改革劃重點。”
醫藥產業目前正面臨著困境,相關統計數據表明,中醫的制藥企業數量,包括批發的企業數量均逐年在減少。張伯禮院士對此有著自己的看法,“我們常說,風雨過后才見彩虹,雖然現在有很多企業退出了醫藥產業,但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一件好事,關停并轉之后鼓勵大企業適度兼并,形成大的集團才可能有大的投入,以此增加企業的科技含量,才能使企業健康發展,所以面對目前的困難,我們不能停滯,要大力發展科技研究,加大生產過程中對質量的把控。”張伯禮院士還談到,去年年底在韓國召開的大會發表了一個名為“智慧制藥”的宣言,特別強調要把大數據、信息科學引入到制藥過程中,進行全程質量監控,為的就是生產出更好的藥。
對于今年的醫改新動向,張伯禮院士指出,“今年新的醫改所涉及的醫保藥品目錄問題啟動得比較倉促,這也是為了配合兩會和‘十二五’的改革。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逐步規范醫保藥品目錄,規范就是你說你的藥是好藥要拿出證據來,你說你的藥能解決什么問題,也要拿出證據來。這些工作都要提前來開展,提前來應對,才能使醫改立于不敗之地。”
“總體來說,中國的醫藥衛生事業是全世界最復雜的,但是在底子差、基礎薄、人口眾多、國家投入不大的情況下,我國的醫改還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績。醫改路上還存在著很多的困難,只有我們團結起來,一起克服困難,一起解決困難,醫改才會成功,醫藥產業才能健康的發展。”張伯禮院士最后強調,“我特別愿意傾聽大家的意見和建議。我愿意同企業家聊一聊你們遇到的真正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