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和訪談
張利
張永和訪談
張利
雛形/Infancy
張利:在今天,您如何評價當(dāng)時在南工(現(xiàn)東南大學(xué))接受的建筑教育?
張永和:關(guān)于建筑教育,在說南工之前,其實還有一段該提一下。
我是1974年高中畢業(yè)。畢業(yè)后我就被分配到北京一個單位,叫北京市稀土研究所。實際工作是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圖1)。我爸覺得這個不是個事兒,其實我自己覺得還好。因為我的標(biāo)準(zhǔn)是沒下鄉(xiāng)就行。我爸認(rèn)為我得學(xué)一技之長。所以他就找一位老朋友教我畫建筑畫,這人是傅熹年先生。傅老師是看我父親的面子,因為我畫得實在是不怎么樣。傅先生自己畫得非常之棒。他給我看很多他從雜志上剪下來的畫,其實對我挺有幫助的。有的我還臨摹過。總之這就是一個開場白。
其實我在南工受的建筑教育是特別極端的。我是1977年上南工,文革后第一屆。按照現(xiàn)在眼光看當(dāng)時是完全不教建筑學(xué)的,就是教房屋設(shè)計。老師講得非常具體,有好多東西都明確地告訴你,比方說挑一個雨棚不能超過60cm,做個窗臺,坡度是多少。又比如一般磚頭怎么砌,表面是不是抹灰,要抹抹多厚。總之我學(xué)了3年蓋房子,從來不會談到任何想法,也不會談到形式、審美、理論什么的,一概沒有。原因是文革剛結(jié)束,老師們怕和意識形態(tài)掛鉤,不敢講。
張利:您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張永和:我曾經(jīng)覺得是壞事。
后來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跟沒學(xué)過建筑一樣。不過我覺得我挺有狗屎運,凈偶然碰對了事。我到了美國,是去了一個特別鄉(xiāng)下的地方,跟現(xiàn)在留學(xué)去精英學(xué)校什么的不一樣。我到了一個波爾州立大學(xué)(Ball State University),后來我愛開玩笑叫它“球大”。這個“球大”,是在印地安納州老玉米地里的一個小鎮(zhèn)上,任何方向走出去,恐怕開一小時車看不見別的,就是老玉米地。甭說什么先鋒的藝術(shù)、設(shè)計,完全不沾邊,就是那么一個地兒。
我去的第二個學(xué)期,就碰上一個老師。當(dāng)時美國英文我基本上能聽了。這個老師講話口音不一樣,一開口,什么也聽不懂。我問旁邊一個認(rèn)識的同學(xué),你覺得這人講得怎么樣,他說這人講得特有意思,我就跟著上了這人的課。這個人實際上是英國建筑聯(lián)盟學(xué)院(AA)來的。你知道好多歐洲人,把美國文化想得特別有意思,他就是奔著這個最平均的、最普通的美國去的。這個人教書,跟蓋房子一點都沒關(guān)系。他還挺跳躍,講講文藝復(fù)興時代的一些藝術(shù),繪畫、雕塑,然后就是現(xiàn)代藝術(shù)。
我從南工“啪”跳到“球大”這么一個地方,這個反差極大,極不適應(yīng)。可是最終不但適應(yīng)了,我還“進去”了。再過了一兩年回頭看,我又把南工學(xué)的東西拾回來,這倆搭上了,還行。也可以試想,如果搭不上,只有南工那種訓(xùn)練或者只有像這種“二手的AA”教育,還真有點麻煩。
張利:在南工時,您當(dāng)時和王群(現(xiàn)王駿陽)同一宿舍,而王建國和孟建民當(dāng)時也是同一宿舍,這實在是個有趣的現(xiàn)象。您能評價一下“舍風(fēng)”對一個人的成長所起的作用么?
張永和:我和王群,我們倆是77級的,王建國和孟建民是78級的。我們好多課都在一起上。這幾個人物里,孟建民是當(dāng)時幾個年級里最拔尖的,從文革前一直到78級,設(shè)計專業(yè)課成績最高的。在孟建民進來之前,設(shè)計最高分有人得過79分,但是沒得過80分。孟建民進來之后可能一下子就出現(xiàn)過84什么的,他把整個成績都給推上去了。不過他們宿舍里的情況就不清楚。
有意思的事兒是,如果南工有一個傳統(tǒng),主要還是源自巴黎美術(shù)學(xué)院的畫渲染什么的。現(xiàn)在有一波從南工出來的人都參與教學(xué),我和王駿陽在同濟,他在南大也還教點兒課,在南大的還有我們班的丁沃沃,顧大慶、朱競翔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王澍在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葛明留在東南大學(xué),看上去好像是一個體系,可是我不認(rèn)為南工真的很明確地教了這個體系。我認(rèn)為更是瑞士聯(lián)邦高工來的,實際上是南工受瑞士的影響。
張利:南工受瑞士影響?
張永和:因為這兩校有一個長期合作,有一大批人是從瑞士回來的。王群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他沒去瑞士,去的瑞典。到了瑞典之后,他接觸到北歐對建造的重視。在那兒他最終還是建立起來對于建筑的這么一個本體的認(rèn)識,所以還沾邊。我呢,是最不沾邊的,我去的是美國,學(xué)的很多是虛頭八腦的東西。那會兒正趕上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高峰,接觸了好多跨學(xué)科的、往外擴散的東西,我自己當(dāng)時也都覺得特別有意思。至今也一直喜歡電影啊、文學(xué)啊什么的。

1
再回到這個故事。我和王群呢,一個宿舍,同學(xué)關(guān)系很近,但不記得有什么舍風(fēng)。我1981年去美國,他把他的一本當(dāng)時沒畫完的速寫薄送給我做禮物了,特別珍貴,我也一直留著。
張利:聽您這么一說,原來南工到東南對“本體”的興趣,實際上跟蘇黎士有很大的關(guān)系?
張永和: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蘇黎士那個學(xué)校的體系,他們教一年級的那個老師,通常是一個很重要的教授,能夠把這個架子撐起來。他們的教學(xué)體系,換個老師可能改一改,但總有一個很完整的教學(xué)法。1980年代后期教一年級的叫克萊默(Herbent Kramel),他對這一批后來回來當(dāng)老師的南工學(xué)生影響非常大。
實際上我作為一個學(xué)生、以及后來工作多年都沒有直接和瑞士有交集。反而是回國后,從瑞士回來的同學(xué)那里了解了一點。近些年,我也去過若干次蘇黎世聯(lián)邦理工(ETH),到何塞普·路易·馬泰奧(Josep Lluis Mateo)的研究所講演,去參加迪特馬爾·埃伯利(Dietmar Eberle)的住宅與城市研究所開的研討會。
這個事和周榕還有關(guān)系。他寫了篇文章,是批判所謂本體建筑這波人。他說王群是最主要的人物,是“精神領(lǐng)袖”,還有受王群影響最大的那個人就是我。讓他那么一寫,等于替我們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東南學(xué)派”。(笑)
張利:那這倒是讓人感興趣,您赴美留學(xué)時中外差異遠(yuǎn)比今天大得多,您當(dāng)時是如何找到融入西方體系的切入點的?這對您之后的軌跡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您當(dāng)時在美國受的影響,全都是AA那些嗎?
張永和:AA對我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我在玉米地里沒有別的影響,也沒有太多理論學(xué)習(xí),就是之前說的AA來的這一個人,他叫羅德尼·普萊斯(Rodney Place)。他又有魅力,又有熱情,就照片上這位。他上課經(jīng)常是躺著上的,你看學(xué)生都圍著坐著。(圖2)
后來去了伯克利(Berkeley)就接觸到理論的東西了。美國東岸真正是理論的重鎮(zhèn),不光是理論家的理論,還包括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等建筑師的理論,那些我是比較后才接觸到的。可以說AA這點影響,慢慢過渡到了美國那些東西,所謂美國的東西實際上是以埃森曼為代表的,以理論優(yōu)先,然后實踐作為理論的一個物化或表達(dá)。我教書也是從“球大”開始的,那會兒對美國就比較熟悉了。后來去到了密大(密西根大學(xué)),就接觸到好多像埃森曼這樣的重磅人物了。
張利:我印象中,可能不準(zhǔn)。我記得那會兒我們都剛上學(xué),您做的一些東西當(dāng)時得了很多國際重要獎項,和美國人不一樣,有一種味道,或者有一種情感或者感情在它的幾何邏輯后面,這是怎么回事?張永和:其實是這樣的,最終這個躺著的羅德尼·普萊斯還是影響到我。這個人挺絕的,他非常能說,給我們看很多藝術(shù)的東西,但是到了具體指導(dǎo)設(shè)計時,他不會像美國老師那樣直接討論設(shè)計或形式,也絕沒有風(fēng)格傾向,就老說你多畫點再畫點。我現(xiàn)在特理解,只不過晚了40年,就是通過畫把設(shè)計往深里挖。我對文藝復(fù)興早期的繪畫以及對西方文化的普遍興趣,也是受他啟發(fā)。也可以說我被他帶入了西方文化。我開始教書后,發(fā)現(xiàn)老師可以在學(xué)校隨便聽課,我就學(xué)版畫、燒陶,還上過法文、電影史課什么的。自己沒有任何人能交流,當(dāng)時也沒覺得有問題。所以你看到的那些競賽,是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下做出來的:白天教書聽課,晚上帶著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到學(xué)生的圖房里,隨便找張空桌子,攤開了就畫。學(xué)生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也沒有人來問我,我就在那兒畫我的。
張利:所以反倒是這種環(huán)境屏蔽了當(dāng)時的所有的影響(contamination)?
張永和:現(xiàn)在回想可能是。當(dāng)時盡管還相對踏實,可是也知道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想象中那個世界一定特別振奮人心,比如像東海岸、西海岸。但總的來說我是在我自己的一個世界里。后來和外界接觸多了些。我還曾經(jīng)作為《世界建筑》的特約記者去紐約采訪了彼得·埃森曼,跟他混了一整天。
上面說的那種工作狀態(tài)可能還是我的一個根兒。后來做東西,受了好多流行的影響,一度相當(dāng)搖擺過,盡管不是太情愿。現(xiàn)在當(dāng)然非常希望“回去”了。
我的那些興趣,有些是有老師點了我,比如羅德尼·普萊斯,不過他們實際上常常帶出來的還是我原來就有的興趣,比如繪畫,還有文學(xué)、電影。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是留美時期特別重要的經(jīng)歷。
張利:您這么說我覺得一下子點透了現(xiàn)在這個問題。

2
成型/Formation
張利:在1990年代,您回到國內(nèi),以席殊書屋和非常建筑工作室開始了一種當(dāng)時在國內(nèi)還沒有的建筑方式。您當(dāng)時曾經(jīng)用到“純建筑”一詞來定義以建造本身為核心關(guān)注的現(xiàn)代性。這個“純建筑”的概念是當(dāng)時的一種批判性建構(gòu),還是貫穿至今的一種理論性建構(gòu)?“純”所針對的“不純”指什么?
張永和: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特別有意思。因為“純建筑”這詞好久不用了。其實我當(dāng)時說的所謂“純”就是“本體”。我可能還是在那個老玉米地里,老得想著老玉米地。開車特別容易走丟,因為那里的景觀是不變的,所以就可能有時想得比較極端。但是簡單地說,純建筑表達(dá)的無非是一個以建造和空間為基礎(chǔ)的建筑觀。那會兒是1985-1989年,盡管只是畫,可是畫的時候有一個建筑的語言,畫的都是房屋的基本構(gòu)建元素。
說到這兒,其實我還有一個相關(guān)的興趣一直沒太發(fā)展起來,而且到現(xiàn)在也沒想清楚,就是我對普通建筑的興趣。新文化運動推白話文,建筑有沒有白話文?現(xiàn)在的建筑設(shè)計實際上整個是文言文,這和它的新或舊沒關(guān)系,它可以是新的,但還是文言文,因為有一種自我意識,如果說得矯情些。
我有時會在圖里顯露出來一些把設(shè)計做得直白的傾向。回到中國做實踐之后,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如果設(shè)計沒自我意識,業(yè)主一看會認(rèn)為沒有設(shè)計啊。當(dāng)然我也把握不住那個東西,所以至今也沒做出來一個有說服力的“普通建筑”。
張利:但是您還對這個話題一直感興趣。
張永和:一直感興趣。偶爾會看見有建筑師做普通建筑做得挺好的,這些房子表面上看起來普通但常常有很講究的細(xì)部,只能說這仍是一個難題。它最終回到一個很簡單的評價問題,怎么區(qū)分這就是建筑,而不是房屋?建筑是不是就是指建筑師設(shè)計的?還有一個問題,是否存在沒有設(shè)計的設(shè)計?如果有,它質(zhì)量在哪兒?當(dāng)然我也沒解。我的《圖畫本》里畫的一些東西還是反映出這個興趣。后來我也把這個事兒和其他興趣串起來了,我對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的現(xiàn)成品也感興趣,可是也沒走遠(yuǎn)。最早在席殊書屋,就是用現(xiàn)成的——自行車輪子——接近“普通”,做了“書車”—— 一個旋轉(zhuǎn)的書架,但是結(jié)果并不普通。
你看得出來“普通”和“本體”有點近親關(guān)系,因為都相對比較直接、比較基本的,但又不是同一個概念。本體關(guān)心的更是建筑的核心知識,一個明確的范疇。至于你問題里頭建構(gòu)這個詞的用法,我不太明白。對我來說,在這里頭可能不是一個理論的建構(gòu),而是一個在操作層面上的東西。
最后說說“純建筑空間”。因為我一直認(rèn)為建筑空間是可能和用途脫開的,做到純。建筑如果每一個空間都是實用的話,建筑好像也有危險失去自己。所以我老覺得建筑里應(yīng)該有點純的,只是為了建筑本身存在的空間,但總不知該怎樣做,一直到最近。
在烏鎮(zhèn)的吳大羽美術(shù)館里終于做出來了,我把純建筑空間做成半戶外和戶外空間。這些沒有或局部沒用屋頂?shù)目臻g有著和室內(nèi)空間一樣的清晰圍合,但沒用確定的功能,設(shè)計中通過這些純建筑空間把功能空間串起來了。所以那個項目不是從面積上,而是從空間分布上,使得純建筑空間和功能空間各占一半。這個項目才剛剛開工,看看做出來會怎么樣。

3
筱原一男給一位詩人和尚蓋的谷川之宅,有個說不出功能的大空間,日本話叫“廣間”。我理解那就是一個純建筑空間——草坡穿堂而過,地面是泥土的。

4

5

6
張利:您剛才講了老玉米地,后來又到伯克利,這樣您在西方、在中國大城市、再到鄉(xiāng)鎮(zhèn)都有所接觸,應(yīng)該說有一個縱深的距離去深入到每一個社會。下面一個問題,就是關(guān)于您在北大創(chuàng)立建筑教育。您能不能講一下當(dāng)時這一選擇背后的策略,以及在今天看來這一選擇的得失?
張永和:我的經(jīng)歷中有兩個關(guān)鍵詞,一個是偶然,一個是矛盾。可能還得再加上一個——無知。我覺得常常對一件事情不夠了解的時候會構(gòu)成行動的力量。我們小時候有一個口號老掛在嘴邊——“知識就是力量”。后來我發(fā)現(xiàn),知識未必是力量,你要不知道,才比較會傻乎乎地往前沖。
首先,關(guān)于回國來實踐。我跟魯力佳那會兒稀里糊涂回來的,本來是回來過一個春節(jié)。后來就有人找上門來,反正我是很想蓋房子,就這么開始了。如果當(dāng)時真知道實踐是怎么回事,不見得敢開始。當(dāng)時真的是稀里糊涂就開始了,開始了就騎虎難下了,到現(xiàn)在想要退休好像也挺費勁的。(笑)
北大的事有一點點不一樣。我之所以教書也是因為羅德尼·普萊斯。后來有人跟我講,如果老師太好了,常常會影響學(xué)生去教書。羅德尼不但感染了學(xué)生,而且讓學(xué)生覺得教書這事兒特有意思。后來我到了伯克利,又遇到兩個老師,一個是我的碩士論文導(dǎo)師——典型的實踐建筑師斯坦利·塞托維茨(Stanley Saitowitz),他和羅德尼都是南非人,我開自己的事務(wù)所就是受他影響。另外一個又是學(xué)者,又是藝術(shù)家,是一個瑞典人,拉爾斯·萊勒普(Lars Lerup),又是一個好老師。所以我一路挺幸運。
總之我對教書這事兒一直比較起勁,我當(dāng)時有一個想法,也許什么時候我可以辦學(xué),那可能是1995年的時候。
張利:辦學(xué),已經(jīng)不是教別人讓你教的東西,而是教自己想要教的東西?
張永和:對,辦學(xué),要辦自己的學(xué)校。有個小插曲:有一天聽到消息說清華要來一個人做講演,這個人叫丹尼爾·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這人我認(rèn)識,我去匡溪藝術(shù)學(xué)院參觀時有一面之交,于是我就毛遂自薦給他當(dāng)翻譯。講演完了,我和魯力佳帶著他在動物園附近特爛的一個小館吃飯。我那個時候有各種野心,想要辦學(xué),我和他說我要辦一所前衛(wèi)的建筑學(xué)校。里伯斯金說話很婉轉(zhuǎn),原話我記不太清楚了,大意是你辦一所學(xué)校就好,不用前衛(wèi)。(笑)
總之你知道我有這么一個心。到了1998年,同一年,終于在席殊書屋之后又蓋出倆房子來,一個是中科院晨興數(shù)學(xué)中心(圖3),一個是山語間。在晨興數(shù)學(xué)中心的開幕式上,我爸也被請去了。我還作為建筑師代表,上臺露了一面,說了兩句話。
中午我們趕到人民大會堂找我爸吃飯,結(jié)果我一進貴賓室,一個人看見我就說:你是不是剛才那個建筑師?我說:是。他說,他是北大副校長,問我愿意不愿意去北大教書,辦一個建筑學(xué)研究中心,是這么來的一個事兒。如果我那天沒去吃飯,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找我,又是很偶然。辦學(xué)的事,我比實踐還想得多一點。有人來找我,我就去了。
去了北大教書之后,我有些東西是現(xiàn)成的,就是現(xiàn)在所謂的“本體建筑學(xué)”的框架。那會兒辦學(xué)方向更明確了,是因為我又有了實踐中的教訓(xùn)。雖然經(jīng)歷了南工,我還是太缺乏工程和實踐方面的基本知識和訓(xùn)練,所以自己實踐起來特別費勁。覺得一定得改變這種情況,就這樣開始了。
第一學(xué)年,就讓學(xué)生們自己動手蓋點房子。可費勁了,但我有些思想準(zhǔn)備,首先時間上碩士生一年級就干這一個事兒。我們那地兒——靜春園,是屬于北大的后院——也有點地,也有點需要,不用花太多錢,頭幾年就蓋了幾個小東西。第一個房子,木工車間(圖4、5), 還出了一個小冊子《79號甲+》(圖6),大概是這么一個開端吧。那會兒,也完全沒有可持續(xù)辦學(xué)的概念。
你要說策略吧,我真不敢說有,當(dāng)時倒是真有股有勇無謀的勁兒。
張利:您在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與一些日本建筑師一起分享了一種“非暴力革命”式的建筑語匯,實現(xiàn)了一種貌似溫和、實則激進的東方建筑實驗。如今,我們在日本乃至韓國看到這一實驗體系的寬頻譜的發(fā)展,而在中國,我們看到建筑實驗在憤怒的懷舊與炫耀的迎新之間兩極分化。這種現(xiàn)象是您當(dāng)時所預(yù)期到的么?它的原因是什么?
張永和:從今天看,還是有兩件事情要做。第一件呢,是建立對中國近現(xiàn)代建筑發(fā)展的認(rèn)識,尋找我們當(dāng)代建筑的基因。這里面也有一個白話建筑的概念,因為基因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當(dāng)時新文化運動那一批人,是在創(chuàng)造一個充滿著理想的世界,因為那是全新的,他們沒有完全準(zhǔn)備好也在情理之中。比如胡適寫的那個白話詩,當(dāng)時被取笑,人家說他寫的是打油詩,其實他寫的就是打油詩,但不妨礙他們走向?qū)儆谥袊默F(xiàn)代性。我覺得中國建筑可能真正缺的就是這個階段。我自己現(xiàn)在也還是沒準(zhǔn)備好,在四川安仁的那個橋館,可以說是往那個方向走,想找1960-1970年代的中國建筑基因,因為當(dāng)時設(shè)計的出發(fā)點是“實用、經(jīng)濟、在可能的情況下注意美觀”,有它樸素的邏輯。
如果第一件事構(gòu)成一條垂直的線,一個歷史、時間的軸;還有一條水平的線,一個地理、空間的軸,也就是第二件事:重新認(rèn)識“東西方”。應(yīng)該說“東西方”這個概念在今天的建筑學(xué)里很有問題。東西文化差別肯定有,這個不是要討論的。現(xiàn)在討論的是東西方建筑學(xué)的不同,在今天來說其實是比較模糊的,而且會更模糊,因為現(xiàn)在的全球化經(jīng)濟和地理政治帶來了東西方界線的移動。我的想法不是取代“東西方”,這個一定有,因為多少年來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我想的是“南北方”的差距對建筑學(xué)更重要,是地理、氣候的差距,它們帶來了文化差距,包括飲食著裝的不同,方方面面的。這樣一來就出現(xiàn)一個很不同的世界地圖。當(dāng)然中國很大,美國也很大,這樣的大國家肯定有南方,也有北方。可是跟歐洲比,整個亞洲都是偏南方嘛。張利:對。
張永和:北京可以說是南方的北邊緣,仍然可以有很多戶外生活發(fā)生在四合院里。越往南越暖,戶外生活就越豐富,院落里,檐下,廊下,堂間也是開放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建筑空間形態(tài)。通常說東西方的人跟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建筑跟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差異非常大,是因為東方是南方、西方是北方嘛。
所以從這兩個點,“近代基因”加上“南北方”,我覺得可能能找出一個屬于自己的建筑。
當(dāng)然肯定還有其他的因素,不同地區(qū)的技術(shù)條件是很不一樣的。比方說日本的情況,文化上現(xiàn)代傳統(tǒng)并舉,技術(shù)上非常先進,很具特殊性。
我覺得“實驗”這個詞容易誤導(dǎo)。真正的實驗,你得允許失敗。現(xiàn)在亞洲建筑中有很多趣味的東西,它們是特別保險的,不存在失敗的問題。更完全沒有像剛才講的新文化運動的那股沖勁。這是我的一個觀察。
成熟/Maturity
張利:您在近年曾經(jīng)不止一次地表達(dá)過對基本的建筑學(xué)的回歸,并戲稱這是年齡增長使然,而且明確宣稱自己不懼“不再前衛(wèi)”。在您看來,基本的,或經(jīng)典的建筑學(xué)關(guān)注是什么?我們在年輕時總是試圖擺脫,在年長時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的,是什么?如何在當(dāng)前易受各種浪潮沖擊的建筑教育中傳遞這種基本的建筑學(xué)的信息?
張永和:我覺得以前好多房子沒蓋好,有的時候就是因為對建筑基本知識不清楚、又缺乏經(jīng)驗,也有時候是設(shè)計用力有點猛,過猛造成的后果自己也得認(rèn)了。這個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對文化的認(rèn)識,需要有一個連續(xù)的時間軸的認(rèn)識。去了解不同的歷史階段怎么作為一個連續(xù)體過渡和演變,而不是切斷的。而且離咱們越近的這個“過去”越重要——1980年代的,就比1960-1970年代的重要。當(dāng)然我有自己的審美趣味,我可能更喜歡1960-1970年代,不是1980年代。因為你可以看到自己是哪兒來的,你可以看到一個領(lǐng)域是如何一步一步發(fā)展過來的,你就比較能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當(dāng)然可以再往過去倒騰。
我覺得現(xiàn)在這條時間線一旦切斷,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對立和武斷的選擇。有時候人家好意說,我在中國把現(xiàn)代主義給怎么著了。可其實問題不是我干沒干這事兒,問題是我最感興趣的其實不是現(xiàn)代主義,而是古典主義向現(xiàn)代主義的過渡期。
在古典主義向現(xiàn)代主義過渡那個時期,大家有一個朦朧的意識,這事兒要變。有的人也是勇一點,可能也是無謀之勇,也可能就是有個激進的態(tài)度。就有一系列多種多樣的嘗試,有的還輝煌了一陣子。今天也有一些建筑師會游離在古典和現(xiàn)代之間,并不是把現(xiàn)代主義排除掉,而是琢磨怎么從古典到現(xiàn)代。像柏林的漢斯·庫霍夫(Hans Kollhoff),有時候戴維·奇普菲爾德(David Chipperfield)也會。我在興趣上和他們有點像,可是又沒人家堅定。
我試圖把那個過渡期給拉開、放大。那個時代代表的是一種探索的狀態(tài)。是不是意味著可能性就多了?
但基本建筑學(xué)關(guān)心的就是材料、結(jié)構(gòu)、空間、使用、基地這些問題,是可以給學(xué)生一個明確的建筑學(xué)核心知識范圍的。
如何將基本建筑學(xué)明確的立場和文化上開放的態(tài)度結(jié)合,是我自己面臨的挑戰(zhàn)。
張利:我有那么一個感覺,從大概1990年代到20世紀(jì)初的中國開始,您那會兒的所謂的無知使得的純粹的東西,有點像春秋時候的感覺,后來就戰(zhàn)國了,變得完全是目的性的血腥征服和最后的統(tǒng)治,那個時候開始沒有,想打就打。
張永和:有一點吧。問題是后面也變得程式化了,你必須這么著這么著,甚至必須到哪兒念書去、讀哪些書等等,一下變得很窄。我在一定程度上,很懷念1980年代,并不是那個年代的房子,前面提過不喜歡1980年代的設(shè)計,而是那個年代西方開放的氣氛。其實后現(xiàn)代主義,不也是一種春秋戰(zhàn)國嗎,又亂了,大家瞎琢磨,胡想,胡說,過癮。
張利:“非常建筑”在很早就把建造的研習(xí)當(dāng)成是建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當(dāng)時的國內(nèi)是頗具爭議的,雖然在今天已被大多數(shù)院校所授受。能先講一下當(dāng)時創(chuàng)立建造課程的過程和所遇到的挑戰(zhàn)么?接著,能否再談一下對當(dāng)前的建造課程的看法?
張永和:我曾經(jīng)帶過清華的幾個同學(xué)一塊參加了一個建造活動,建了兩道互相支撐的墻,那是我在國內(nèi)比較早帶著學(xué)生搭東西(圖7)。關(guān)于建造這事,一定要想清楚,不能違背了摸索、探索、努力想辦法往前推進的這個初衷。
建造的目的,如果很明確了,其實也不見得非得造。造,常常是因為一個學(xué)生沒有任何機會去工地學(xué)習(xí)施工,而且沒想到過建筑師也可以動手,所以一造他會發(fā)現(xiàn)很多東西他沒學(xué)過。
如果這個學(xué)生有了一定的思想準(zhǔn)備,很可能他就不需要造了。舉一個例子,我以前在同濟教過一門設(shè)計課,大概是2003年、2004年那會兒。我當(dāng)時的思想方法都是得讓學(xué)生造點什么。用建造教學(xué)需要許多條件,你要造一個小房子,你得有地、有錢,施工一學(xué)期也不夠,再加上設(shè)計時間,更不夠。
后來我就想了一個招,讓學(xué)生設(shè)計一個30m2的房子,從第一張圖開始就畫1∶2的(圖8)。所以實際上你看那張圖是30m2的1/4那么大,零幾年還都是用圖板什么的。圖太大,圖板上畫不了,學(xué)生得趴在地上畫(圖9)。畫1∶2的圖馬上就牽扯到一個用什么材料,因為得有具體尺寸才能畫。他們就到材料店里去量、去照相,拿回來貼在圖上,這是一條木頭、那是一根型鋼,其實等于是沒建造的建造。我覺得完全達(dá)到目的。學(xué)生的思想方法是建造的,可是實際上他是通過畫圖完成的。
張利:剛才您說的那一點確實是,反正對我來說是太有啟發(fā)性了。這么說,原來的建造課,不管是不是真的像現(xiàn)在有這么豐富的材料、豐富的技術(shù)去造,它都是把“造”看成一個從“不知道”到“知道”而去追求新知識、甚至學(xué)生都不知道他追求到什么新知識的過程。現(xiàn)在造等于是反過來,先知道再造了,您說不需要造了。
張永和:因為比方說,同濟有建造節(jié),一個新生進去了,可能沒他事兒,他挨個一看,就了解好多。那他還造什么呀,他可以跳過那一步,他可以造難度更高點的東西。我看現(xiàn)在造的質(zhì)量都上去了。我那天在雜志上看幾張照片,好像是湖南大學(xué),我看他們造得挺好的。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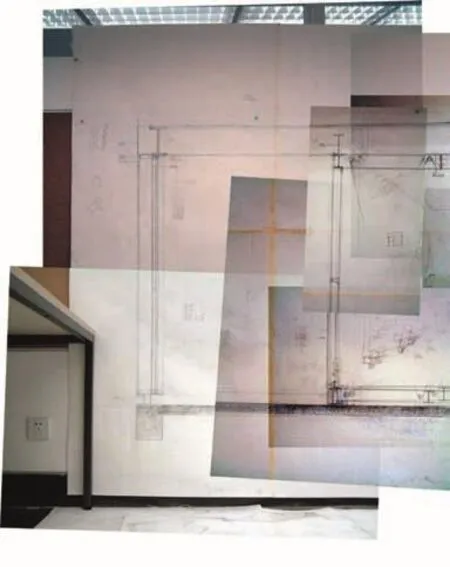
8
而且造還有一定的局限性,現(xiàn)在大家造都是用木頭多,不是因為這個房子要用木頭蓋,只是因為這個建造活動用木頭比較方便。砌磚頭不行,砌磚頭造價上還行,施工費勁。澆混凝土也是費勁。恐怕最好的學(xué)習(xí)建造的方式還是去建筑工地看,一看就明白,可得多去幾次,看不同材料的不同施工階段;如混凝土,要看支模、綁筋、振搗、拆模,所以得跑4次。
張利:能否敘述一下在麻省理工大學(xué)擔(dān)任建筑系主任對您的建筑觀所產(chǎn)生的影響?您認(rèn)為基于知識傳播、技術(shù)進步和平權(quán)運動的社會改良建筑學(xué)有光明的未來么?
張永和:我去美國的時候,是1981年,覺得終于能夠擺脫政治了,并不是左或右,一定程度上還不太清楚。你可能能夠想象,去了美國一聽人談?wù)危筒桓信d趣。
早年在美國教書那些日子就這么不關(guān)心政治,過得好好的。后來有機會回中國實踐,從1993年的春節(jié),大概干了幾年,我那政治覺悟就大大提高了。因為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殘酷了。再回到美國教書就不一樣了。1993年秋季回去萊斯大學(xué)(Rice University)教書。
學(xué)校里老師大多是左派,他們說的話我終于聽懂了,當(dāng)然也就轉(zhuǎn)過去了;到麻省理工的時候,我基本是西方所謂中偏左這么一個傾向,領(lǐng)導(dǎo)我的左派同事們就沒問題。

9
講一個麻省理工的事。麻省理工的規(guī)劃系,收的中國學(xué)生,都是北大的。因為美國式的規(guī)劃專業(yè)像文科、社科,北大的規(guī)劃也是從人文地理教,因此對口。所以我也不奇怪,北大學(xué)生也非常聰明。但是他們毫無政治頭腦,一說到政治左右不分,就跟小孩子似的,不像20幾歲的人。所以我在麻省理工的時候,我當(dāng)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當(dāng)?shù)眠€挺起勁,教訓(xùn)這些國內(nèi)來的學(xué)生。回頭看,要建立起一個基本政治立場我可能還會中偏左,也不會偏到右。回答你的問題,我認(rèn)同建筑學(xué)關(guān)懷社會。不過柯布“革命還是建筑”的命題早有答案了。還有,政治本身是個相當(dāng)復(fù)雜的問題。
例如,美國所謂的政治正確,就是用相對僵化的左派觀點對待一切問題,在大學(xué)里鬧得最厲害。我當(dāng)時在麻省理工做建筑系主任的時候最棘手的工作之一是處理種族問題。
再說兩句今天關(guān)懷社會的建筑實踐。這事兒,應(yīng)該是坂茂起的頭兒。去年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在威尼斯雙年展給燒了一把火。坂茂的操作我覺得是比較簡單的,更接近“本體建筑”,接近建筑的根。一方面他幫助弱勢群體,那些受災(zāi)的人,解決一些問題。另一方面他把他的建筑能力以及設(shè)計興趣可以發(fā)揮出來,如果就是為了救災(zāi),可能他買倆帳篷也行,他還要做建筑。阿拉維納是一個有很多建筑學(xué)以外能力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加社會活動家。他在那些方面的成就跟他在建筑學(xué)上的成就是有一拼的,他有一個并不是非盈利公司(NGO),而是盈利公司干這事兒的,建設(shè)社會住宅。等于他是開發(fā)商加建筑師。所以兩人的做法很不一樣。
現(xiàn)在全球面臨的最大的社會性建筑問題應(yīng)該是城市里的住宅。當(dāng)然,由于氣候變暖,災(zāi)難也特別多。一個建筑師應(yīng)當(dāng)有一個基本政治覺悟,能真正參與到社會事務(wù)里去,通過設(shè)計起到積極作用,是個好事。
至于我的建筑觀,在麻省理工經(jīng)歷了一個劇烈搖擺時期,我一會兒被像媒體實驗室(Media Lab)那種技術(shù)發(fā)展吸引過去,一會兒被這種社會因素的事兒、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事兒影響,不過最后又回到本體上來了,可能這個方向最適合我吧。
張利:在擔(dān)任普利茲克獎評委期間,您所參與過的最激烈的爭論是什么話題?您是如何捍衛(wèi)自己的觀點的?
張永和:普利茲克評委的人選,常常都是脾氣比較好的,討論不會是硬邦邦的。社會問題肯定是一個話題,建筑的本體問題也是一個,還有一個就是如何比較做得精的、好的和有突破的。現(xiàn)在好像進入一個時期吧,有很多很棒的建筑師,可是也沒有跳出來的那一個。評委們會很平和地發(fā)表意見,其實你一聽就是不同的觀點。最后當(dāng)然是投票解決問題。
張利:您曾談到“對過去自己做的設(shè)計看不上了”,能否展開一下這個話題?您如何總結(jié)您的設(shè)計思想在這20年間的變化?
張永和:我看過特別棒的建筑,而且是不同的好法。現(xiàn)在對我最大影響的建筑師之一,是一個瑞典人,叫西古德·萊弗倫茨(Sigurd Lewerentz),我每年在同濟都講他。他蓋房子,想得特別特別透。他最重要的房子是從78歲開始蓋的,82歲又蓋了一個,他挺長壽的,活到90歲出頭。看了他那個透徹之后,就沒有精細(xì)什么的這回事了。他獲得自由了。他的建筑是有質(zhì)量,但不光是工匠的質(zhì)量、施工的質(zhì)量,實際上是建筑師對一些東西有一個透徹的理解體現(xiàn)出來的思考的質(zhì)量。我以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建筑。再看自己的工作,很受刺激。
現(xiàn)在我又回到建筑的本體上,并不是我不再關(guān)心社會或環(huán)境或技術(shù)。對我來說建筑的核心就是蓋房子,從蓋房子這個事兒出發(fā),你可以關(guān)心所有那些事兒。但是如果不是從蓋房子出發(fā)而是倒過來的,先從外邊進來,我認(rèn)為是有問題的。因為這事兒如果先從外邊進來,它不一定到建筑學(xué)。比方說環(huán)境,該不該關(guān)心?當(dāng)然該關(guān)心。我要污染嗎?我肯定不要污染。那咱們解決這個問題吧,是不是用建筑的方法解決?當(dāng)然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有一個最經(jīng)典的例子,我以前在文章里寫過,塞德里克·普萊斯(Cedric Price)這個英國建筑師沒蓋過多少房子,他有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其中一個特出名的事兒是一個農(nóng)民買了一個農(nóng)場,找他蓋一個房子。這塊地離家開車來回大概要3、4個小時。所以這個農(nóng)民想讓這個建筑師在地邊上蓋一個房子住那兒,比方說干一個禮拜,周末回去。這個普萊斯接了這個活,過了一陣子他說我這個事兒給你解決了。你不需要蓋一個房子,你需要換一輛好點的汽車。(笑)
他這件事就是我說的那個思維,一個建筑師提供了一個非建筑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他一算帳你蓋房子花多少錢,你買了這個好汽車,第一少花錢,第二你每天可以回家跟你家人在一起,特棒。當(dāng)然這個建筑師失去了一個蓋房子的機會,假設(shè)他仍然拿到了所謂設(shè)計費。
也不是絕對說這個建筑師對或者不對。只是想說明為什么有“本體”這個事兒,也可以說是用建筑的立場和思維解決問題。反過來也可以說,建筑學(xué)就是沒這么重要。好多問題,建筑解決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法國的西線不就是這么回事,蓋了好多最先進,最棒的碉堡,結(jié)果德軍從后面過來了。
張利:那這個就附加疑問,詹姆斯·高爾韋(James Galway)年輕的時候在皇家音樂學(xué)院,一會兒想模仿馬賽爾·穆瓦斯(Marcel Moyse),一會兒想模仿更年輕一點的讓·皮埃爾·朗帕爾(Jean Pierre Rampal),而且模仿誰像誰,最后他到了一定年齡以后,他說他誰都不模仿了,想開了。您覺得您現(xiàn)在應(yīng)該是想開了?

10
張永和:不敢說。周榕給過我一些很開竅的總結(jié)。周榕他特聰明、看得準(zhǔn),他指出我特別幸運的就在于,我學(xué)什么都特別費勁,或者根本學(xué)不會。所以我想學(xué)別人也學(xué)不會,像高爾韋的模仿問題我沒有,我沒有能力模仿。周榕還會看我的設(shè)計,哪個方案里有股笨勁一定是我做的,像這次巴黎中國之家的競賽,他一猜就中。他很了解我,我從他那兒很受益。一定程度上,建筑不是一個需要太高智商的職業(yè),但需要非常耐心和細(xì)心。近年來,我的耐心和細(xì)心都有長進,再加上不知是缺點還是優(yōu)點的笨勁,我好像終于具備做建筑師的條件了。我這么說,很容易被誤認(rèn)為是謙虛,其實我是不信聰明人就一定能做好。
其實我不堅定的時候也想跟人家學(xué)。因為學(xué)不會,所以又回來了,但是我絕對動過心。有件事我特佩服我這老師羅德尼·普萊斯,可能是1983年,有一天,他跟一個好像是AA來的朋友在那兒八卦,說誰誰現(xiàn)在又跟風(fēng)做哪種設(shè)計了,又被別人的工作吸引了。我在旁邊搭茬,說那我也是,我看別人做東西都覺得比我做的好。后來我那個老師隨口一說,他說你還不一樣,你被吸引幾天就回來了。他說的是對的,不知他是怎么看出來的,當(dāng)時我自己反而不清楚。現(xiàn)在我就更知道我為什么喜歡某些東西。
張利:這是太大的一個福氣了。
張永和:就是現(xiàn)在才意識到,要是年輕時就明白了,那得多神呀。我給你看一個我喜歡的比利時人馮索瓦·史奇頓(Fran?ois Shuiten)畫的繪本(圖10),他是布魯塞爾人,畫的城市是在布魯塞爾的基礎(chǔ)上。他畫的都是新藝術(shù)運動時期的建筑,因為他懷念那個時代。可是人穿的衣服是文藝復(fù)興時代的,然后大家坐的交通工具都是飛行器。這個就是我特別感興趣的一個事兒:把不同的時代根據(jù)自己的世界觀搭在一起。實際上,我自己也是這樣,一個人喜歡的東西,并不屬于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文化。我根本不認(rèn)為時代精神是一個值得去追求的事兒,因為我碰巧生活在這個時代,你要是喜歡這個時代,那當(dāng)然太好了。可是我要喜歡其他時代的東西,那也沒轍。可是有意思的是這個人通過他的視覺小說,把這個自己的世界表現(xiàn)出來了。補充一句,他們家都是建筑師,他畫得太好了,就沒去當(dāng)建筑師,就干了這個。
我了解自己比較慢,可是這個過程不斷在發(fā)生。看不上以前的設(shè)計是一回事兒,但是真的還是在不斷地發(fā)展。沒多久以前,在麻省理工的時候,我還認(rèn)為自己的發(fā)展是獲得外面的知識,跟我?guī)У膶W(xué)生又知道一個新知識是一樣的,就覺得長進了。
張利:不管承認(rèn)與否,中國的建筑師在客觀上存在體制內(nèi)與體制外兩個陣營。體制內(nèi)建筑師陣營主攻國內(nèi)的主流項目,作用于大多數(shù)中國公民的生活,定義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城鎮(zhèn)主體面貌;體制外建筑師陣營主攻國內(nèi)的實驗項目,表達(dá)精英人群的人文情懷,在國際(特別是西方)語境內(nèi)呈現(xiàn)中國當(dāng)代建筑的探索。可能不是自愿的,您一直被認(rèn)為是后一陣營的引領(lǐng)。您認(rèn)為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陣營劃分會在短時間內(nèi)得到消融么?您目前所做的,受到國家相關(guān)部門重視的巴黎大學(xué)城項目會是這種消融的開始么?
張永和:這個問題真是最難的一道題。首先這個體制,老讓我想起我喜歡看的那個卡夫卡的小說《城堡》,真的就是無形的,可是就在那兒,而且很分明,它根本不是模糊的。建筑師們的工作,不管是體制內(nèi)的還是體制外的做的,差距又在縮小;有些房子的設(shè)計,看不太出來是設(shè)計院設(shè)計的,還是一個小事務(wù)所或者工作室設(shè)計的了。但我覺得建筑界的交流,陣營之間的交流,實際上比十幾年前少了。因為當(dāng)時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有很多建筑的事情會找一些體制內(nèi)的,找一些體制外的,一起聊;比方說早年,劉家琨在成都蓋好幾個房子,請大家去看,好多人去,然后也開座談什么的。
有一些項目由于規(guī)模和重要性不太會到獨立實踐那兒;也有些模糊的區(qū)域,比如民宿什么的,一個建筑師,不管是體制內(nèi),還是體制外,都有機會做一把。實際上我覺得問題在于,這種體制的界限還在,這個界限顯然沒起到積極作用。
最好建筑師們大家能共同來關(guān)心這個領(lǐng)域的發(fā)展,關(guān)心建筑的知識怎么能夠創(chuàng)造一個更好的居住和生活環(huán)境。在中國,大的住宅區(qū),意味著大塊的利益,通常不太會到體制外的小事務(wù)所那兒。其實像這種特別大量的,本質(zhì)上是社會性的項目,不能說是簡單的房地產(chǎn)項目。能夠讓更多不同的建筑師去參與,打破陣營界限來參與,我覺得應(yīng)該是一個特別好的事兒。現(xiàn)在因為渠道不通,大量的設(shè)計智慧和知識,就浪費掉了。
體制這個問題,是有點跟政策相關(guān)的事兒,是不歸咱們管的。如果有某種改善,肯定對推動中國建筑學(xué)是積極的,比如競爭會變得更公平。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這次參與的巴黎大學(xué)城“中國之家”競賽,可以說是這種改善的開端。
張利:體制最后需要您這樣有某種改變體制的能力的人。感謝您的時間。□
Interview with Yung Ho Chang
ZHANG Li
清華大學(xué)建筑學(xué)院
訪談日期:2017-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