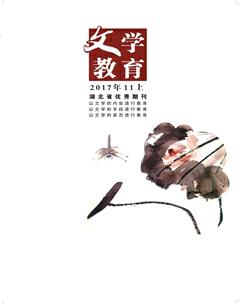論盛可以《野蠻生長》中的悲劇意識
內容摘要:不同于革命啟蒙或烏托邦理想式的鄉土書寫,70后作家盛可以延續其冷峻凌厲的筆觸,以寓言的形式重構了現代鄉村圖景,講述了另一維度的鄉村故事。不再是城鄉“二元對立”的敘述視角,盛可以將人物放置在由鄉村到城市的寬廣視域里,完成了別樣的“鄉土書寫”。社會形態、道德規范、情感交流、精神郁積、生命面貌等都在《野蠻生長》中得以淋漓盡致體現。三代底層人物“自由”卻不自主地在文明社會野蠻生長,最終被文明社會以“野蠻”的方式馴服。由身份危機帶來的認同焦慮,由情感危機引發的精神圍城,由命運危機造就的現實桎梏共同構成了一幅“非正常死亡群像”,籠罩著厚重的悲劇意識。
關鍵詞:身份焦慮 情感圍城 命運桎梏 悲劇
故事以“我”的視角,從我爺爺李辛亥講起,貫穿一百多年的歷史,將個人放在歷史時間和國家的維度里,展現了個體在歷史和社會中的浮沉。
一.身份焦慮
身份認同作為一種自我意識,更是一套社會關系建構的過程。人類對自身價值的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人的每一階段,無論是兒童期還是青春期或成年后,都在努力尋找“同一性”和“穩定性”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或認為是來自“他者”的認同)。[1]而“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完全受制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2]所以,當自我身份無法得到提升,同時對外在的“他者”因素,如觀念、機制、種族、歷史、社會等因素無力改變時,焦慮便隨之產生。
“第二性”。“女性有著不可超越的性屬身份,這意味著她無法在男權主導的社會中獲得對自身的超越”。[3]母性、妻性、女兒性——小說呈現出三代女性的精神底色。“我”媽謝銀月命苦模樣甜,一輩子忍辱負重,總是喜歡用眼淚表達一切。在她的觀念里,自覺女人比男人低賤,甚至從來不敢把底褲曬陽光下。“我爹是一家之主,老婆和孩子是他的子民。婦孺的羸弱溫順不但沒有讓主人變得溫和,反而助長了他的暴戾。我爹經常打我媽……我媽被揍得滿地滾,蓬頭散發一身血,終于離家出走。[4]“我”姐想要通過結婚擺脫我爹的專制和暴力,卻又陷入另一個牢籠:家庭生活寡淡,情感無從寄托。在建房時,她被當做牲口一樣勞作,得了闌尾炎后有幾回休息,被丈夫劉芝麻強拽著繼續勞作,并且認為當務之急是建房而不是去醫院。大姐深受母親好脾性的影響,“懂得真理在大多數人手里,她不可能一腳踹破真理”,[5]她將成為城里人和過上好日子的希望寄托在兩個女兒身上,而劉一花卻選擇輟學后進入廣州打工——面臨著更多的誘惑和逼仄的現實,經歷、學識的限制又使得她處處碰壁,只得在酒店、夜總會工作以維持生計,混跡于復雜社會。
“鄉下人”。“我媽……一刻不誤們迅速生下一窩鄉下人”,[6]生命從降臨的那刻便迅速被標簽化,打上了命運的烙印。這種與生俱來卻有差別的身份使得城鎮人與農村人,等級分明,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爹精打細算地申請病退讓“我”大哥退學頂班,大哥一下子實現農轉非,成為了村里人艷羨的對象;大嫂看中提前釋放的大哥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大哥的城鎮戶口,而她的理想就是在城里安家置業,將女兒李線線送到城里念書。成為城里人是家人及鄉下人賴以生存的最高理想。劉一草即使每次努力考到第一,仍會受到同學們“考得好有什么用,還不是鄉下人”的欺壓凌辱;大哥在菜市場上厘清“碰瓷”老太的事情原委,也因對方扔出一枚“農村人”落荒而逃;肖水芹在看清孫湘西奸詐本質后決定離開卻遭其糾纏,“不是他多愛她,而是被一個鄉里女人拋棄了,沒面子”。[7]“鄉下人”的自然身份使得這一群體自覺跌落到社會底層,而“外來人員”、“移民”的社會身份又使得他們“居間”于大城市的邊緣,成為“邊緣人”。[8]
二.情感圍城
沈從文在“城鄉對照”的原則下構建了一個優美、健康,有著強勁生命的湘西世界,展現出了城里人生命情狀的萎靡。盛可以則用冷峻的筆觸勾勒出另一維度的湖湘圖景。前者更多呈現出溫和平靜,而后者則是暗流涌動的狀態。這股暗涌在肢體和言語沖突及情感冷漠中,滲透著再平常不過的鄉村政治生態、人情態勢和“鄉土意識”——直接以鄉里社會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精神環境為根基的群體意識。[9]
被拆解的家庭倫理及溫情。從祖輩開始,家族的三代人的精神底色中都帶有明顯的“審父”意識,這成為影響他們日后行走的的動因。文始便牽出爺爺對爹的第一個妻子的侵凌,“我爹和我爺爺像兩頭老牛,平時各自吃草,萬不得已說句話,也會頂角打架,牛角碰撞出卵石聲響”。[10]爺爺嗜賭成性,父親以挖苦咒罵的方式表達不滿。加之先前結下的“梁子”,爹一直冷落爺爺;“在女嬰還沒成為負擔之前,他要去屋后的蘭溪河淹死這個‘背時鬼”。[11]父親重男輕女,面對父親的專制暴力大姐只敢在夜里嚼火柴棍,最后以草率結婚來逃離;“對于無法改變的現實,她尤其不說話,比如她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失學,當然她也沒把讀書看多重,只嫌父母的態度太冷”,[12]面對父母寄予的進城讀書出國留學的理想,劉一花選擇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南下進入飯店、夜總會工作。 而家人之間的怨懟、傾軋、冷漠、抗議、“報復”更體現在處理一些復雜事件上。大哥在嚴打時期莫名進入監獄后,父親一次也沒去看過;二哥將生命永遠停留在首都后,父親一把火燒掉了二哥所有的東西,他認為這比大哥成為勞改犯還讓他丟臉;在懷胎數月時,為上繳兩萬超生罰款(她身上僅有一百八十三塊五毛),大姐和劉芝麻四處求助親戚,卻總吃閉門羹,最終被“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13]……
對抗廝殺的兩性關系。“我”媽溫順老實,一輩子都在隱忍“我”爹的打罵,卻和馬社長茍且;為著手女兒的進城計劃,肖水芹在讓大哥白日去做工,夜里去捉田雞,大哥長期體力透支,還因此得了血吸蟲病。“我”爹為了省錢找江湖郎中隨便給大哥用藥導致傷口感染惡化,在考慮到長期的經濟成本后,爹毅然為大哥做出截肢的決定;大姐在婆家被當做牲口使喚,而當她迷上字牌后便對家里不管不顧,在進城注意到自身價值后展開了和有婦之夫的孫湘西的戀情。面對劉芝麻的多次糾纏,她總是把“我要和你離婚”當做令箭;而劉一花為了報答胡禮來對六子的“救命之恩”,不惜以身體為賭注,在她提出分手準備離開時,卻在與胡禮來糾纏中丟掉性命。橫沖直撞的他們在情感的世界里兜兜轉轉,走向對抗。endprint
三.命運桎梏
“命運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14]鄉下人有著自己的命運觀念,他們的潛意識中帶著天生的宿命感。而在參與社會關系建構的過程中,個人的命運卻更多地受到時代、社會、機制等的桎梏。野蠻”成為鄉下人并不自主的命運狀態,如同一株在野外生存的植物,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蠻荒的世界中畸形生長,且無力反抗。
性情忠厚的李春天最初將對“我”爹的不滿和對命運的反抗寄托在土地廟里,“我姐就在這兒跪拜,雙手合十,咒我爹病死、淹死、被水牛頂死、被瘋狗咬死、被汽車軋死;怎樣死都行,就是別讓他活著”。[15]而當“我”爹健朗地繼續罵罵咧咧,她發現土地爺是個騙子后便朝廟里扔泥巴,坐在田埂上面無表情地嚼草根,轟鳥群,扒蛙皮,在夜里嚼火柴頭,以此展開惡意而無力的反抗;李順秋在經歷勞改、截肢、妻女“變”故之后充滿宿命的溫和,“這無盡的叵測就是他的信仰,他的宗教,他認為他和世界的關系是設置好的,不可違的。”[16]劉芝麻苦心經營烤串攤受到城管的暴力執法的同時得知剛初中畢業的女兒劉一草跳樓身亡,“屋漏偏逢連夜雨”。“人生幕后,似乎總有一個人跟他過不去,破壞他的生活,損害他。[17]
另一方面,在經歷現代性革命之后,鄉村結束“無為而治”的社會生態,個人命運與時代、社會展開了掣肘。如大哥在嚴打時期莫名被抓走;大姐被強行結扎;二哥將生命永遠停留在了首都北京;劉芝麻去工地拿血汗錢被打至渾身血糊;六子被強行抓至派出所,再被遣到收容所,后在救治所不治而亡;喻書中因為弱勢群體爭取公平而尊嚴的生存及社會權利報道真實社會事件被撤職,繼而因被栽贓的經濟罪名被判刑十年。
最終,盛可以冷靜干練地素描出一幅“非正常死亡群像”。故事以女祖先難產而死開頭,而后“我”爹的第一個老婆因爬灰沉尸河流,首犯李大個在嚴打中被墻壁,大哥李順秋也因此入獄,大姐兩歲的兒子掉進水溝溺斃,二哥李夏至在夏至后將生命永遠留在了首都的“火葬場”,蔡老鱉被車撞死,大舅死于腦溢血,護工頭喬飛燕被槍斃,劉一草跳樓,劉芝麻被判死刑,李春天精神失常,喻書中被判十年監禁,胡禮來精神病復發,劉一花被掐死,肖水芹得癌失蹤,“我”媽患上了老年癡呆,故事尾以“我”爺爺壽終正寢。生命如同他們的姓名一樣卑微,而所有卑賤的生命在飽受肉體損害和精神摧殘之后,不約而同地走向了消亡。
家庭、社會是盛可以窺看生命的底色,在由城市、鄉村共同構成的生命冷暖、人性嬗變的空間里,卑弱的生命野蠻沖撞前行,在身份焦慮、情感圍城、命運桎梏的困境中最終走向了悲劇。“經由這些人的生命狀態,盛可以其實也在窺看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精神底色”。[18]“善的東西,是浮在上面的,而惡是沉下去的”。[19]作為當下少數以理性見長的女性作家,盛可以以其冷峻凌厲的筆觸,用這血淚書寫向我們展現出最原始且本真的粗暴力量,并以有深度的冒犯力量直面人生的和生活的陰暗和人性中的的原欲、瘋狂和失常,為從而折射出種種社會性問題,引人深思。
參考文獻
[1]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M].北京:三聯出版社,2015:32.
[2](英)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M].陳廣興,南治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117.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7:4.
[4][5][6][7][10][11][12][13][15][16][17].盛可以.野蠻生長.[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10,28,9,216,2,5,79,55,5,
163,272.
[8]翟晶.邊緣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論研究.[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69.
[9]程歗:晚清鄉土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1.
[14]鄭克魯.外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9.
[18]蘇沙麗.以“野蠻”之名穿透生命的風景—評盛可以《野蠻生長》.[J].百家論壇.2015(12).
[19]盛可以.后記·文學需要冒犯的力量.缺乏經驗的世界.[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211.
(作者介紹:丁紅丹,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