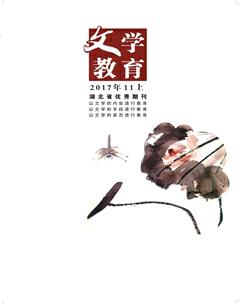《歸園田居》其三內涵新探
內容摘要:陶淵明的田園詩有大量表達隱居生活的內容,《歸園田居》組詩往往也被這樣解讀。但陶淵明既是一位隱士,也是一個“斗士”,《歸園田居》其三就表達了作者平和無爭的外表下的憤激的斗志,不宜因其為田園詩就放棄了對它的思想內涵的全面挖掘。
關鍵詞:陶淵明 歸園田居 田園詩 斗士 隱士
《歸園田居》組詩是晉代文學家陶淵明的代表作品,組詩共五首,其中第三首原文如下: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1]13。
“種豆南山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寫實的語句,描寫陶淵明鄉居生活中的一個片段,表現其親近自然,接近田園的質樸的生活方式。筆者此句并非寫實,而是暗用了漢代楊惲的典故。楊惲歌辭如下: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2]14可以發現,楊惲的歌辭和陶淵明的這句詩有太多的相同信息。如果陶淵明僅僅是想寫其歸隱后親近自然的田園生活,可以截取的生活畫面實在太多了,未必一定要寫種地的場景。就算寫種地,其當時種植的作物也未必是豆,就算其確實是種的豆子,也未必那么巧在南山也有一塊地。以上信息和楊惲的歌辭諸多相似,難道都要歸結為巧合嗎?似乎這樣解釋不太合理。
仔細品味楊惲的這首歌辭,表面上是說自己性情疏狂,放任怪誕,不屑與世俗人一樣去追求功名富貴,但不難看出歌中蘊含著對朝廷混亂、社會黑暗的憤慨和無力改變現實的無奈。楊惲雖然說“人生行樂而,須富貴何時”,但他并不是不需要功名富貴,而是如果要追求富貴必須要違背自己的良心參與到黑暗的朝政中去的話,那么二者權衡,他寧愿選擇了不要功名富貴也要遠離黑暗的官場。這一點和陶淵明的人生理想是如此的吻合。因此,有理由相信,陶淵明開篇第一句是借楊惲對朝政混亂和社會黑暗的不滿情緒表達自己也有相同的看法。與其說“種豆南山下”寫實,不如說一種間接抒情,在表達自己對時局混亂的不滿。
“草盛豆苗稀”表面上是說他不擅長農事,帶著一種自我調侃意味。但也交代出一個重要的事實:陶淵明歸隱田園后,并沒有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民以食為天,田里的收成不好,不難想象陶淵明退隱田下后生活的困境。《五柳先生傳》寫道:“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這是他實際生活的寫照。那么既然家無余財,倉無余糧,為何作者還要堅定的辭官返鄉呢?這就挑動起讀者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原因讓他寧愿自己種田也不愿為官呢?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這四句說明陶淵明的歸田是真正的自己種田勞作,而不像那些坐享其成的地主,他們雖然不做官了,但是家里有土地田產靠收租也可以生活無憂。譚元春《古詩歸》評道“高堂深居人,動欲擬陶,陶此境此語,非老于田畝不知[3]13”。陶淵明的這些詩,若非親自參加過農事勞作,不可能寫得出來。事實上,在過去封建王朝效法陶淵明歸隱并寫出大量的“仿陶詩”的人有很多,但實際上都是官僚地主階層,和陶淵明身為一個“農民”自己耕田的身份是不同的。比如唐代的王維,他的“漠漠水田飛白璐,陰陰夏木囀黃鸝”只是他退朝后在他的輞川別墅休閑,觀看農民勞動之景,并不像陶淵明一樣身體力行參加農事勞作。王維既無身體勞乏之苦,更不用焦慮衣食不足。陶淵明的日常生活像一個普通農民,整日勞作。大清早出門直到晚上月亮升起才扛著鋤頭回家,非常辛苦。山路陡峭難行,荒草上的露水打濕了他的衣服,備嘗農家耕作之苦。
如果說上句的“草盛豆苗稀”只是激起了讀者的好奇心,那么這四句詩進一步推動著讀者的好奇心不斷增加,不斷積蓄這種好奇心,這是一個蓄勢的過程。讓讀者們知道,原來陶淵明辭官并不是因為家境優越,不需要考慮生計問題,他辭官后日子過得其實很艱難;也不是因為辭官能夠在家清閑,他辭官后在家要每天耕田勞作,比做官要勞累的多。那他到底為什么要辭官呢?把這種好奇心蓄積得越來越強烈,最后,陡然一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干脆利落地揭示主旨。其實,作者想表達的不光是衣沾不足惜,而是包括了上面寫到的所有的內容都不足惜,衣服被打濕不足惜,道路難走也不足惜,工作勞累也不足惜,物質貧乏也不足惜,所有的這一切都不足惜,那到底什么才是值得珍惜的呢?最后一句,“但使愿無違”,如金石擲地有聲,令人恍然大悟。表現出了一個誓不與黑暗官場同流合污的文人的氣節和尊嚴,也表現出陶淵明隱藏在平和淡泊的文字外表下的火熱的憤怒和嫉惡如仇的剛強性格。
魯迅先生在《野草》的題辭里這樣寫道:“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4]。”陶淵明用淡淡的語氣訴說著前面幾句詩,就好比是地面上長滿野草的原野,顯得平和而安靜:“我辭官在家種田,莊稼收成不好,日子很艱難,從早晨到深夜,整日的勞作也讓我備嘗艱辛、疲憊不堪。”但這種平靜只是地表上的平靜而已,“地火在底下運行”,最后陶淵明說:“但就算再艱難困苦,我寧愿作種田的農民過這樣的苦日子也不愿意去做官。”這種表達方式就好比是熔巖噴出,爆發是如此的突然,令人看到了陶淵明的錚錚鐵骨和桀驁不馴的一面。魯迅先生曾評價陶淵明:“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5]。”陶淵明的這首《歸園田居》其三,最后一句和前面幾句共同構成的獨特表達方式便是其“金剛怒目式”的表露。
如果不看最后一句,將本詩的內涵定義為對田園生活和自然風光的熱愛是沒多大問題的。但是有了最后一句,我們反觀前面的詩句,將其解釋為“田園生活中一切都是美好的。……繁重的農業勞動在他筆下完全詩化了……心間裝滿充實與歡喜”[6]13恐怕就不合適了。梁啟超先生評價陶淵明,“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極多情的人”,“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7]。有關學者對本詩闡釋時往往忽略了陶淵明的這種“熱烈、豪氣”的情感內涵,而將本詩完全解釋為平淡自然的文風的體現,反應的是平和寧靜的隱士生活,似乎有待商榷。endprint
其實關于陶淵明的詩歌所表現出的思想內涵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陶淵明是一個隱士,其作品也主要表現內心平和,超然曠達等類似的思想內容。二是認為陶淵明是一個斗士,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他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抨擊劉宋政權的戰斗性,“讓蘊藏在心靈深處的感情的烈火象火山爆發一樣進裂而出。[8]”前者以昭明太子等人為代表,姑且稱為“隱逸派”;后者自宋代曾纮首倡《讀山海經》精衛一詩中“形夭無千歲”應為“刑天舞干戚”以來,擁護者甚多,清人陶澍、邱嘉穗等皆力主“戰斗說”,部分當代學者繼承此說,可謂之“戰斗派”,如游國恩等編的《中國文學史》即此說之延伸。
自魯迅先生撕破陶淵明“靜穆”的外表,揭示其“金剛怒目”的一面后,學術界也逐漸全面審視陶詩,不再單獨以隱士或斗士來標記陶淵明,這固然可喜。但對陶的田園詩和詠史詩還是容易類型化,標簽化。隱逸派多就田園詩來解讀其隱士生活,戰斗派多針對《讀山海經》、《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等作品探討其“微言大義”,強調“政治斗爭”,從而又形成了一種新的標簽化的劃分:即,田園詩便是表現陶淵明隱逸的一面,詠史詩等是表現其戰斗的一面。實際這是一種新的僵硬化解讀。
筆者以為:陶淵明是隱士嗎?是!不光其飲酒詩、農事詩、田園詩中可以看出這點,即便是廣為“戰斗派”學者津津樂道的《讀山海經》組詩也不全是“戰斗”,除了寫精衛、夸父等幾首詩有“戰斗力”外,寫西王母和追求長壽的幾首詩也可見其隱逸思想。陶淵明是斗士嗎?是!但也不局限于《讀山海經》、《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等作品,在部分田園詩中也蘊含了戰斗性,比如本文分析的這首《歸園田居》其三,平和的外表下蘊含著憤激而火熱的情感,就具有十足的戰斗力。
參考文獻
[1][2][3][6]周建忠:《大學語文》第二版,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魯迅:《野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5]魯迅:《題未定草》(六),《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7]梁啟超:《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3
[8]鐘優民:《陶淵明論稿》第11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介紹:王德龍,江蘇省聯合職業技術學院運河分院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唐宋文學,大學語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