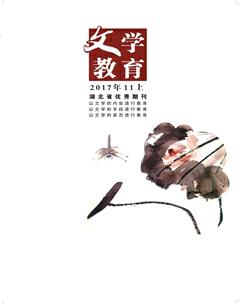MTI職業探索對職業使命感的影響
謝玖蘭+王恒


內容摘要:目的探索職業探索與翻譯碩士職業使命感之間的關系以及未來工作自我在二者關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職業探索問卷、未來工作自我問卷和職業使命感問卷,對206名翻譯碩士進行了調查。結果翻譯碩士職業探索對其未來工作自我和職業使命感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未來工作自我對職業使命感有顯著正向影響,未來工作自我部分中介職業探索和職業使命感。結論 翻譯碩士職業探索既可以直接影響其職業使命感,也可以通過未來工作自我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其職業使命感。
關鍵詞:翻譯碩士 職業探索 未來工作自我 職業使命感
1.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國際交往與合作越發頻繁,對各類高水平專業翻譯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翻譯碩士研究生作為高素質翻譯人才的主要來源,自2007年首批翻譯碩士專業開設以來,在學科建設和招生規模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翻譯碩士畢業后從事職業翻譯或與翻譯相關工作仍占很小的比例,一項針對7所高校翻譯碩士研究生的調查顯示,畢業后計劃從事翻譯相關工作占總數的41%[1],以暨南大學翻譯碩士的調查顯示65%的翻譯碩士沒有在畢業后從事翻譯工作的意愿[2],陸曉冰對廣西高校首屆翻譯碩士就業情況調查報告中發現,35人中只有6名是職業翻譯,10名從事英語教師兼職翻譯,19名從事跟翻譯無關的工作[3]。翻譯碩士(MTI)是培養實踐型的翻譯人才,這顯然不能滿足社會市場對翻譯人才的需求,也不利于行業的發展。當前,穩定與壯大翻譯專業人才隊伍是促進翻譯事業發展的基礎,增強翻譯專業人才對自身專業的認同感和使命感是穩定與壯大翻譯專業人才隊伍的關鍵,鑒于此,如何提升翻譯碩士職業使命感應該是當前翻譯人才培養與發展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研究翻譯碩士職業使命感的特點,分析其影響因素,對于高水平翻譯人才的培養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使命感是一種復雜的內心體驗,擁有高職業使命感的人將自身的認同性與其職業相結合,將自身同工作和社會價值相聯系,追求自身的工作在為社會貢獻出一定價值的同時能夠在工作中體驗到強烈的意義感,并從中實現人生價值[4]。職業使命感表現為對某種特定職業的強烈激情和有意義的體驗[5]。近年來,職業使命感因其對個人與組織發展的積極作用而成為職業心理學研究的熱點,相關研究發現,職業使命感水平高的個體,在做決策時會更加果斷,對工作會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熱情[6]。Hirschi和Herrmann的縱向研究也發現,職業使命幫助個體進行了更好的職業準備,即有助于職業規劃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7]。職業使命感會促進大學生求職清晰度,職業使命感高的大學生對職業目標以及將來的職業生涯規劃有更明確的認識[8]。胡湜研究了主動性人格、職業使命感與職業目標確定度的關系,結果發現主動性人格、職業使命感對于職業目標確定度有顯著的預測作用[9]。葉寶娟和鄭清等研究發現,職業使命感通過求職效能感對大學生求職行為和可就業能力產生積極影響[10-11]。另外,職業使命感還可以通過職業結果期待、職業自我效能正向預測免費師范生的學業滿意度,進而正向預測他們的學業投入[12]。綜觀以往國內外研究,關于職業使命感積極作用的研究多,前因變量研究少,而對職業使命感影響因素的研究對于感知和提高職業使命感就變得相當重要。
職業探索(career exploration)是個體認識自己并獲得自己與工作世界之間認定的過程,對個體的職業興趣和對未來的看法有顯著的影響,它能夠促進個體的職業成熟和與職業有關的自我概念的發展,以便對未來職業發展目標的確立有更明確的導向。根據 (Werbel)的觀點,職業探索包含自我探索和環境探索,自我探索是指個體通過探索自身的興趣、價值觀等進而對自身有更清晰的了解并對職業有更明確的規劃,而環境探索是指個體收集與就業以及求職相關的信息,進而對職業有更明確的認識[13]。己有理論研究者提出清晰而真實的自我意識可能是發掘職業使命的基石[14]。很多職業心理學理論均在強調職業選擇即是自我概念通過職業來表現的一個過程。可見,自我在職業發展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這種重要性同樣可能體現在職業使命中。Weiss等認為一個人要通過自我探索來了解真實的自我,并做出對可能自己的認知,從而發現自己的使命[15]。
未來工作自我(future work self)的概念來源于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是可能自我在工作領域的具體化,是一種積極的、以未來為導向的、工作中的特定可能自我,是一種指向希望的未來工作角色的自我認知結構。根據生涯建構理論(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個人通過好奇并不斷認識未來可能的自我來建構自己職業生涯[16]。Strauss等研究發現,未來工作自我能有效地預測個人的主動性職業行為(proactive career behavior),當一個人對自己未來想做什么有個清楚的認識時,他們會傾向于主動投入職業行為以達到這些未來的目標[17]。Guan,Guo,Bond等在對中國大學生的研究中發現,未來工作自我對生涯適應力和求職自我效能感(job search self-efficacy)都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18]。諸如此類的激勵作用可能是因為未來工作自我創造了一種在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差距,這一差距為個人提供了一種目標感和意義感,激勵個人去達到理想中的未來自我,從而更積極主動地投入到相關的職業行為中,未來工作自我為個人提供了一個目標、意義或原因去找到自己的職業使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清晰的未來自我認知和其提供的意義感可能是理解職業使命形成過程的關鍵因素。另外,職業探索對未來工作自我清晰度有正向影響作用[19]。個體通過自我探索,對自身內在特征有了充分的認識,從而有助于形成一個清晰的與工作相關的自我形象;通過環境探索,個體關注到工作環境和職業特點,有助于識別與自身價值觀一致的工作機會。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職業使命感的研究還較為基礎,研究內容上內涵辨析和積極作用多,前因變量研究少,本研究從自我概念的角度探討翻譯碩士研究生職業使命感的特點和前因變量,為職業使命感理論的豐富及翻譯碩士研究生教育培養提供有效參考價值。本研究具體探討:(1)職業探索與職業使命感之間的關系;(2)未來工作自我與職業使命感之間的關系;(3)職業探索與未來工作自我之間的關系;(4)未來工作自我在職業探索與職業使命感之間的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廣西五所高校翻譯碩士專業研究生,共發放調查問卷224份,回收有效問卷206份,有效率為92.0%。其中,男生75人,女生131人;研一124人,研二82人。
2.2研究工具
2.2.1職業使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Dobrow和Tosti-Kharas編制的12條目使命感量表(Calling Scale,12-CS)[5]。Dobrow和 Tosti-Kharas分別施測了四類大學生被試(音樂專業、管理專業、商學專業和藝術專業),驗證該量表可以根據不同職業變換不同的關鍵詞進行施測。國內研究表明,該量表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20]。測量方式為Liket7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06。
2.2.2職業探索量表
本研究采用許存根據斯頓夫(Stumpf)等編制的職業探索問卷(Career Exploration Scale,CES)[21],該問卷包括18個條目,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環境探索、自我探索、目的-系統探索和信息數量。測量方式為Liket5點計分(1=非常少,7=非常多)。本研究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56,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20、0.751、0.743和0.765。
2.2.3未來工作自我量表
本研究采用Strauss等編制的未來工作自我量表[17],該量表包括4個條目,用來考察被試對自己在未來工作中形象感知的清晰程度。被試被要求去想象一下未來的自己,然后評估這個未來形象的明晰程度。測量方式為Liket5點計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分數越高說明未來工作自我越清晰明確。Strauss等的研究證實該量表具有很好的內部一致性系數(a=0.92,并發現未來工作自我與職業承諾和主動職業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聯系。該量表己被基于中國樣本的研究所采用,在一個對中國大學生的研究中,Guan等(2014)報告了很好的信度系數(a=0.94),并發現未來工作自我與職業適應為、求職自我效能感和就業狀態等存在正向的聯系。
2.3研究過程和數據處理
在廣西大學、廣西師范大學、廣西民族大學、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和廣西科技大學教室內發放問卷,完成問卷大約需要20分鐘,所有問卷當場回收。本研究的數據使用SPSS18.0和AMOS17.0進行統計分析。
3.數據分析與結果
3.1效度檢驗
為了檢驗職業探索、未來工作自我和職業使命感這3個構念之間的區分效度,本研究采用AMOS17.0對三個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在三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以及單因子模型之間進行對比。結果如表1所示,相比二因子模型和單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最佳。這說明上述變量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確實是3個不同的構念。
3.2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總結了變量的平均值、方差以及相關系數。從表2中看到,職業探索的均值為3.365,未來工作自我的均值為3.265,職業使命感的均值為4.442,都大于中位數,表明翻譯碩士職業探索、未來工作自我和職業使命感總體處中等偏上水平。職業探索與未來工作自我(r=0.423,p<0.01)、職業使命感(r=0.542,p<0.01)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未來工作自我與職業使命感(r=0.492,p<0.01)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從整體說明,翻譯碩士職業探索水平越高、未來工作自我清晰度越高,職業使命感越高;未來工作自我清晰度越高,職業使命感也越高。
3.3回歸分析
3.3.1主效應檢驗
根據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模型1和2的結果,職業探索對未來工作自我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407,P<0.01),模型3和4表明,職業探索對職業使命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512,P<0.01);模型3和模型5表明,未來工作自我對職業使命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19,P<0.01)。
3.3.2中介效應檢驗
Baron & Kenny(1986)提出中介作用的檢驗可以運用3步回歸法[22]。首先檢驗職業探索與職業使命感的關系,其次檢驗職業探索與未來工作自我的關系,最后檢驗職業探索、未來工作自我和職業使命感的回歸方程。
從主效應檢驗中得知,職業探索對職業使命感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β=0.407,P<0.01),未來工作自我對職業使命感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β=0.512,P<0.01),滿足中介效應的前兩個條件,根據表4中模型6的結果可知,在將未來工作自我加入職業探索和職業使命感的回歸模型后,在未來工作自我進入回歸方程后,職業探索對職業使命感的回歸系數β值從0.512下降到0.394。由此推斷, 未來工作自我在翻譯碩士職業探索與職業使命感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說明,翻譯碩士職業探索不僅對其職業使命感有直接的正向效應,也可通過未來工作自我的中介效應而間接影響其職業使命感。
表3:職業探索、未來工作自我對職業使命感的回歸分析
4.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6名翻譯碩士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對職業探索、未來工作自我與職業使命感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得出了以下研究結論。(1)本研究發現翻譯碩士研究生職業探索和未來工作自我均值大于3,職業使命感的均值大于4,表明翻譯碩士研究生有較高水平的職業探索,對未來工作自我有比較清晰的認識,以及較高的職業使命感。(2)職業探索及其四個維度對翻譯碩士研究生未來工作自我有顯著正向影響。個體通過自我探索了解自身的價值觀念、需要、欲求和興趣等,通過環境探索了解工作機會、工作性質、薪酬待遇、工作環境、發展前景等,經過有目的性的選擇和搜集信息,進而對自身未來工作自我形成清晰的圖像。(3)職業探索及其四個維度對翻譯碩士研究生職業使命感有顯著正向影響。個人發現使命感的首要步驟是關注自我,了解真實的自己,然后去發現世界與自我的聯系,從而發現自己的使命,并做出合適的職業決策。(4)未來工作自我對翻譯碩士研究生職業使命感有顯著正向影響。未來工作自我為個人提供了一個目標、意義或原因去找到自己的職業使命,只有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真實地活著,才能清晰認識自己的未來,也才能明確什么是自己的職業使命。(5)本研究還發現未來工作自我在職業探索與職業使命感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說明職業探索不僅能直接對職業使命感產生影響,還能通過未來工作自我對職業使命感產生影響。這對提升翻譯碩士研究生職業使命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徑。
從本文研究結論可知,職業探索及其各維度和未來工作自我對翻譯碩士研究生的職業使命感有著顯著的影響作用,高校可以通過提升提高翻譯碩士研究生的職業探索水平及清晰的未來工作自我,進而提高其職業使命感。一是提高翻譯碩士職業探索水平。首先是加強職業生涯教育。高校將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培養目標與翻譯職業的特點相結合,形成全面的、系統的職業生涯教育體系,宣傳就業政策、提供招聘信息和教授應聘技巧這種單一的就業指導模式已經不能滿足職業生涯,必須加強翻譯碩士人格和素質的培養,提高職業生涯理念,以提高翻譯碩士職業化水平。其次是樹立全面的探索觀。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變遷,傳統的職業理論已不能適應現代職業的發展,翻譯碩士需要樹立全面的終生的探索觀。通過自我提問法和心理測驗法了解自身價值觀念、人格特點和職業興趣等心理特征,通過兼職、專職和間接搜集信息等途徑了解工作機會、工作性質、薪酬待遇、發展前景、提升機會等外部職業環境,不斷提升職業生涯適應力。最后是提供社會支持網絡。環境因素對個體職業探索行為的影響主要來自家庭、學校及同伴的支持。父母的物質支持、職業經驗和人際關系網絡可以轉化為職業探索的有效資源,同伴的支持可以拓展職業關系網絡和信息來源,學校和社會的職業培訓機構和職業咨詢機構可以提供專業的就業指導。二是重視未來工作自我的作用。通過職業咨詢,幫助翻譯碩士形成清晰的未來工作自我。首先幫助個人形成清晰的自我認識,通過探索自己的興趣、能力和欲求來認識自己是誰以及自己追求的目標,建構清晰的自我概念。其次是引導個人關注未來,通過找到自我與未來的聯結,評估未來職業中的可能達到的自我,幫助個人建構清晰的未來工作自我圖像,提供清晰的目標感和意義感,使個人認識到自己人生的意義和追求。最后是鼓勵個人尋找現在自我與未來自我的差距,去實現未來工作自我并從中感知到自己的人生意義,進而激勵一種主動去尋找職業使命的傾向。
參考文獻
[1]高黎,崔雅萍.翻譯碩士培養環境實證研究[J].教學研究, 2016,13(1):56-67.
[2]梁瑞清,李昕冉.高校翻譯碩士(MTI)教育現狀分析——以暨南大學為例[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5,36(2):155-158.
[3]陸曉冰.廣西高校首屆翻譯碩士就業情況調查報告[D].廣西民族大學,2014.
[4]Bellah,R.N.,Madsen,R.,Sullivan, W.M.,Swidler,A.,&Tipton,S.M.(1985).Habits of the heart.New York,NY:Harper & Row.
[5]Dobrow, S.R., &Tosti-Kharas, J. (2011). Ca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measure. Personnel Psychology, 64(4), 1001–1049.
[6]Duffy,R.D.,&Sedlacek,W.E.(2007).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a calling: Connections to care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0(3),590–601.
[7]Hirschi, A., Herrmann, A. Calling and career preparation:Investigating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temporal precedence[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13,83(1):51-60.
[8]沈雪萍,胡湜.大學生主動性人格與求職清晰度的關系:職業使命感的中介與調節作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5,23(1):166-170.
[9]沈雪萍,胡湜.大學生職業使命感與主動性人格、職業目標確定度、家人支持程度的關系[J].人類工效學,2014,20(4):5-11.
[10]葉寶娟,鄭清,陳昂等.職業使命感對大學生求職行為的影響:求職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及情緒調節的調節作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6,24(5):939-942.
[11]葉寶娟,鄭清,董圣鴻等.職業使命感對大學生可就業能力的影響:求職清晰度與求職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發展與教育,2017,33(1):37-44.
[12]陳鴻飛,謝寶國,郭鐘澤等.職業使命感與免費師范生學業投入的關系:基于社會認知職業理論的視角[J].心理科學,2016, 39(3):659-665.
[13]Werbel J D. Relationships among career exploration,job search intensity, and job search effectiveness in graduating college students[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0, (57): 379-394.
[14]Hall, D.T., & Chandler, D.E. Psychological success: When the career is a calling.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26, 155-176.
[15]Weiss,J.W.,Skelley,M. F,Haughey,J.C.,&Hall,D.T.(2004).Calling,newcareersandspirituality:Areflectiveperspectivefororganizationalleadersandprofessionals. In J.W.Weiss,M. F.Skelky,J.C.Haughey,D.T.Hall(Eds.), Spiritual intelligence at work: Meaning, metaphor,and morals.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inOrganizations, vol.5, (pp. 175—201).Amsterdam:ElsevierLtd.
[16]Savickas,M.L.(2013).Careerconstructiontheoryandpractice.InR.W.Lent,&S.D. Brown (Eds.),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pp. 147—183)(2nd ed.). Hoboken, New Jersey:John Wiley&Sons.
[17]Strauss, K., Griffin, M.A., Parker, S,K. (2012). Future Work Selves: How hoped for identities motivate proactive career behavio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3),580-598.
[18]Guan; Y-,Guo, Y.,Bond, M. H... 2014).New job market entrants future work self,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job search outcomes: Examining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odel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5,136-145.
[19]Cai,Z.J.,Guan,Y.J., Li,H.Y.,Shi,W.,Guo,K., Liu, Y., Hua, H.J.(2015).Self-esteem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work self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process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6, 86–94.
[20]張春雨,韋嘉,張進輔,李喆.師范生職業使命感與學業滿意度及生活滿意度的關系:人生意義感的作用[J].心理發展與教育,2013,29(1):101-108.
[21]許存.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其與焦慮、職業探索的關系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08.
[22]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51(6):1173-1182.
(作者介紹:謝玖蘭,廣西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2016級翻譯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等;王恒,西安政治學院2015級應用心理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應用心理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