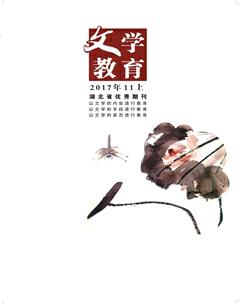莫言談新作《錦衣》的創作
莫言最近集中發表了一批新作,那么他在創作這些作品和修改打磨這些作品時又是怎樣進行的呢?莫言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說:去年年底的時候,有一次徐則臣來北師大參加活動,我說我寫了個劇本,要不要給你們看看,因為在我的記憶里,《人民文學》好像發這種戲曲類的劇本比較少,沒想到則臣很愉快地答應了,說他們很期待。之后由于春節比較忙碌,也因為當時沒有想好一個好的修改方案,因此一直沒把劇本修改好。《錦衣》這個文學劇本在2014年的時候寫好的。早在2000年的時候,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亞演講時曾使用過“錦衣”這個素材,因為這是我童年記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我母親跟我講的: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待字閨中,她母親卻經常在半夜聽到這姑娘閨房中傳出男女談笑的聲音,于是她母親跑來問女兒這是咋回事?女兒告訴母親說,一到深夜,就有一個年輕帥氣的小伙子來和她幽會,他穿著一身金光閃閃的衣服。母親對她說這必是妖孽,要她在這小伙子下次來的時候把他的衣服藏起來,女兒聽了母親的話后,真的把小伙子的錦衣藏到了一個柜子里,后來小伙子很無奈地在天明時分走了。第二天,這姑娘打開衣柜一看,柜子里一地雞毛。我在第一稿的時候曾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個類似于《白蛇傳》的神話故事,可越重讀越覺得這樣寫沒有現代意義,因為反封建、婚姻不自由等問題已經不再屬于現代問題,可是我又無法舍棄我母親講的這個故事。后來我讀到一些資料,看到在山東的膠東半島,曾經有很多青年男女遠渡重洋去日本接受孫中山同盟會的思想,回國后組織起來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錦衣》這個故事的時間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有了這個構思后,我修改得十分順利,加上之前寫了一些詩,就都交給則臣看了。戲劇創作一直是我創作中的重要方面,我的處女作其實就是一部話劇劇本,創作于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上海宗福先有個話劇叫《于無聲處》,影響很大,又看了郭沫若、莎士比亞很多劇本,嘗試了一下,自己感覺寫得不好,后來在搬家途中丟失了。2000年后,有位朋友跟我合作了一個劇本叫《霸王別姬》,空軍話劇團把它搬上了舞臺,連演了40天,而且作為文化部外派的劇目出國演出。這部劇的主演還因為出演這部劇獲得了梅花獎。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荊軻》。當時也是空軍話劇團的導演說他手中有一個劇本,寫的是荊軻刺秦王這樣一個歷史素材,他本人不太滿意。于是我想試試,便按照我對荊軻的理解把這個歷史故事重新演繹了一下,一個星期就交了初稿。這部劇后來在沈陽、北京人藝、圣彼得堡、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很多地方上演了。我當時熱情很高,想創作系列歷史劇,也有一些素材方面的準備,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沒能繼續。我是戲曲、尤其是民間戲曲的發燒友。我們高密這個小地方有一個很獨特的劇種叫茂腔,現在已經成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我的創作受到茂腔的影響很大,《檀香刑》里面就有大量的戲文。由于受過民間文化尤其是戲曲的滋養,我一直想做這樣一個嘗試,也作為我對民間文學的報答。《錦衣》是我獨立完成的戲曲文學劇本。之所以叫“戲曲文學劇本”,就在于它不是特別規范的戲曲演出劇本,一方面因為劇本太長,有三萬多字,而按照舞臺的要求大約一萬多字就夠了,所以《錦衣》若要搬上舞臺還要進行大量刪節;另一方面,里面的唱詞也不是按照規范的唱詞寫的,這個唱詞對平仄有要求,我卻寫得很自由。這是一種嘗試,也是我對民間藝術的致敬,同時也能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試圖開拓我藝術創作的領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