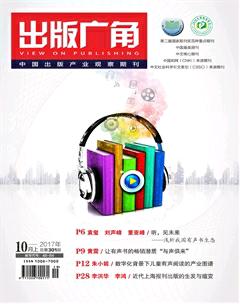社會化媒體輿情生成與傳播機制探析
【摘 要】 社會化媒體時代,媒介新技術的快速發(fā)展,深刻影響著我國信息傳播環(huán)境和輿論生態(tài)格局,變革著輿情生成與傳播機制。文章系統(tǒng)分析了社會化媒體輿情傳播機制,指出共情心理已經(jīng)成為社會化媒體輿情熱點的觸發(fā)模式之一。社會化媒體基于特定的網(wǎng)絡空間關系,存在不同的輿論自凈化現(xiàn)象,存在基于網(wǎng)絡表達情緒化和非理性的群體極化情形,以及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的新型議程設置功能。文章認為,社會化媒體具有獨特的輿情生成和傳播機制,給網(wǎng)絡輿情的研判和社會輿情的治理帶來了全新的挑戰(zhàn)。
【關 鍵 詞】 社會化媒體;網(wǎng)絡輿情;傳播機制
【作者單位】趙作為,內蒙古民族大學傳媒學院。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媒介新技術的發(fā)展日新月異,深刻影響著我國的媒介生態(tài)和輿論環(huán)境。近年來,眾多網(wǎng)絡輿情熱點事件呈現(xiàn)出社會化媒體時代即時性、網(wǎng)絡性和互動性等特點,深刻變革著輿情生成與傳播模式。與傳統(tǒng)媒體相比,社會化媒體正在以截然不同的傳播模式、傳播手段、傳播議題影響著社會公眾輿論生成格局。
一、社會化媒體已經(jīng)成為輿情事件的首曝媒介和傳播主渠道
社會化媒體(Social Media)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美國網(wǎng)絡社區(qū)研究學者Antony Mayfield名為What is Social Media的著作中。社會化媒體的傳播特點是信息多元化和碎片化、受眾分眾化、傳播過程從傳統(tǒng)媒體“一對多”的線性傳播發(fā)展成“多對多”的網(wǎng)狀互動傳播模式。社會化媒體因其兼具社交屬性與媒體屬性,符合當前信息傳播規(guī)律和受眾使用習慣,近年來得以高速發(fā)展。
2011年以來,以微博、微信為典型代表的社會化媒體呈高速發(fā)展態(tài)勢,成為輿論熱點事件的策源地和傳播主渠道,越來越多的信息和話題由社交媒體發(fā)端,向主流媒體擴散,經(jīng)主流媒體報道和傳播,繼而成為社會輿論熱點。媒介的話語結構悄然發(fā)生變化,作為“非主流”的社交媒體常常設置主流媒體議程,決定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
二、社會化媒體輿情生成及傳播特點
1.輿情聚集快,周期短
社會化媒體輿情發(fā)酵、生成和擴散迅速。社會化媒體降低了公眾的言論表達門檻,公眾可以在相關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發(fā)表個人的意見和態(tài)度。通過社交媒體的議題設置,分散在網(wǎng)絡上的“民意”聚合時間大大縮短,為輿論發(fā)酵奠定了基礎。輿情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中呈幾何級數(shù)傳播擴散,聚集速度非常快。一般輿情從生成到演變成熱點只需一至兩天,個別輿情事件以小時、半天計,如2016年8月的“王寶強離婚”事件,從發(fā)酵到引爆網(wǎng)絡輿論場只用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同時,由于我國正處于經(jīng)濟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中各種矛盾突出,網(wǎng)絡中涉及公眾利益的事件頻發(fā),輿論熱點呈多元化形態(tài),輿情迭代周期短,輿情變化和反轉頻度大大加快。
2.輿論多元、分散,成為真正的網(wǎng)絡“公共領域”
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認為,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公共領域的外延在逐步擴大,但作用卻愈加微弱。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是指一個介于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力領域之間的中間地帶,它是一個向所有公民開放,由對話組成,旨在形成公共輿論,體現(xiàn)公民理性精神,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運作工具的批判空間。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導致社會輿論和網(wǎng)絡輿論呈現(xiàn)多元、分散的狀態(tài),社交媒體中廣大網(wǎng)民個人意見的匯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哈貝馬斯口中的“公共領域”。
3.基于關系傳播的“輿論場效應”凸顯
輿論的形成除內容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傳播渠道和空間。在社交媒體時代,以社交媒體為載體的虛擬空間成為基于各種關系傳播的輿論場,不同身份的公眾或是因為共同利益、共同興趣,或是因對話題的看法、理念和傾向趨同,形成不同的輿論群體,“輿論場效應”逐漸凸顯。
強關系和弱關系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拉諾維特最早提出,強關系理論是指現(xiàn)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聯(lián)系緊密,弱關系是指人與人之間關系不緊密,異質性較強。基于不同的傳播架構分析,微信是典型的強關系傳播,而微博則是明顯的弱關系傳播。微信中的關系是人際關系的網(wǎng)絡延伸,輿論可以通過這種新型的“網(wǎng)絡人際傳播”迅速形成“封閉式”的輿論場域;而微博用戶雖然在表面上看是弱關系,但可以通過“共同關注”“話題聚焦”以及興趣愛好對其進行分類,在相對弱關系的環(huán)境下,微博也為網(wǎng)絡輿論場的快速形成提供了平臺。
4.強大的輿情聚合能力
當前,網(wǎng)絡輿情事件呈現(xiàn)出熱度高、影響深、范圍廣的特點,這與社交媒體對輿情強大的聚合推動效應密不可分。聚合放大是指社交媒體憑借自身的信息傳播特點,在輿情事件中所起到的聚合信息、引發(fā)社會討論和關注,從而產(chǎn)生一定社會影響的傳播效應。在輿情聚合過程中,個人的從眾心理、趨同心里、共情心理,社群中的群體極化、情緒感染以及鄰避效應等因素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現(xiàn)實中表現(xiàn)為觀點、碎片信息、情緒及行為等的聚合放大。
網(wǎng)絡輿情聚集的結果之一是容易引發(fā)輿情下線。近年來,諸多網(wǎng)絡公共熱點事件中,輿情下線成為輿情演變的趨勢之一,成為現(xiàn)實矛盾沖突和社會對抗的潛在隱患,對網(wǎng)絡環(huán)境和現(xiàn)實社會秩序帶來了不利影響。輿情下線引發(fā)的群體性事件,經(jīng)過網(wǎng)絡發(fā)酵和傳播擴散,極易勾連起其他地區(qū)利益相關的民眾表達類似訴求,發(fā)展成全國性事件,涉及主體的網(wǎng)絡輿論環(huán)境因此惡化,政府公信力受到破壞。
5.隱性輿情多發(fā),輿情軟風險管控和輿情治理難度增大
社交媒體的信息流動隱蔽性、用戶匿名性等特點,決定著社交媒體的源發(fā)輿情更加隱蔽,從而給輿情軟風險管控和輿情治理增加難度。復旦大學張濤甫將社會風險分為硬風險和軟風險兩個方面。硬風險是一種實體性風險,諸如自然災害、戰(zhàn)爭、社會安全事件、群體性事件等。軟風險則是一種“人化”風險,多是由人和社會系統(tǒng)中的主觀因素造成的,諸如社會認同、文化觀念、輿論等方面的威脅、危險。社會化媒體時代,以新媒體輿情風險為表現(xiàn)形式之一的軟風險急劇升級,在各種輿情事件中頻繁出現(xiàn),給網(wǎng)絡輿論環(huán)境的營造和社會治理工作帶來了嚴峻挑戰(zhàn)。endprint
當今社會化媒體時代,網(wǎng)絡輿論風險呈現(xiàn)“風險放大”效應,并表現(xiàn)出網(wǎng)絡輿論的負功能,即網(wǎng)絡輿論在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不可避免地存在情緒化和極端化表達傾向,并夾雜著網(wǎng)絡謠言和網(wǎng)絡暴力等社會負面信息,極易引發(fā)線上輿論風險和線下社會風險。
三、社會化媒體輿情傳播機制
1.基于共情心理的輿情熱點觸發(fā)模式
社會化媒體具有開放性、參與性和互動性等特點。從實質上來看,社會化媒體包含著個體之間的互動性以及溝通的社會性,體現(xiàn)著“使用和滿足”理論。人們通過自己特定的需求,參與網(wǎng)絡意見和輿論表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種表達來自受眾自身的私欲,并非出于構建公共輿論的目的。共情心理是基于人類同理心的心理活動。近年來,在輿情生成過程中,利用大眾的同理心觸發(fā)共鳴形成輿論聲勢的共情效應頻頻出現(xiàn),共情心理已成為引爆輿論的因素之一,在民生輿情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強烈的代入感易激發(fā)民眾的同理心,讓他們突破年齡、職業(yè)、性別等限制走到一起,去表達共同的訴求,發(fā)泄共同的情感,而社交媒體為此提供了絕佳的平臺。
2.基于網(wǎng)絡空間特定關系和理論下的輿論自凈化現(xiàn)象
社會化媒體時代,相對自由的信息傳播環(huán)境使得約翰·彌爾頓筆下的“觀點的自由市場”成為可能。在微博這一以開放性、弱關系為特征的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中,輿情熱點事件涉及的各種輿論觀點可以在網(wǎng)絡的持續(xù)傳播、爭論、辨析中去偽存真,愈加趨向于真理和真相,使得社會化媒體使用者在兼聽則明的環(huán)境下做出理性判斷。相較于傳統(tǒng)媒體時代和以論壇、社區(qū)為代表的web1.0時代,在社會化媒體時代,網(wǎng)絡輿論的自我糾錯與自凈化能力日漸凸顯。
輿論自凈化現(xiàn)象多見于網(wǎng)絡謠言和社會公共事件負面輿情的傳播中。微博成為當前我國治理網(wǎng)絡謠言的最有效渠道,因為在微博這一“意見多元”的平臺環(huán)境下,各種流言會被真相和理性觀點“糾錯與自凈”。在近些年諸多輿情熱點事件的負面輿情傳播中,微博、知乎等社交媒體也對輿情和公眾行為進行了有效的輿論引導,減少了社會隔閡,促進網(wǎng)絡和社會和諧。
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輿論形態(tài)的不斷演進以及學界的持續(xù)關注,作為輿論自凈化理論基礎之一的“反沉默的螺旋”理論越來越受重視。“反沉默的螺旋”理論,是指網(wǎng)絡及新媒體時代,由于受眾在“技術賦權”下民主參與意識的提高以及網(wǎng)絡虛擬特性等因素的影響,網(wǎng)絡輿論中的“少數(shù)”意見被更多的網(wǎng)民接受,逐漸發(fā)展為與“多數(shù)”意見勢均力敵甚至超越“多數(shù)”意見的情形。在此理論下,網(wǎng)民的從眾心理開始弱化,敢于公開發(fā)表自己的觀點和傾向,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輿論的演變,這些“少數(shù)”觀點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逐漸發(fā)展壯大。
3.基于網(wǎng)絡表達情緒化和非理性的群體極化
社交媒體受眾以年輕人居多,他們在強烈的民主參與意識、權利平等意識下容易產(chǎn)生話語的極端表達,從而形成由網(wǎng)絡表達情緒化引發(fā)的輿論亂象,如網(wǎng)絡暴力、網(wǎng)絡謾罵、人肉搜索等行為,給輿論環(huán)境和輿情治理帶來新的挑戰(zhàn)。
1956年,社會學家戈夫曼在《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xiàn)》一書中提出了“擬劇理論”,該理論認為:“人際傳播的過程就是人們表演自我的過程,但并非真實的自我,而是經(jīng)過符號喬裝打扮的自我。”社會化媒體打破時空限制,加之網(wǎng)絡的虛擬性,人們可以較為自由地參與網(wǎng)絡表達,不再喬裝打扮自我或偽裝自我。因此,社交媒體的網(wǎng)絡表達呈現(xiàn)出自主性、參與性強等特點。
社會化媒體的受眾特點使輿論態(tài)度變得感性化。作為公眾話語平臺,公眾對輿論客體即公共議題的表達往往出于個人的私利,呈現(xiàn)出情緒化、戲謔化的表達形式,這些情緒化的信息容易引發(fā)其他人的從眾心理,從而引發(fā)網(wǎng)絡輿論的非理性群體極化。
網(wǎng)絡輿論中的“羊群效應”,也稱“從眾效應”,是個人的觀念或行為由于真實的或想象的群體的影響或施加的壓力,而向與多數(shù)人相一致的方向變化的現(xiàn)象。群體極化最早由詹姆斯·斯通于1961年提出,是指群體在進行決策時,人們往往會比在個人決策時更傾向于冒險或保守,向某一個極端傾斜,從而背離最佳決策。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1895年出版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指出,群體成員易受暗示和輕信,群體情緒較為夸張和極化,容易形成群體極化現(xiàn)象。美國當代法哲學家凱斯·桑斯坦認為在網(wǎng)絡中也存在群體極化現(xiàn)象。網(wǎng)絡群體性是形成輿論的前提之一,因此,在多數(shù)輿情事件中都能找到群體極化的痕跡。當前,我國網(wǎng)絡傳播中輿論的“群體極化”現(xiàn)象比較突出,網(wǎng)絡群體性事件頻發(fā),已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突出問題。
4.基于新型媒介話語結構的“議程設置”
在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社會話語權被重新分割,傳統(tǒng)的話語傳播結構被顛覆,社交媒體的內容生產(chǎn)能力和傳播能力大大增強,影響力日益提高。隨著社交媒體中受眾角色的轉變,社會化媒體的媒介議程、公眾議程及行為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在眾多輿情事件中,社交媒體成為網(wǎng)絡話題和社會議題設置的主體,搶先設置議題,形成輿論,深刻影響著我國網(wǎng)絡信息傳播環(huán)境。
近年來,網(wǎng)絡熱點輿情事件頻頻呈現(xiàn)出“自媒體引爆輿論,主流媒體再跟進報道”的現(xiàn)象。從微博熱搜(話題排行榜)到各種社交媒體的新聞(話題)頭條推送,社會化媒體設置的議題時刻影響著社會議題的走向,眾多網(wǎng)絡輿情事件演變成人人議論的頭條新聞。憑借社會化媒體互動性強、受眾廣泛、信息傳播和輿論生成速度快等優(yōu)勢,社會議程設置和社會話語表達進入了人人皆可參與的泛眾化時代。
5.基于強弱關系下的不同輿論形態(tài)傳播
隨著我國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快速發(fā)展,社會化媒體趨于移動化、微型化,微博和微信作為微媒體的典型代表,已經(jīng)成為當下我國互聯(lián)網(wǎng)輿論生態(tài)的核心平臺。2016年絕大多數(shù)網(wǎng)絡輿情熱點事件都源發(fā)或傳播于微博或微信,但在具體的輿論傳播過程中,兩個平臺下的輿論形態(tài)卻有著很大的區(qū)別。
(1)“沉默的螺旋”效應
“沉默的螺旋”假說是德國著名的傳播學理論家諾依曼于1974年發(fā)表的論文《沉默的螺旋:一種輿論學理論》中提出的觀點。該假說認為,人們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之前,會判斷和比較別人的觀點,如果覺得自己的意見與群體意見一致處于“優(yōu)勢”時,就會果斷發(fā)表自己的觀點,踴躍地參與討論;相反,當發(fā)現(xiàn)自身的觀點與大多數(shù)人所持觀點不一致,屬于“較少數(shù)”或者處于“劣勢”時,擔心“被社會孤立的恐懼”心理會促使他們選擇保持沉默。這樣,“優(yōu)勢”的意見和“劣勢”的意見便呈螺旋態(tài)勢發(fā)展。
“沉默的螺旋”假說曾經(jīng)風靡一時,在一定歷史時期能夠幫助人們的揣測輿論走向成立,但是在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該假說并不能普遍適用。“沉默的螺旋”基于人們“害怕被孤立”的心理,在微博環(huán)境下,由于用戶匿名這一特點,“害怕被孤立”心理被極大弱化。同時基于微博的“弱人際關系”,人們在發(fā)表意見時,不必在意是否會被孤立,因為現(xiàn)實中沒人知道他們的具體身份。而在微信這一強關系平臺下,“沉默的螺旋”依然成立,人們在發(fā)表與多數(shù)公眾意見相左的看法時,會考慮“被熟人孤立”這一結果,從而不傾向于發(fā)表不同的意見或看法。
(2)網(wǎng)絡謠言自凈化效應
謠言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人際傳播。在微信這一強關系和封閉環(huán)境下,由于人們比較相信熟人說的話,使謠言的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廣。此外,在微信熟人間的封閉環(huán)境下,外部真實信息難以進入,謠言自澄清機制較弱,謠言管理難度增加。而微博作為信息公開的媒體平臺,謠言的自澄清能力極強,信息糾錯能力能夠很好地體現(xiàn)出來,這是微信所不具備的。有人戲稱:“微博是微信謠言的清道夫。”
|參考文獻|
[1]張濤甫. “軟”“硬”風險交織的中國社會治理及其對策[J]. 人民論壇,2014(9).
[2]趙作為. 社會公共熱點事件中“網(wǎng)絡輿情下線”的成因及防范[J]. 西部廣播電視,2017(9).
[3]方曙光. “弱關系”和“強關系”下的網(wǎng)絡互動和網(wǎng)絡運動[J].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
[4]覃夢河,晉佑順. 基于微博顯性結構特征的用戶強關系研究[J]. 圖書館學研究,2013(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