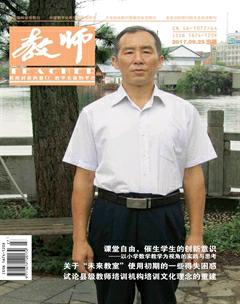行走中,聽教育的聲音
毛錫榮
著名教育家、美學家什克洛夫斯基說過:“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 一如作家周沖所說:“因為拒絕一目了然的人生,將自己放逐于各種可能,遍地花開,山河浩蕩。”所以,行走并不意味著毫無目的的流浪,對于教育者而言,行走就是讓你在山河故人前引發出對生命、責任、成長、選擇等深層次話題的思考。
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知識的遷移更替、教育常識的回歸與思考,已經將教育者推上了更高的價值評判之尺上。確實,教育絕非只是在靜態的書本中傳道,教育者只有自身視野開闊才能啟明教育智慧,才能將對生活的理解滲透進教育的紋理,達到對生命思索的提升、對教育認知的升華,推動教育路徑的流轉。
因此,每一次在臨近或是長途的行走中,我總會很珍惜生命里的種種遇見,在遇見里思索、在相遇中積淀教育的夢想。尋著人文的印跡,踏著江浙的山山水水,我一路跋涉,一路在學習中憧憬。我一直在想最好的學校的樣子,百年前的春暉肯定可以實現。白馬湖畔,老舊校舍,文人意氣,揮斥方遒。每一片瓦上都流淌著年輪的痕跡,背后的山更是默然無語,教育就是年代的久遠的滲透,是歲月有情的移植,更是春風化雨的柔情。蒼翠的磚瓦上密布的是流年的影子和無聲的誓言。教育是有聲的,碑刻的文字字字珠璣;教育是無聲的,路過的何止我們。每一個來過春暉的人都會感恩那個時代的理想,每一個默默矚目的人都會期許與春暉的一次重逢。“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盛大的重逢”,而且,我們在心里都有最誠心的儀式。
夜色來臨的時候,人文教育的大旗上的鮮紅也隨著時代的風風雨雨有了一些斑駁。在素質教育、核心素養呼喚聲中的當下,我們還是分外懷念像白馬湖畔、將軍橋邊的人文校園。也是在一次次出行和思考中,教育者對教育的理解、教育的憧憬才會越來越明晰,教育的行為才會真正落地生根。這些,都需要有心的教育者懷著對教育的熱忱不停止行走的步伐。
我們越是呼喚,越是憧憬,越是證明著這樣的教育的稀缺;但也越是表達著我們的渴求和追求腳步的熱烈。
每個教育者的心里都有一個影子,是白紙上用鉛筆輕輕的勾勒,是一個大概的輪廓,如同晨起的霧靄一般輕蒙,但它真真切切地存在著,成了教育最最動人的“場”。在這樣的教育的“場”里,某一日,學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每一縷聲音、每一個教育的表情和故事……在與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相遇時,教育理想的那個輪廓就豐實了,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影子了。
行者無疆,教育者,你更加不能停下。
(作者單位:江蘇省無錫市輔仁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