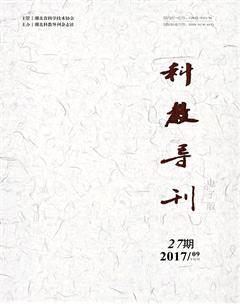論修辭語境創造的方法與技巧
龍永府
摘 要 修辭必須以語境為基礎,修辭語境的創造既要注意作品本身的時間、地點、故事情節、人物及人事之間的關系,又要從人們的生活經驗、社會知識和文化修養等方面入手構造,還要注意人們心理活動的變化。
關鍵詞 語言學 修辭學 語境
中圖分類號:H15 文獻標識碼:A
語境,話語所處的語言環境,是修辭學非常關心的問題。語境包括社會環境(交際者所處的社會環境、所陳述的事件發生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和上下文環境等。根據語言環境來加以處理,話語的意義既包括那些能作為單獨的詞的所指或所指意義來加以陳述的方面,又包括了那些必須作為句子甚至整個話語的意義來加以陳述的方面。因此,語言的意義就不止是一個簡單的關系或只有一類關系,而是包括了存在于話語、話語語境及其組成部分之間的各種各樣的關系。語言環境對語言意義有著不可分享的關系,對人們使用語言有很大的約束力量。正因為如此,修辭就不能不以使用語言的環境為基礎,也不能不以適應語境為第一義。所以說,語境對修辭是至關重要的。那么,如何創造適合修辭表達的語境呢?筆者認為應該從三個方面入手:
1作品本身的時間、地點、故事情節、人物及人事之間的關系
這是修辭語境創設的最基本的要素,由這些內容構成的語境是作品直接明顯表現出來的。例如鄧友梅的作品《追趕隊伍的女兵們》中寫到:
孫大胡子口氣莊重起來,“對敵人,仍然要叫他相信我軍主力在東邊,并且還繼續向東進!所以,天亮之后我們就要在敵人的視線之內,大搖大擺向東走!”
“我們都指誰?”
“一個團!”孫大胡子又笑起來,“你記得吧,在文工團里時,一唱平戲就叫我跑龍套。團長總說,老孫,你別看不起龍套,四個人代表千軍萬馬!這回我又跑龍套了,我們一個團代表整個南線的野戰軍!”
在這里,作者運用戲劇藝術中跑龍套的程式化表演特點來作比喻,非常確切地表現了戰略上跑龍套的重要作用。這一修辭形式就是以作品里發生的事作為語境的。
2從人們的生活經驗、社會知識和文化修養等方面入手構造修辭語境
與作品有關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都是作品本身提供的,而人們的生活經驗、社會文化知識則是積累的結果。魯迅在《阿Q正傳》中寫“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委屈。”“文童落第”的感受不是人人經歷過的,但人們可具有這種間接的知識。《牧馬人》中郭扁子給逃荒來的李秀芝找了對象,他把李秀芝帶到許靈均的住處,作了一番介紹,他說:“什么都好,就是窮點,不過越窮越光榮嘛……嘿嘿。”“越窮越光榮”是一個尋常的句子,但它卻引起了人們會心的嘲笑,因為觀眾都了解“四人幫”時的那條極左路線,把貧窮當作社會主義。這種語言效果的取得,不在于語言形式的本身,而在于它與深刻的背影意義的聯系。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新聞報》上,曾有過這樣的一個文章標題:豐子愷畫畫不要臉。理解和運用這樣的標題,是需要社會文化知識補充的。“不要臉”中的“臉”這個語素是多義的:指面孔,也指“情面”。“不要臉”這一語言單位可以是述賓詞組“不要(文中義:不畫)——臉”,也可以構成熟語“不要臉(不知羞恥)”。如果了解豐子愷先生畫人物面部只勾勒輪廓,而不畫臉部的眼睛、鼻子的特點,那么就會體會到語言藝術的趣味。如果沒有這種背影知識,就會產生聳人聽聞的效果。
3創造修辭環境要注意人們心理活動的變化
語言和心理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人們用語言來描寫心理,同時也用心理的變化來增強語言的表達效果。古詩中就常用人的情感變化來改變自然界的色彩。例如“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李白《菩薩蠻》),高樓上閨中人的愁緒使得碧色也具有了感情。“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王建《行宮》),詩人撫今追昔的感傷情緒,連紅色的宮花也不是絢麗而熱烈的。這種修辭形式一直沒用到今天。例如魯迅先生的《熱風·隨感錄四十》中寫到:“終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過看見窗外四角形慘黃的天,還有什么呢。”在這里,由于主人人心情的變化,那么在主人公的眼里,窗外的天空的顏色黃色前面便加入了主人公個人的情緒,一個“慘”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再如艾青的詩歌《生命》:“依照我的愿望/有期待的日子/也將要用自己悲慘的灰白/去襯映出/新生的躍動的鮮明”在這里,把日子賦予了顏色灰白,不僅如此,還加上了個人的心情作為定語“悲慘的”,這種修辭環境就是依據人們的心理活動來進行創造的。
色彩的變化完全系于人的情感。修辭的語境相當多是人們的心理因素構成的。阿Q的癩瘡疤與“亮”產生聯系是人們的想像活動的表現。《天云山傳奇》中宋薇看著羅群的照片“象一團火炭,從手上一直燃燒到心里”“照片”和“火炭”毫無相似之處,它們之所以產生聯系,是聯想活動感情作用的結果。
當然,語境是修辭形式產生效果的內在條件,語境需要作者和讀者來共同創造。作者要充分調動作品本身的一切因素,還要利用讀者的歷史、文化、社會知識經驗。除此外,作者還要了解讀者的思想見解、藝術情趣、審美心理,離開這些就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所創造的修辭語境,只有起到思想和感情交流的作用,那才是成功的創造。
參考文獻
[1] 鄧友梅.追趕隊伍的女兵[J].十月,1979(01).
[2] 張賢亮.靈與肉[M].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