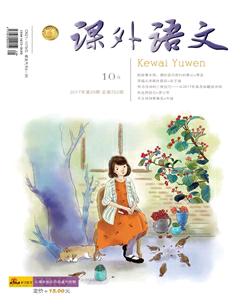千古詩詞賞菊花
牛銳
深秋時節(jié),百花凋零。大自然里惟有菊花在傲霜獨(dú)放,迎著這颯颯的秋風(fēng)起舞,形成了一道獨(dú)特的風(fēng)景。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菊花一直被看作是凌霜怒放、冷傲高潔的象征。《山海經(jīng)》載:“女人之山(在河南宜陽),其草多菊。”《禮記·月令》也說:“秋冬之月,菊有黃花。”屈原在遭讒被逐后,寫《離騷》以寄志:“朝飲木蘭以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花不僅五彩繽紛,艷麗嬌媚,而且具有多方面的經(jīng)濟(jì)價值,既可入藥,又可用來做清涼飲料。農(nóng)歷九月的深秋時節(jié),正是菊花盛開的時候。所以古人在賞菊的同時,留下了大量的詠菊詩篇,在凌風(fēng)傲霜的菊花身上,寄托了無盡的情懷。
因為菊花不與百花為伍,獨(dú)自開在秋風(fēng)里,因此菊花歷來被視為孤標(biāo)亮節(jié)、高雅傲霜的象征,代表著名士的斯文與友情。 很多詩人喜歡菊花,看重的是它歷盡風(fēng)霜而堅貞不屈的高尚品格。杜甫曾說“寒花開已盡,菊蕊獨(dú)盈枝”。元稹說得更直接:“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后更無花。”這兩句詩抒寫了自己的愛菊之情,盛贊了菊花的堅貞品格。東坡一句“菊殘猶有傲霜枝”,既贊菊花的品格亦隱喻自己的情操。鄭谷的《菊》則贊頌菊花的高風(fēng)亮節(jié)。“王孫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鬢毛。露濕秋香滿池岸,由來不羨瓦松高。”一、二兩句對比不同的人對菊的不同態(tài)度,初步點(diǎn)出菊的高潔。三、四兩句詩人以池塘岸邊的菊花與高屋瓦上的矮松(一種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處的植物)作對比,意在表明菊花雖生長在沼澤低洼之地,卻高潔、清幽,毫不吝惜地奉獻(xiàn)芳香;而瓦松雖居高位,實際上“在人無用,在物無成”。在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賦予它不求高位、不慕榮利的思想品質(zhì),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氣節(jié)。 宋代詩人鄭思肖的《寒菊》中“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fēng)中”一句則借菊言志,菊花寧可一直守在枝頭,何曾被北風(fēng)吹落在塵土泥沙中,菊花此時成了高尚人格的寫照。
由于詩人的經(jīng)歷和心境不同,同樣的菊花在不同人的眼里也有著不同的情致。比如有的詩借菊花表現(xiàn)了一種悠然自得的閑情。要論菊花詩,得先說陶淵明,因為他那篇《飲酒》太膾炙人口了:“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個人只有在心靜如水的時候,才能有如此的境界。其中的閑適和快樂,只能意會,不可言傳。還有的詩人借菊花表現(xiàn)了一種樂觀向上的熱情。不與春花爭奇斗艷,不與夏綠試比風(fēng)采,而是等到秋風(fēng)送爽時,才顯露出自己的追求和熱愛。所以杜甫在《云安九日》中說:“寒花開已盡,菊蕊獨(dú)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白居易的《詠菊》則更加明快:“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新折敗荷傾。耐寒唯有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自珍自愛,自立自強(qiáng),這是菊花的品格,也是人們的向往。
菊花開在秋天,有勇于與寒秋斗爭的勇氣,因此古代詩人也借菊花表現(xiàn)了勇者的豪情壯志。唐代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黃巢曾寫過兩首有關(guān)菊花的詩歌。第一首《題菊花》這樣寫道:“颯颯西風(fēng)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縱觀全詩,詩人實際上是以花喻人,托物言志。菊花,是當(dāng)時社會上千千萬萬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贊揚(yáng)他們頂風(fēng)傲霜的生命活力,又為他們的處境、命運(yùn)而憤憤不平,立志要徹底改變,讓勞苦大眾都能生活在溫暖幸福的春天里。第二首是《菊花》,又題《不第后賦菊》,大概是黃巢科舉落第后的泄憤之作。全詩這樣寫道:“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在這首詩中,詩人也是借開滿京城、占盡秋光的菊花來渲染起義軍大獲全勝,笑逐顏開的喜悅。全詩表達(dá)的應(yīng)該是一種對起義必勝的堅定信念和美好憧憬。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陳毅寫過一首《秋菊》詩,其內(nèi)容是:“秋菊能傲霜,風(fēng)霜重重惡。本性能耐寒,風(fēng)霜其奈何!”這樣的詩,的確可以給人力量。菊花能夠迎著寒風(fēng)開放,我們?yōu)槭裁床荒茼斨щy前進(jìn)?看似柔弱無比,卻有不屈不撓、枯而不凋的韌性。贊美菊花這種風(fēng)骨的名句,還有朱淑貞的“寧可抱香枝頭老,不隨黃葉舞秋風(fēng)”,許廷榮的“質(zhì)傲清霜色,香含秋露華”等。
菊花在自然界的百花中地位可能不甚突出,不喜歡菊花的人也大有人在。但菊花是幸運(yùn)的,它能得到中國文學(xué)史上偉大詩人的欣賞——與之為伍。花之形和詩人高尚的靈魂融為一體,造就了永恒的美。千秋萬代,士人百姓——不論是否知道屈原與陶淵明,讀過還是沒有讀過他們的詩作,都可通過凌霜盛開的菊花,與詩人的靈魂相晤,走進(jìn)一個個鮮活靈動的心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