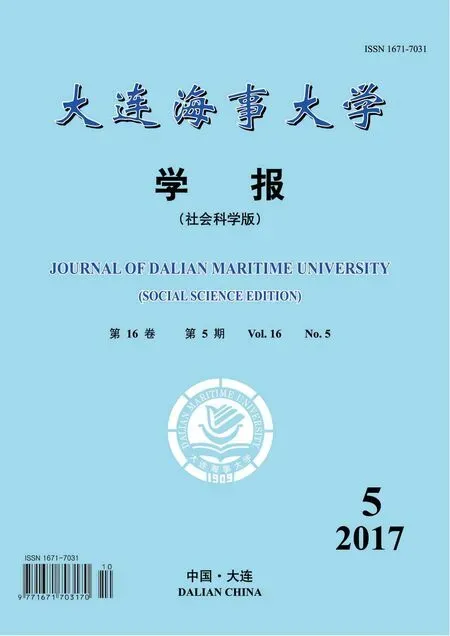從拉康話語交流理論的視野探析“藝術真實”
厲 梅
(大連海事大學 公共管理與人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從拉康話語交流理論的視野探析“藝術真實”
厲 梅
(大連海事大學 公共管理與人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藝術真實是指通過假定性的情境來反映社會生活內蘊的真實,它與歷史理性互為他者與動因,形成主人話語,這一話語中有一個惱人的剩余——小對形“不合情合理的可能”。在大眾傳媒語境中,“不合情合理的可能”在“新聞真實”中獲得了自身的合理性。圍繞著新聞真實,形成大學話語,塑造出強迫癥似的“知曉”主體。主體“知曉”而不“相信”。知曉主體面對“超真實”造成的幻境追問質詢,形成歇斯底里話語,其中生成了新的知識“交互被動性”。最終,一方面,“超真實”讓人在幻象中樂不思蜀;另一方面,“新聞真實”又將主體緊緊壓迫在堅硬的現實上,“藝術真實”中的歷史理性終為“剩余快感”替代。但今天的大眾仍然有自己的思考和成長,這為以價值理性反撥工具理性提供了可能。
拉康;藝術真實;新聞真實;超真實
在今天,一般意義上的真實似乎是觸手可及的。大眾傳媒中生成的符號影像無孔不入,超級真實。從網狀廣布的監控到全民激情參入的人肉搜索,使得真實無所遁形。對于文學藝術來說,它們的界限不斷被模糊和挑戰,從照相寫實主義到現成品藝術,再到網絡上流行的梨花體、羊羔體等,這些文本不再講究藝術光暈的營造,而是追求粗野實在。在這種語境中,新聞真實、超真實等成為文化的關鍵詞,那么,藝術真實這個經典的范疇還能否闡釋這些時代精神的癥候呢?
藝術真實是指通過假定性的情境來反映社會生活內蘊的真實,是“合情合理的不可能”。它不同于生活真實和科學真實,是主觀的真實,詩藝的真實。藝術真實這一概念對文學藝術文本具有廣泛的解釋力。世易時移,面對日益更新的文本,藝術真實是否也要尋找自己新的理論生長點呢?借助于拉康的話語交流理論,一方面可以一窺藝術真實的內部脈絡,另一方面,或許還可以為我們打開當今時代的文化地圖。
拉康的話語交流理論包含動因、他者、原因、效應四個要素,形成四種話語類型:主人話語、大學話語、歇斯底里話語、分析者話語。在每種話語中主人能指(S1)、知識網絡(S2)、主體($)、小對形(a)分占某位,形成各種可能的社會形態和調節主體間關系的網絡連接。[1]210所以,當藝術真實成為其中某一因素,進行話語交流時,應該可以為我們呈現今天的社會形態以及主體的生成狀態。
一、主人話語:“藝術真實”的意義交流模型
如圖1所示,這一模型呈現的是藝術真實的敘事機制。藝術真實是廣被接受的文學藝術之合理性的根據,是既有的知識網絡(S2)。文學藝術之存在的價值是通過營造假定性的情境,在情理邏輯的支配下,去打開更多的存在可能性,讓我們去發現更值得和更希望的一種生存狀態,即社會生活內蘊的真實。而誰需要這一真實?開卷求益,渴望被知識啟蒙的主體($),借助于打開的文本去實現自己意志的休歇或生命的激發。用拉康的理論來說,這一主體需要借助于藝術真實去彌合自己現實的與理想的、情感的與欲望的、意識的與無意識的等方面的分裂,去形成同一性的自我。這一主體構成了這個話語模型深層次的原因。另一方面,社會生活內蘊的真實由誰來決定或賦予?誰是這一話語的主人?由假定到真實,把不可能變成合情合理,這是如何發生的?顯而易見,這一過程離不開接受者的參與,和經由文本的自我確認,而接受者基于自己語境的有限性,使得他們的闡釋容易產生蔽見和誤讀。雖如耶魯學派的布魯姆所說,影響即誤讀,但要獲得社會生活內蘊的真實,在正誤與反誤的二元對立中,誤讀只能是正誤。再而,歷史維度的存在,使得對社會生活內蘊之真實性的把握變得復雜起來。如何超越這一維度帶來的盲點,恐怕只有使主體進入歷史,以理性為引導,以實踐為驗證,即上升到歷史理性的高度。

圖1 主人話語:“藝術真實”的意義交流模型
關于歷史理性,學界尚未形成統一認識。有人認識到,“自從黑格爾以來,‘歷史理性’常常被理解為這樣一種觀念:人類歷史乃是一個同時具備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客觀進程,歷史規律是同自然規律一樣不容違背的鐵的法則,人在歷史過程中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在于,在認識到此種規律之后自覺地順應和推進它的實現”[2]。另一種觀點認為,“在馬克思看來,合規律性合目的性只能是人的活動區別于動物本能活動的本質特征,社會歷史根本不存在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問題”[3]。兩種相反的觀點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對于主體而言,主體的認同需要投射出歷史理性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這也是后現代主義理論盛行之前總體性敘事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歷史理性并沒有關于社會生活內蘊的真實的“知識”,它只是占據了那個貌似擁有“知識”的位置,它成為一個主人能指,以其為動因,生成意義交流模型中的主人話語。
基于歷史理性作為主人能指的空洞性,歷史理性顯出了它詭辯或辯證的一面。當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被描述為血淋淋的時候,對于陳述的主體來說,那里積存著無以言說的烙在骨髓的創傷。但是對于歷史進程來說,它似乎又是一個必經的能夠自證的階段。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真”與“善”在此是錯位的。劉小楓已經捕捉到這一點,“歷史說明一切,證明一切。歷史哪怕制造了最野蠻、最荒唐的德行,都可以從歷史自身得到合理說明。人們不敢質問歷史理性的野蠻,因為歷史理性是客觀的,有自己的自然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4]。文學藝術之令人著迷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它們對這種錯位的敏感與呈現,這種錯位是存在的創傷。另一方面,它如緩釋劑一樣,在不斷的磨礪中導引調整著歷史理性的方向。如蕭紅的《看風箏》所呈現出來的在“革命者為革命事業拋家舍業”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間的尖銳撕裂中,在“做大事不拘小節”的流行腔調中,仔細思來都深潛著一種“真”與“善”錯位的悲哀,而文學藝術的呈現則讓人們思考如何避免、超越這種錯位,存在是否還有別樣的可能性。
這種“真”與“善”的錯位所帶來的創傷性重負如刺在喉,成為渴望啟蒙的主體難以圓滿的a(小對形)。也就是說,在以“歷史理性”為動因、以“藝術真實”為他者的意義交流中,有一個“剩余”——a(小對形)不能被縫合進去。如果說藝術真實指向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合情合理的不可能”,那么,這個a(小對形)可以稱之為“不合情合理的可能”,是“藝術真實”這個概念所遮蔽和難以消除的內核。
二、大學話語:“新聞真實”的意義交流模型
圖2中,“新聞真實”作為難以整合之殘余(a),促成了“大學話語”之形成。大學話語是主人話語的一種“現代”形式,即它們都是一種用權力支撐起來的話語,只是權力發揮其效能的方式和位置發生了變化。[5]825在這一話語中,話語的發出者——動因是藝術真實(S2)。藝術真實在這里是知其所以然的知識,是純粹中立的知識,對幾乎所有的文學藝術文本具有不容置疑的闡釋力,也是使得文學藝術在文化形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不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作品,也不論是中國或者是西方的文本,藝術真實都可以引導接受者從假定的情境中尋找到某種社會歷史的、審美意蘊的、哲學意味的真實。從李白的《靜夜思》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從席里柯的《梅杜薩之筏》到達利的《帶抽屜的維納斯》等,莫不如是。

圖2 大學話語:“新聞真實”的意義交流模型
在這一知識(S2)的背后,潛藏著它的支撐——歷史理性(S1)。在此,歷史理性不再是高調的頤指氣使、發號施令,而是隱蔽地實施著它的規訓的權力,它所指向的,是在主人話語中不能整合的小對形(a)。在主人話語中,小對形(a)是“不合情合理的可能”。在大學話語中,它變身為“新聞真實”。“不合情合理的可能”強調的是一種悖于目的性的存在,在大眾傳媒語境中,之所以冠之以“新聞真實”,是因為這種悖于目的性的存在經常出鏡為新聞,而新聞報道的傾向性與客觀性有著莫比烏斯帶式的扭結,這又賦予了它某種真實性。另一方面,“不合情合理的可能”在某些文學藝術文本中的呈現與新聞真實無異。余華在作品《現實一種》中早有提醒,小說看似虛構,實則是一種現實。小說中親人相殘看似超出情理、夸張假定,實則此類真實,新聞中皆所常見,不必渲染,自成小說。新聞真實堅硬、粗糙,藝術想象無力企及。只能疊合現實與文本,小說、新聞泯然為一也。
由此可見,在大眾傳媒語境中,“不合情合理的可能”在“新聞真實”中獲得了自身的合理性。歷史理性借藝術真實之口對話他者——新聞真實,實際上是基于一腔前仆后繼的豪邁情懷或者野心,即“藝術真實”給人以超越的快感,“新聞真實”給人以直面的痛感,故而,經由藝術真實去整合新聞真實之“不合情合理的可能”性,完成歷史理性啟蒙的大業。
這一整合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因為產生了分裂主體($)——知曉主體。在藝術真實中,由假定到真實的跨越需要主體去相信,去形成自身同一性的認同。而在新聞真實中,不合情合理卻又實在可能,這種矛盾不斷折磨著渴望啟蒙的主體,使其變成強迫性的主體,“不相信有什么用,現實就是這樣子的”,“我知道了,讓我知道更多點吧”。追求知曉,知曉卻帶來了更多的空無,主體的分裂醒目而驚心。大眾傳媒文化成為生成這一主體的溫床。例如影視作品多版本結局的現象。電影《勞拉快跑》給我們呈現了三個結局,形式新穎。在香港TVB拍攝的許多電視劇中,也流行起了多版本結局。在播放結局之前,電視臺會讓觀眾在兩個版本之間投票,哪個更得民意就播放哪個版本。從表面上看,這一舉動給了觀眾更多的選擇主動權,去熨帖自己的內心;實際上,它打破的是電視劇的真幻邏輯。電視劇本來在煞費苦心地講述一個“為真”的故事,但是多版本的結局消解了它的“真實”,并凸顯了它的虛幻性。這一舉動暗示著,觀眾要想從其中獲得形而上的教誨或享受,不過是把追問轉向自身而已,他們從虛幻美妙的世界中跌落到了粗糙堅硬的土地上。
“去幻”成為這個時代文化的一種標記。對于傳統審美文本而言,虛構假定常常是它們營造自己深度空間的法寶,而在今天,審美文本的作者時不時會跳出來跟接受者打個招呼,“嗨,不要當真,這是我虛構的”,如馬原的《虛構》等。與此相關的照相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等文藝創造的走向也暗示出這是時代集體無意識的一種顯形。在今天,某些文學藝術文本與新聞、報道、生活日記,乃至科學研究之間的界限越漸模糊,其合法性焦慮也日益顯明。例如,面對著玻爾斯坦的《兩模特與彎線椅和奇勒姆地毯》這樣超級寫實的審美文本,接受者不得不去尋求反審美的蹊徑。這意味著文學藝術已經無須濃妝淡抹,去營造那些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美了。這也是信息開放時代主體強迫性的體現,借助于大眾傳媒可以發現一切如皇帝的新衣,揭之即現,何必再故作姿態,假裝深沉。
三、歇斯底里話語:“超真實”的話語交流模型
如圖3所示,在歇斯底里話語中,主體($)向主人(S1)發起追問,即我們接受了你的符號性委任,但你許諾給我們的呢?為什么這樣?為什么那個人是我?這一追問使主體陷入到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態。在這個話語交流模型中,知曉主體($)知道得越多,失去的快感也越多,就像我們面對很多的新聞真實,不僅沒有洞明真相的快意,反而滋生了無盡恐慌。這構成了主體之言說的原因——(a)信仰缺失,是主體知曉太多所付出的代價。從西方的文化發展來看,當上帝、理性、科學等被證明不必然宜于歷史的連續發展時,人們陷入到了信仰缺失、價值虛無之中,如現成品藝術的流行反證了“怎么都行”的時代邏輯。于是,主體向他者——超真實(S1)尋求答案。超真實在此作為主人能指縫合起一套新的符號秩序。超真實是借助于大眾傳媒塑造出來的符號真實。按照鮑德里亞的說法,形象表面上是基本現實的反映,但實際上卻掩蓋了基本現實的缺失,最終成為與任何現實無關的純粹的仿像而已。[6]超真實在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方面給我們勾畫了美好的愿景,塑造著我們的想象,同時又侵染著我們的無意識,將我們對時代、對現實的感知變成了如安迪·沃霍爾批量制作的符號記憶,將我們對生活不論是歸順還是叛離的選擇都變成了二手貨。

圖3 歇斯底里話語:“超真實”的話語交流模型
“一切很美,為什么我卻為幻象之奴?”大眾傳媒告訴我們可以擁有的生活,為什么我們卻離它那么遠?對此的回答是新的知識(S2)——交互被動性。這一知識是歇斯底里主體的發現,這一發現盡管不能解決信仰缺失(a)的問題,但畢竟是向真相邁近了一步。交互被動性,即主體不間斷地主動行動著,同時把自己生命的根本被動性轉移給另一人。[1]280這另一個人可以是小他者,也可以是大他者。如今天的藝術欣賞經驗,人們走進影院,看完、笑完、罵完,離開影院,僅此而已。人們看似主動,盡享選擇自由,實則可選為無,熬過時間罷了。伊沙的《等待戈多》對此有著精彩的點睛。在實驗劇場,大家都在無聊看戲。大家都知道戈多不會來,但大家都在等。后來看門老頭的傻兒子上場,他們興奮,起立鼓掌。生命的根本被動性在這里表現為“知曉太多,提前劇透”,生命變成了一場沒必要的等待,但大家依然在向他者進行著“等待”的表演,以對后者的遵從來轉移自己的被動性。
這一交互被動性不僅發生在主體身上,歇斯底里的主體發現,這也是大他者,即符號秩序的一個強迫性行為,符號秩序通過對主體的閹割,使其認同其父法權威。但是它對主體的失信暴露了它內在的缺失和不完滿,它不過也是圍繞著某個(a)建立起來的象征秩序而已。它以不容置疑的父法的閹割,來掩蓋自身的被動性罅隙。這就解釋了超真實無論如何精美、如何表達關懷,都不能慰藉焦慮分裂的主體,因為畫餅如何充饑?
四、結 語
從藝術真實、新聞真實到超真實,從主人話語、大學話語到歇斯底里話語,如一條幽長的小徑,灑落了一些當今文化的斑駁倒影。一方面,“超真實”讓人在幻象中樂不思蜀;另一方面,突然闖入的“新聞真實”又將主體緊緊壓迫在堅硬的現實上,“藝術真實”中的歷史理性終為“剩余快感”——能享受就享受吧——替代。在享受剩余快感之余,主體也會發出歇斯底里的追問,這種追問總是能夠抵達某些真相,窺得人生的某些實在。“一當歇斯底里主體真的認同了他者指示給她的某個主能指,一當她真的從這個主能指中獲得了自身同一性的幻覺,即讓S1居于主導的位置,歇斯底里話語就轉向了主人話語”[5]851,開始新的話語循環。或者,歇斯底里主體可以一直在言說的路上,追問、覺悟、判斷,就像大眾對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依然飽含期待一樣,去發現知識,去尋找值得相信的可能性。
[1]齊澤克.實在界的面龐[M].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彭剛.歷史理性與歷史感[J].學術研究,2012(12):87.
[3]劉曙光.歷史合規律性合目的性問題辨正[J].北方論叢,2006(6):102.
[4]劉小楓.拯救與逍遙[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60.
[5]吳瓊.雅克·拉康——閱讀你的癥狀: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6]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42.
I0
A
2017-07-02
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L16BZW006)
厲 梅(1979-),女,博士,副教授;E-maillm_llm@163.com
1671-7031(2017)05-01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