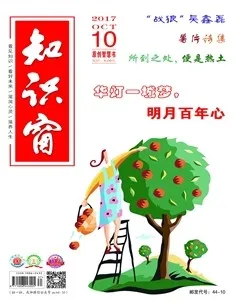一群人的狂歡,勝過一個人的孤單
程錦
時隔多年,當有人再次和我聊起那個被風吹過的夏天,我都會特別掛念,掛念那個自由自我的孩子。
1
世上除了一個孩子,其余所有的孩子都會長大。
那個永遠拒絕長大的孩子,不知現在如何。他還在永無島自由自在地飛嗎?我很掛念他。
書上曾說,從第二個路口向右拐,再徑直走,一直走到天明,就會到達永無島。可惜,我到現在也沒法到達永無島。因為我不是彼得·潘。
我只是平凡世界里的一個孩子。按部就班地讀書,按部就班地高考,按部就班地上大學……對我來說,生活就像一本定了稿的劇本。我痛恨這些平凡。
其實,我可以像曹哲那樣不按部就班的。
2
那年,曹哲19歲,披頭散發,穿著破洞牛仔褲。他沒有讀高中,而是去了本地的藝術學校學習音樂。他說,音樂是一個烏托邦,它容許你的白日夢做得更久一些。
畢業之后,他在一個無人問津的胡同里捯飭了一個音樂班。由于起步晚、名聲小,前來學音樂的孩子寥寥無幾。他整日百無聊賴地把玩著樂器,慘淡經營。
走進音樂班,我看見房間墻壁上掛滿了各種各樣的吉他:安德魯、卡馬……他看著我背了把吉他,問我是不是想學琴。我搖了搖頭,取下吉他包,從口袋里掏出一張A4紙。
我說自己寫了一首歌,希望他能給這首歌賦予靈魂。
毛茸茸的陽光下,鋼琴蓋被他微微支起。他坐在鋼琴前,勾起溫和的笑,讓我把曲子哼一遍,接踵而至的是從他指尖奔流傾瀉而出的旋律。
“這首歌蠻小清新的,應該配C調。你先回去,過幾天編好了曲譜,我給你電話。”他嘴角微微上揚,爽快地答應了我。
我蹬著單車絕塵而去,開心得像夢想照進了現實。
3
雨后初霽的傍晚,我接到他打來的電話。
他背對著我撥弄琴弦,頭發被他懶懶地綁在腦后,白皙纖細的手指在吉他指板上自由地轉換和弦。泠泠沏沏的歌聲,伴隨著悠悠長長的旋律,如同清風穿過夏日蟬鳴的樹林。
我為之啞然,這是我寫的那首歌嗎?婉轉的R&B曲風如此驚艷。副歌結尾的那段間奏短促而嘹亮,如同明亮的曙光將我灰暗的心房一點點照亮。
我如癡如醉地聽完后,迫切地問他:“你可以教我這首歌嗎?包括伴奏。”他問我為什么寫這首歌,“歌詞蠻憂傷的,看多了郭敬明的小說吧?”我撓了撓后腦勺,什么也沒說。
4
他沉默地轉過身,打開電視,電視上正放著《中國新歌聲》。他突兀地說:“你知道嗎?我去年參加過這個節目呢。”
“然后呢?”我好奇地問。
“沒有然后了。”他像個泄了氣的皮球聳了聳肩,說他去年參加《中國新歌聲》的海選,評委說他唱歌時河南話口音太重,就否定了他。他不服輸,又參加了《鶴壁好聲音》,結果毫無懸念地拿到了冠軍。
我樂不可支,說他如果以后出唱片的話,他的歌絕對走不出河南省。
他憤懣不平地說:“誰說的,當年還有人說黃家駒的歌走不出香港呢?莫欺少年窮!”
5
下班后,他讓我留下來陪他一起看NBA。他手指著電視熒幕,說:“快看,科比要絕殺了,他的轉身投籃無人可擋。”
末了,科比一個轉身起跳,三分球入籃。果真像他說的那樣,科比所向披靡。他看到科比進球了,振臂狂呼,天真得像個孩子。
我問他平時就這樣孤僻嗎?他說他平時也會參加各種派對,也喜歡熱鬧的場合。
我疑惑地問:“創作不是一個人的戰爭嗎?”
他搖了搖頭說:“一群人的狂歡,勝過一個人的孤單。”
說著,他刷地拉下卷簾閘門,發動起摩托車,遞給我一個頭盔,問我要不要“擬把疏狂圖一醉”。
6
藍灣街頭燈紅酒綠的酒吧。
原來他是一名酒吧駐唱歌手。斑斕閃爍的燈光下,震耳欲聾的重金屬音樂里,掩藏著一群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也有一個群體,他們或低吟淺唱,或徹夜狂歡。他們不知道愁之滋味,他們只知道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
曹哲站在臺上高呼我的名字,讓我上臺唱歌。我羞怯地走上臺,握著麥克風,跟著樂隊的伴奏,唱了一首《十一月的雨》。
一夜的狂歡。我們都忘了外面的天空到底是日落星辰,抑或東方魚肚白。
恍惚之中,我聽見他對我說:“千萬不要長大,長大是人必經的潰爛。”
7
那天,他和一個人在音樂班門口發生爭執。最后那人狠狠地掌摑了他一下,憤然離去。他沒有還手,只是直挺挺地站在烈日下,哭了。
我想走上前去安慰。他擺了擺手,讓所有人散去,說今天打烊了。說罷,他轉身將卷簾門擲地有聲地拉了下去,把自己幽禁在里面。他如同一只受傷的貓蜷縮起來,舔舐著身體上的傷疤。
自從那件事發生以后,他的店面一直打烊,手機總是打不通。直到我去大學報到前,我們再也沒有聯系過。
時間就像手中被風揚起的細沙,吹走了,再也沒有飛回來。
今年7月,我大學畢業。我與青春也走失了,我早就不看郭敬明的書了,再也不是那個動輒45度角仰望天空,一言不合就淚流滿面、悲傷逆流成河的那個孩子了。
我沒有成為我崇敬的偶像,我依然是那個在理想路上踽踽獨行的小人物。我沒有再像18歲那樣迷戀音樂,而是換了另一種方式對抗孤獨——寫作。
時隔多年,當有人再次和我聊起那個被風吹過的夏天,我都會特別掛念,掛念那個自由自我的孩子。